孟京辉:我就是想让你误解堂吉诃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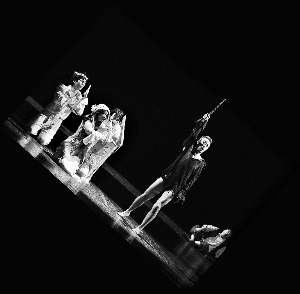
现场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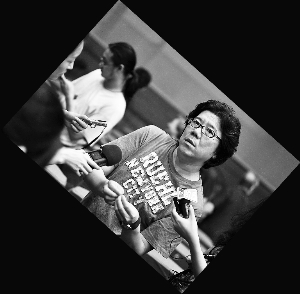
导演孟京辉
本报记者 于 雪
让400年前的堂吉诃德说着中文纵横驰骋,让塞万提斯这篇不朽之作被中国观众重新认识,这是孟京辉正在搞的大动作——今晚,话剧《堂吉诃德》即将在国家大剧院首次面见观众。9月10日至13日,该剧将南下深圳在少年宫剧场连演4天。本报记者应孟京辉工作室之邀,前往北京观看了该剧8月30日晚在中戏逸夫剧场的联排,并于31日在孟京辉导演的工作室与他进行了一番对话。
引诱观众“跑偏”
《文化广场》:《堂吉诃德》原来打算排成3小时45分,现在改成了2小时20分,听说你是忍痛割爱,把这样一部78万字的大部头改编成两三个小时的话剧是很困难的,为什么要挑这么高难度的?
孟京辉:我最初看这本小说是在大学的时候,当时看了不到一半就搁下了。前几年我又拣起来重读,十几章之后就完全读进去了,还没读完的时候我就决定要把这部小说排成话剧。《堂吉诃德》虽然是400年前写成的小说,但它具有强大的穿越时空的力量,书里面对疯狂与理想主义的解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构,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即便是现在的小说家也难以企及。而它的游历冒险的写作结构,它的形式感,我觉得比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国明清的小说也都要高明。尤其是下半部,那语言真是恣肆汪洋、翻江倒海、漂亮极了。
《文化广场》:看了彩排,感觉是刘晓晔扮演的桑丘跟原著中不太一样,好像还是《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的感觉。
孟京辉:我觉得这并不重要,比起堂吉诃德和桑丘的一路“打架”,我更看重的是他们两个人情感上的成长。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发掘出堂吉诃德性格上的很多方面,好玩的、可爱的,有时候他还装疯卖傻、抖小机灵,但我觉得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里,我们顾不了那么多,因此绝不能让堂吉诃德太丰富,太多元。桑丘也一样,有人也跟我说刘晓晔演得太游刃有余了,但我更看重他身上那种跟桑丘相似的沉着的气质。改编这么一个大部头,面面俱到肯定不可能,所以我必须割舍一些东西。
《文化广场》:既然不想表现堂吉诃德的丰富,那你想表现的是什么?
孟京辉:我最想让观众误解堂吉诃德(笑)。比如看到他种种疯狂的举动,可能有些观众就会认为这人怎么这样啊,这么傻啊,然后哈哈就笑。这其实是我一路在引诱观众“跑偏”,引诱大家去误解他,但到了最后,观众会恍然大悟,会为自己刚才的误解和笑而对堂吉诃德有一丝的内疚。这个内疚不是来自简单的情感上的误解,而是觉得其实我离他老先生挺远的,我并不理解他。
《文化广场》:剧中堂吉诃德的三大段独白,是不是你让观众内疚的三次提醒?
孟京辉:对。第一段独白是堂吉诃德对他心目中黄金时代的认识;第二段是他的内心追求以及他对骑士精神的理解;第三段是他在最后弥留之际对人生的反思,也可以把这段看作是他经历人生种种挫折后,与小说作者塞万提斯的一个心灵对话。我在这段的处理方法上,采用了一种布莱希特式的陌生感。
我坚信视觉引导创作
《文化广场》:堂吉诃德的第一段独白,关于“黄金时代”的那段特别让人感动,这是不是你刻意安排的对现实的投射?
孟京辉:没有。我会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两只狗的生活意见》里踏踏实实地投射,认认真真地嘲讽,而不会在《堂吉诃德》里为表现现实意义下功夫。我觉得现实意义是在心里的,不是说出来的,这里面的味道你品出来了,而一些人没品出来,没关系,可能是他一时感冒了,也可能是他暂时味觉不灵了。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那段黄金时代的独白,因为在那段里堂吉诃德描述出了自己认为的最美好的时代特征、社会良知的标准,非常美好,充满阳光。
《文化广场》:这次的音乐,让人感到相当精彩,听说用了很多当地的民乐。
孟京辉:这次的音乐都是我们从西班牙的拉曼却地区、加泰罗尼亚地区、安达卢西亚地区找来的当地的民歌,然后由吉他手阿兰现场用一把吉他弹出来,挺有西班牙风情的。在视觉效果上,我们分为舞台视觉和多媒体的影像视觉,影像视觉是王之纲做的,他除了用多媒体技术串联剧情,还加入了自己对堂吉诃德的情感。舞台视觉是由张武负责的,他做得既简练又充满创意,非常独特。我觉得视觉效果今后越来越会影响舞台创作。
《文化广场》:看彩排的第一感受是它的视觉效果做到了极致,虽然你一路以来都是以追求形式感为自己的风格,但会不会怕别人说这次孟京辉只剩下形式感而没有了内涵?
孟京辉:我就希望他们这么说(笑)。你说的特对,我一路以来就特别追求形式感,追求不同形式的创作方法。当然,我也有追求内涵的戏,不过这次排《堂吉诃德》不同,因为这部戏不用表现本身就已经充满了内涵和意义,因此表现形式感就格外重要了。
《文化广场》:对这次合作的演员有什么评价?
孟京辉:都挺好的。杨婷和韩青都是和我合作超过二十年的“老战士”了,可以说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体,郭涛和刘晓晔的配合也不错。(感觉彩排时郭涛有点紧)对,是我不让郭涛放出来的,你看到的彩排他也就发了50%的力,台词和激情都没有起来。因为彩排主要是做灯光、音响、舞美的调整,到国家大剧院和深圳公演时演员们的状态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