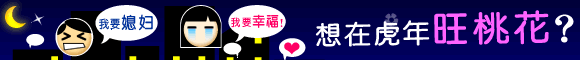“一切从零开始的”赖声川:创造戏剧的桃花源

赖声川
本报记者 端木复
他,络腮胡、长发、黑框眼镜,语速很慢,浓浓的“台湾腔”。
他,拥有独特的创意,不断追寻“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平衡。
他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使台湾相声起死回生。
他的《暗恋桃花源》,使无数青年男女为之痴迷,在上海也是久演不衰。
他每次带来的作品都与众不同,但全都叫好又叫座。似乎他与生俱来就有这个本事,能在不动声色间赢得市场,征服观众。
1月29日,我们在上海大剧院刚刚送走了他的那台让人边看边落泪的《宝岛一村》,2月4日又迎来了《他和他的两个老婆》。
他,就是被誉为“台湾现代剧场的创造者”和“亚洲剧场导演之翘楚”的赖声川。
一切从零开始的艺术家
赖声川,1954年生于美国华盛顿,是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戏剧博士,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
赖声川告诉记者,他年轻时喜欢画画玩音乐,又对文学有兴趣,1972年就读辅仁大学英语系,同时在台北一家餐厅从事民歌演唱和演奏,玩音乐玩了整整5年。1978年申请到美国读戏剧艺术,这对当时许多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决定,因为那时的中国台湾连剧场都没有,可谓是剧场沙漠,更少人有看戏的习惯。
赖声川回忆,30多年前赴美很贵,40元钱台币才可以换1元美金,但妈妈并不反对。他跟丁乃竺1978年7月结婚,9月到美国,10月存的钱被人盗了。本来可以在美国生活两年的,突然都没有了。幸好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一面打工一面读书,5年里在学校得了很多奖,导戏还得了一个学校最高奖。 1983年拿到了学位,由于成绩好,留美国是不成问题的。
赖声川说:“我为什么可以当导演,就因为那时我打过工、跑过堂。那是个五星级中餐厅,出入的都是有钱人,厨房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有大陆过去的红卫兵,有台湾留学生,还有美国土生土长的人,我有机会观看到很丰富的人性,这里面还有节奏感,5桌客人一起来怎么办?怎样做到让客人快点吃完走,又不觉得你在赶他?我学到在学堂上学不到的很多东西。 ”
当时赖声川收到了一封信,是台湾最重要的戏剧前辈姚一苇写来的,说想在台湾成立一个全新的“国立”艺术学院。 1983年,29岁的赖声川选择回台湾。他认为台湾没有剧场工业,这是一个机会,他想创造剧场,也创造观众。 “回去发现真的什么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连校舍都是跟人家借的。可从零开始有从零开始的乐趣,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就变成了可能性很大。 ”
相声剧融合曲艺与话剧
1984年,赖声川的第一部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在台湾上演,当时剧场里只有100多人。直到他采用中国传统的曲艺相声和舞台剧相结合的独创手法创作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才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赖声川说,在久违的老式相声茶楼里,看穿着长袍、摇着扇子的一胖一瘦两位演员闲言碎语、捧哏逗哏,一种快意与亲切油然而生。于是他灵感突发,创造了以相声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舞台剧,突破了常见说唱艺术的框架与格局,但又与传统相声一脉相承。
赖声川认为,相声剧与相声的不同,首先在它有明确的背景和完整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传统或者记忆消失的戏。它以两个主人邀请相声大师来说相声为引子,结果大师没来,他们只好自己假扮大师说相声,牵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消失进行反思。 ”
《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讲述了一个跨越百年时空的轮回故事。戏始于1900年的老北京,下半场则发生在20世纪末的台北,不论在哪里,两位落魄的相声演员总会遇到他们表演上的克星和令他们啼笑皆非的窘境,有点像现代寓言。 2005年的 《这一夜,Women说相声》中,赖声川首次让女人说相声,讲女性的话题,说女性的秘密,从美容、瘦身到恋爱病,女性成了相声剧的绝对主角。
据说,《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面世时,台湾人口只有2000万,但相声剧的磁带居然一下子就卖出了100万盒。有报纸称:“赖声川拯救了台湾相声。 ”
开创戏剧即兴创作方式
随后20多年里,赖声川创作了《遥远的星球一粒沙》等20多部脍炙人口的舞台剧。他曾两获台湾文艺大奖,也曾获选十大杰出青年。他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被评为台湾文学经典,电影《暗恋桃花源》获东京影展银樱奖、柏林影展卡里加里奖和金马奖,《如梦之梦》也获香港舞台剧最佳整体演出奖。由他开创的戏剧即兴创作方式也被广为传诵。
赖声川指出,戏剧的即兴创作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剧本的大纲和基本形式都在自己的脑子里,要时刻保留想法,见了演员后,让演员自己注入自己的角色,在那个角色中创造他所说的话,进而去体会作品。为此,他经常会给演员发很详细的大纲,并不刻意追求固定的细节和模式。像去年排演的《陪我看电视》就是他第一次用即兴方式在大陆排戏。
赖声川说,这种思维方式的养成是源于1983年回台湾任教后。当时那里还没有看戏和演戏的文化氛围,也没有专业的导演、编剧和演员,他们的学校也刚成立,一切都是新的。他一面教书,一面思考关于剧场的创作。那时,他面临两个选择:把美国整个的体系都拿到中国台湾来,包括制作,排戏的过程,这条路是容易的。二是非常不可测的一条路,即用集体即兴创作的方式来做戏,借助导演和演员之间的互动来提炼演员内在的真实感觉,让演员针对导演选择的题目提供自己的想法。这样的方法一直用到今天。
赖声川将这种集体即兴创作称之为 “论坛性”的功能。他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剧场就具有的功能。1984年初,他的第一部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在台北上演,有评论把它称为“一个新型剧场的诞生”。
有商业动机就不易出好戏
近年来两岸戏剧交流越来越频繁,《暗恋桃花源》在大陆演了数百场,还有《红色的天空》《他没有两个老婆》《这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一夜,WOMEN说相声》《如影随形》《宝岛一村》等,都大获成功,尝到甜头的赖声川由衷地说:“台湾导演来大陆还是来得太少,将来只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对台湾导演来说,台湾市场很小,不过我们有大陆的市场。 ”赖声川相信,大陆将为台湾导演带来大有作为的空间。当然,对一个导演而言,更重要的是大陆的观众,“你的作品,有更多观众来看,岂不是更好? ”
在美国出生的赖声川戴着眼镜,身上有着儒雅的气质。他说传统文化如同胶水黏合了分散在全球的中国人。他非常赞赏大陆能有如此好的演出创作环境,在目前全世界创作都处于低潮时,祖国大陆却始终能有比较固定的地方让艺术创作者进行创作,给热爱戏剧、热爱艺术的年轻人提供各种演出和交流的机会。
谈及大陆的话剧市场,赖声川觉得有点乱。 “太多人有投机的想法。当你的动机是商业时,就不太容易做出好戏。很多观众因为第一次看话剧就有被骗的感觉,便会对话剧产生误解。这样去做戏,无异是自杀。 ”
小有忧虑的他介绍:“台湾小剧场没有经历过被恶搞戏占据的阶段,即使在最繁荣的时候也都比较先锋。台湾的年轻导演之所以选择小剧场,是因为做实验戏剧的成本比较低,而不是为了赚钱,台湾观众也比较成熟。 ”对于大陆小剧场的乱,他相信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迷失,随着市场和观众的成熟会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