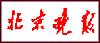李金斗掏心窝子盼出好作品 呼吁相声界要团结
 李金斗 资料图片
李金斗 资料图片
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人缘极好,因此被很多圈中人尊称一声“斗爷”。
“斗爷”也很低调,轻易不接受个人专访。认识他很多年,几乎都是为了曲协或中国广播艺术团以及各种纪念相声前辈的活动才会接受媒体采访。采访时他很少谈及个人,还经常叮嘱记者“千万少提我,都是大家的努力”。
9月7日,由李金斗和冯巩、巩汉林、金珠、赵炎、刘伟、刘全利、刘全和、付强、李伟建、武宾、贾玲(微博)等名家新秀共同主演的《越来越好相声小品新作品晚会》将在保利剧院上演。为了这台中国广播艺术团2011艺术周的重头节目等重要活动,“斗爷”才答应了记者的专访要求。
李金斗能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爱看《北京晚报》。他不仅对晚报的文娱报道十分关注,还特别喜欢看苏文洋的专栏。在他看来,那些深入民生、针砭时弊,文风犀利但又不失幽默和分寸的文章,其精彩程度绝不亚于最受老百姓欢迎的相声。“这些年,我们相声缺少好的新作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好作者太少。”听上去,“斗爷”似乎很期望,有一天苏文洋老师也能为相声创作做点贡献。
学艺艰辛曾改行到“全聚德”当厨师
记者:您最初是怎么走上相声这条艺术道路的呢?
李金斗:我从小失去父母,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家里很穷,上小学时喜欢踢球,但没钱买球。有个叫孙殿华的同学有足球,我就爱跟着他玩。他喜欢说相声,每次表演都让我给他当捧哏。有一天,他告诉我北京市曲艺团招收相声学员,让我陪他去考试,结果我考上了,他却没考上。但我奶奶反对我学相声,瞒着我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撕了。负责招生的赵振铎老师通过街道办事处找到了我家,跟我讲了很多进团说相声的好处,我被深深吸引了,于是成为了北京曲艺团当年最后一名入学的新生,从13岁开始坐科学相声。
张文顺是我同班大师哥,王谦祥、李增瑞也是我同学。我的班主任是侯宝林先生的大弟子贾振良;启蒙老师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王长友和谭伯儒先生;后来我又在王长友老师的支持下,拜了他的高徒、著名相声演员赵振铎为师,王长友老师就是我的师爷。他们都教了我太多太多东西,让我终身受益匪浅。1996年,我师傅赵振铎去世,因为他是回民,我披麻戴孝,给他在清真寺里操办了隆重的葬礼,当时我瘦了十几斤,每天都得吃救心丸。对我来说,师恩实在难忘啊!
记者:但听说您曾经也改过行,到“全聚德”当过厨师。
李金斗:“文革”时,我被下放到农村干校劳动改造挖防空洞好几年;等到“文革”后举办第一次全国曲艺调演,我看到其他演员大显身手,却看不到自己的相声事业前途,于是痛下决心改行,到“全聚德”烤鸭店学厨,苦练配菜切菜、颠勺炒菜。但我的心里还惦记着相声。有一次我拿到一个相声剧本《学徒》,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如何干一行爱一行,成为一名优秀厨师的,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于是,从“文革”开始后就再也没登过舞台的我,终于重返舞台说起了相声。
记者:最让大家难忘的就是您的相声《武松打虎》了。
李金斗:那是1985年,北京市决定要举行“首届中青年演员调演”,这是“文革”后二十年来的第一次文艺赛事,震动了当时文艺界。那时我正守在得了胃癌的养母身边,照顾她生活,是陈涌泉老师到医院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我当时38岁,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参加这次难得的演出,经过再三请求终于争取到了一个剧本,就是廉春明创作的《武松打虎》。为了说好这个相声,我和陈涌泉老师反复研究仔细琢磨,并且多次专门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家中向他求教。他给了我们很多非常有用的指点,帮助我们将京剧艺术糅到相声表演当中,丰富了演员的表演手段,使这段相声非常生动。我们还把传统相声中的醒木等技巧也糅到节目当中。结果《武松打虎》最终以新颖的形式、高难度的表演和巧妙犀利的内容,引起了轰动,剧场效果非常强烈,我也因此获得了“北京市首届中青年演员调演”曲艺组唯一一项“优秀表演奖”。后来我又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全国首届相声邀请赛,获得了逗哏一等奖;文化部“全国新曲目大奖赛”一等奖,被称为“三连冠”,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走出了事业的低谷。
周末相声俱乐部 20元票价8年没涨
记者:您一直都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人。之前几次采访您,您都是为了捧您的徒弟,比如付强、刘颖、方清平(微博)等。而且每次他们办专场,您都利用自己的关系给他们请来一批老前辈、老艺术家,为他们“众月捧星”,真是用心良苦!他们也都得了不少奖,好几个人都上了央视春晚,发展的都不错。
李金斗:他们能得奖,能获得成功,真得感谢周末相声俱乐部。这个平台给了他们很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得到很多的锻炼机会,也让很多观众因此认识了他们。周末相声俱乐部2003年成立,到今年已经8年了。我们一直是下基层演出,我们的口号就是:“给老百姓演出,为老百姓创作,让老百姓满意。”从当初我们一群专业相声演员创办这个俱乐部到今天,20元的票价从没涨过。我们几个轮流去攒底演出,我每月至少去演出一场,但从来没拿过一分钱,还经常往里花钱。今年是第八年了,我们希望能够总结一下,并且看看能不能推举出更年轻的周末相声俱乐部主席。包括北京曲协的主席也是一样,都需要有更年轻有为的人才来接班。这和我捧我所有的徒弟的心态一样,只要他们打算办专场,我就给你出钱出主意。都是希望年轻人能够早日拥有更广阔的舞台,不愿意让他们再经历我们年轻时吃的苦受的罪。
记者:创办青年相声节的初衷也是如此吧?
李金斗:是啊,这些青年相声演员,要是没人捧他们、支持他们,很难出来。所以我们希望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让一些有意思的青年相声演员能够有展示自己才能的地方,并且给他们一些说法,同时也让更多人认识他们,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我们每年还会在民族宫、音乐堂举办演出,每次都差不多会有众多前辈名家把一对年轻演员给捧红的。像我们9月7日在保利剧院的《越来越好相声小品新作品晚会》,也是既有名家也有新秀,要给年轻人更多的展示舞台。
记者:听说您还在北大讲过很多年相声课。
李金斗:是,当时北大开了曲艺课,汪景寿教授请我们去给学生们包括留学生讲曲艺。其实侯宝林、马季都到北大讲过课。我和陈涌泉也差不多在北大讲了十年的课。
说相声也要有责任感
相声界必须要内心团结
记者:那您认为现在的相声有什么问题呢?
李金斗:当年有人批评相声低迷、不景气,我说未必,相声是不断在向健康发展;如今,有人说相声繁荣了,我也觉得不能忽视它的问题。现在的相声比较混乱,有胡说八道的,有比较低级的,还有打严重“擦边球”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提出“反三俗”、“净化相声”。所以参加我们青年相声节的团队个人,都要遵守一定的协议。因为说相声也要有责任感,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记者:那年轻人要如何对待传统相声呢?
李金斗:传统相声必须要学,这是基础。郭德纲(微博)就很聪明也很用功,传统相声瓷实,能来“大活儿”,现在有几个年轻人能有他的功底?而且他确实培养了很多年轻人,让他们从传统相声基本功学起,这是对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学传统,不练基本功,以后会吃亏的。但是对传统相声,也要明白哪些可以说,哪些不应该说。现在有些表演为了讨到廉价的效果,为了讨掌声、笑声而信口开河,什么段子都说,这是不成的。以前相声界的老先生,很重视这其中的分寸,对我们的影响也很深。我们学徒时,老先生教给我们一些传统段子,同时也会明确告诉我们,有些是不能随便演出的。1961年,文艺界内部曾经办过一场挖掘传统相声的欣赏会,一台节目全是相声名家,包括侯宝林、刘宝瑞、赵振铎、王长友、谭伯儒等人,从下午1点半演到6点,效果非常好。当时我和王谦祥作为检场负责搬桌子,见证了当时演出的情况。但演出开场时就明确告诉大家,这台节目不能公开播出,是为了作为传统相声的资料保存的。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学相声的态度和您们当时有很大不同。
李金斗:用侯宝林先生的话来说,很多人的“老师”是“录老师”,都是跟着录音机、录像学的。现在还有“网老师”,就是跟着网络学。这样不行。一个是学不到真东西,另一个是“偷活儿”,不尊重别人的劳动和艺术。学相声不能跟着录音机、录像或者网络学,得到老师家里学。我还是非常欣赏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而且当年我们要去跟别的老师学习,师傅都会写字条儿和人家打招呼,这是规矩。现在很多事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没有五音,就难正六律。我13岁刚学相声,有一次演出自作主张说了段《卖布头》。下来后我师傅对我说:“谁让你演这个的?!这个‘活儿’你现在不能演,因为这是‘角儿’的‘活儿’。”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急于成名成角儿,自立门户。您怎么看?
李金斗:“角儿”毕竟是少数,一个团队中,“四梁四柱”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相声之所以有魅力,在于它是一个很个性化的艺术。一个人的待人接物和人品,都决定了他的艺术风格。相声没有派,没有什么马派、侯派,如果都是侯宝林,就没有侯宝林了。像侯宝林有一位弟子,学侯先生学得特像,人长得也精神,嗓子也好,动作也干净,但一上台准崴泥。就是因为他太像侯宝林了,观众都不是听相声了,精力全放在拿他和侯宝林作比较上了,但在大众心目中,侯宝林的艺术太深入人心了,都是“刻了板的文章”了,所以效果肯定不好。我教徒弟也得根据他们自己的个性风格来调教。
记者:您对相声界团结问题怎么看?
李金斗:相声界必须要团结,而且是内心的团结。当年相声界的老先生们,见面时互相不是说:“吃了吗?”而都是说:“爷们儿,有事吗?用‘活儿’吗?”“练什么‘活儿’呢?有什么我能帮你的说啊!”我师傅也教导我:“吃亏是福。”只有本着肯吃亏的心,才能团结;如果都想占便宜,是不可能团结的。 本报记者王润文图
(责编: 虫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