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忆症 蟒国》剧照
《失忆症 蟒国》剧照
新浪娱乐讯 6月16日至18日,蟒国剧团作品《失忆症·蟒国》将在正乙祠古戏楼演出。剧团导演针对“表演是什么”这个话题,从观念与技术的角度,对当下存在的几个表演误区作出了分析。
表演是什么?
李熟了
当我们谈论表演时,我们在谈些什么?
对于某些接触过专业术语的人而言,它是一种观念:“体验”、“表现”、“塑造人物”、“打破幻觉”等等;对于接受过系统训练的演员而言,它是一种技术:“规定情境”、“行动分析”,演员通过这些完成创作;对于影响后世的大师而言,它是超越戏剧的一种行为手段,用来完成社会批判,或者探索个人精神的终极。对“表演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同,从一开始就让创作者之间划清了界限。
把表演作为一种观念大肆谈论,这样的剧组屡见不鲜:导演告诉演员“要真实”或者“跳进跳出”,接着就要求演员实现自己的要求;剧组对观众宣称自己革新了表演理念打破了传统,然后给出一堆语焉不详的激情文字就此结束。把表演仅作为一种观念,至少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第一,表演观念如果没有具体的技术方法作为支撑,根本无法由演员实现;第二,真正的表演实践中,并不存在那么多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不同观念所追求的状态也往往是共存的。
前者以现实主义表演为例,不可能导演只告诉演员“去体验”,演员就能完成体验,导演需要提供给演员达到体验的手段。在斯坦尼体系的要求中,导演需要告诉演员作为角色的当下规定情境是什么,演员是具体哪一个规定情境没有抓住所以表演不够准确,角色的行动是什么,演员是否陷于于情绪而忘记了行动所以丢失了自己的人物。所谓“体验”这个看似观念性的要求,是由“从自我出发”、“假使”、“规定情境”、“行动分析”等一整套具体而系统的技术手段所支撑起来的。其他体系的表演同样如此。铃木忠志提出“文化就是身体”,是有完整的“铃木方法”训练作为依托;中国戏曲表演被认为“写意”,是以传承数百年的四功五法作为日常训练与评判标准。单纯谈论表演观念基本是毫无意义的。
表演实践中,将“写实——写意”、“体验——表现”之类的观念对立起来,为表演做粗暴的类型化区分,这种行为更是缺乏实践指导价值。以日本歌舞伎为例。日前刚在北京演出过的松竹大歌舞伎《恋飞脚大和往来》一剧中,主演四代目中村雁治郎所扮演的忠兵卫既真实感人,又充满东亚传统表演的程式化美感。一方面,演员在内心上几乎完全成为了人物,细节动作、面部表演准确动人,外部肢体动作都经过了固定化和一定程度的夸张,并且有一些明显程式化的动作,与生活状态拉开了距离。这种表演如果非要用二元对立的观念去归类,显然任何分类是不够准确的,不同观念在演员身上达到了共存。
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影响后世的经典观念都有着完整的技术作为支撑,换句话说,都是“美学观”和“方法论”的完整整体,而美学观与方法论一方面共生,一方面也是可以分离的。譬如斯坦尼体系作为演员创造角色的手段,在最初与现实主义美学捆绑,但是发展到今天,完全脱离现实主义美学,体系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共通性的技术去指导演员,可以说,只要你的剧本有人物、有角色,体系作为创造角色的方法就对你(演员)有用,甚至没有角色,你也逃不脱体系“注意力集中”、“松弛”的要求。不同的技术依靠着相应的观念而产生,又和这些观念分离,对于演员来说,将不同体系的技术同时用于自身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
将表演仅视为观念,固然缺乏实践价值,但将表演仅视为技术,同样不是什么好的态度。大概是由于空谈观念的论调太多,有些具备技术的创作者会倾向与将观念与技术对立起来,排斥谈论观念,而认为专心研磨技术便能呈现最好的作品。但技术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绝对客观的东西,它倾向于提供永恒不变的绝对原理,并不会自我更新和推进。单纯醉心技术同样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技术必将僵化;第二,表演成为单纯的艺术行为,和社会与历史被彻底割离开来。
技术的僵化并不难理解。50年代的中国话剧,以北京人艺为代表,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表演风格,这套风格是现实主义为美学追求,以演员相应的技术手段为方法,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到了80年代之后,创作者们不满于戏剧舞台的单一化,开始抨击这种传统,尤其抨击它的僵化。而时至今日,不少国有院团的大型剧目,明明表演已经看似打破了现实主义,心理时空、与观众直接交流等手段频繁出现,却依然给人腐朽陈旧的感觉,其原因何在?就在于美学观虽然改变,但僵化的表演技术却依然被沿用,导演和演员并没有找到适应新美学的新的表演技术。美学会随着时代自我革新,而技术并不会,技术是必须人为的、极其有意识的去推进和改变它的。
表演与社会、历史的割裂则是更大的问题。许多创作者都将表演看成单纯的演员完成舞台作品的行为,将表演的意义局限于戏剧艺术领域。如果将表演仅看做技术,这也是必然结果。但对于影响后世的大师们而言,表演的意义是超越戏剧的,而正是依托这个更高的超出戏剧领域着眼点,他们才创造出了作用于戏剧领域的最具体的、持续作用于后世的表演技术。
还是以斯坦尼体系为例。尽管“斯坦尼体系等于写实”已经成为一种很难根除的经典误解与偏见,但前文已经提到,体系产生时期的写实美学观和演员创造角色的技术手段是可以分离的。事实上,如果深入观察,就会发现体系即便在追求上也远不止是写实这么简单,而是甚至超出戏剧领域的。铃木忠志在论述契诃夫时认为,契诃夫的现实主义并不是要提供给观众一个还原生活的场景,而是随着以荣格心理分析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在20世纪初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希望以潜台词为手段,描写出日常生活并不会明显彰显的人类实际的、有别于日常的深层心理活动。众所周知,斯坦尼体系的产生是与契诃夫剧本的最初排演共同完成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追求和契诃夫一样,也是希望通过对演员创造角色这一过程的研究,去发现人类心理和行为的产生机制,去探索更深层次的问题:人类的想法是如何形成的?人类的行为是如何导致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思索,产生了“规定情境”、“行动分析”这样的技术,去让演员在舞台上,完整还原一个虚构的人类角色产生自己行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才是斯坦尼所谓的“真实”。
斯坦尼将表演的探索延伸到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探索中去,从而产生具体的表演技术,使得表演不单是一种技术,而且与社会勾连起来,表演成为人类认知自己的手段之一,同时这种认知方式也是与当时的历史思潮有关的。上世纪60年代,格洛托夫斯基开始自己的创作,在西方,格氏被认为是斯坦尼的真正继承者。而格氏的创作美学、格氏的“神圣演员”奇斯拉克所运用的表演技术,都与斯坦尼有着不小差距,这种“继承”的定位从何而来呢?一方面,斯坦尼的一些具体技术在格式这里得到发扬,另一方面,格洛托夫斯基从“贫困戏剧”到“艺乘”的过程,正是研究重心不断转向对个体精神终极探索的过程,在研究思路上是斯坦尼真正的继承和后续。对于这些大师而言,表演从来都是与社会历史紧密相关的。
除去从斯坦尼到格洛托夫斯基这一脉以表演研究为手段,不断探索人类内心世界的传统,在东亚,还有着铃木忠志这样借助表演研究,发现表演的社会批判意义,用演员身体去批判社会的传统。出于篇幅限制,我会在其他文章中详说,这里就不赘述了。
表演决不能空谈观念,表演也不能抱死技术。但是,面对这个时代的创作者,同样不能不痛不痒的批评一句“有观念的没技术,有技术的没观念”,就把自己高高挂起,仿佛戏剧的全球危机和僵化都与自己无关,高处不胜寒。只有在实践中奋力向前探索,革新自己的观念,创造自己的技术,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行为。
“当代表演”的困局,正在于在革新观念与创造技术之间的不平衡。这样的表演我们在近年中国舞台引进的欧洲剧目里也见到不少了。打破旧美学,创造新表演,当然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必须做的,但是提出新的表演美学之后,我们能提供多少具体技术,来让自己提出的新美学有着坚实支撑呢?对于作为观念的表演美学而言,支撑它的具体表演技术的丰富与完整程度,就决定了这种美学的成立程度。创作团队提出一种表演美学,如果能创造出相应的完整技术手段,而且让技术手段与社会时代相关联,这个观念与技术的结合体就可以被称之为“方法”;而提出观念,实现观念的技术手段不仅完整而且丰富,从内部心理技术到外部形体技术无一不包,同时观念在深层次与时代的终极问题不可分割,这样的观念与技术的结合体就可以被称之为“体系”。“当代表演”的问题就在于,它提出了观念,支撑观念的技术也存在,但这种技术单薄且琐碎,不成系统而又数量不足,最重要的,它的观念受时代所限制、所奴役,而不是向时代发问。
创造新的表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能够在观念与技术上同时往前迈进,同时不放弃对时代的思考,是我们剧团的追求。这次我们创作的《失忆症·蟒国》,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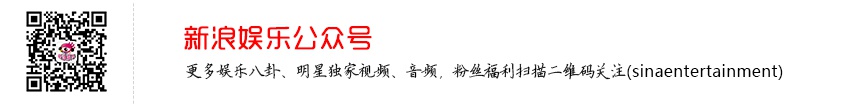































































































 网友偶遇黄晓明baby
网友偶遇黄晓明baby 伊能静儿子正面照曝光
伊能静儿子正面照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