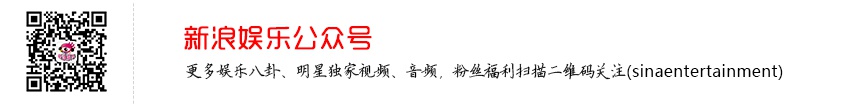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失忆症·蟒国》(剧组供图)
《失忆症·蟒国》(剧组供图)
按:蟒国剧团作品《失忆症·蟒国》将于6月16日起在正乙祠古戏楼进行二轮演出,面对当下剧场文学性缺失的情况,剧团导演与编剧分别从结构和语言的角度提出的剧团作品的追求。
“文学性”的回归
——蟒国剧团
为什么要在今天的中国剧场里重提“文学性”?
“文学性”正成为剧场里的稀有事物。从戏剧市场上讲,“日常叙事”已经成为题材中的主流——以日常语言作为剧本台词,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他们的情感状态或生活方式做出有限的思考。主流题材的单一化使得“文学性”的方向也变得狭窄。书面化和有韵律感的语言、想象力飞扬的非现实故事、丰富而与主题阐释相扣的结构,等等这些在今天的剧场空间都在被逐步压缩。
另一方面,欧洲当代戏剧从理论到演出的大量引入,也培养起了一批将之奉为圭臬的拥趸。在这样的戏剧观念中,文本与身体对立,从剧本出发来谈论戏剧是旧的、腐朽的代表,打破剧本中心才是戏剧的出路。以此作为前沿,“文学性”从创作开始之前就已经是被否定的对象,连存在的价值都应当被质疑。但是,如果中国戏曲为比较对象,我们就能发现它的问题。在戏曲里,文本与身体从来就不是对立的概念。剧本的文学与演员的身体这两方面,对于创作者而言一向是并重的,对于观众来说也是共同欣赏的。戏曲中从来不存在剧本中心,何来打破?在中国戏剧中将两者对立起来,只是让创作理念变得粗暴和狭隘。
在今天的剧场里谈“文学性”,不是想要脱离现实,也不是提倡文本中心。它只是我们自古以来的创作传统和观看传统,从不曾断绝。而关于“文学性”,以我们剧团自己的作品《失忆症·蟒国》为例,结构与语言是我们这篇文章想要先谈论的两个方面。
剧本结构分析
——蟒国剧团导演:李熟了
作为导演,去分析剧本的结构时,值得观察的内容很多。以《失忆症·蟒国》的上半部《失忆症》为例:时空间、线索、节奏、叙事方式,每一个环节的改变都会让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当这些部分统一一致时,结构就会在功能上让剧作整体的表达得到强化。
《失忆症》讲述人类从几百年的荒凉大旱过渡到几百年的大雨滂沱,身体在不同的时代随着环境发生不同的变化。面对横跨数百年的剧情,剧作首先做的是把仅有半小时的演出,进一步切割成了六场。六场戏在时间与空间上来回跳跃,如果按照时间线索排列,六场戏的顺序是这样的:2——4——5——3——1——6。其中在第四场里,又包含了一个小的套层结构,将三、四两场不同时间点上的场景叠加在一起。这种跳跃结构增加了叙事的复杂度,从而赋予作品形式感。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场次间是跳跃衔接,在线索上不具备连贯性,场次间的时间差异感被进一步突出,故事中纵深数百年的洪荒感也从而得以强化。
在复杂化时空间顺序后,剧作又在线索上将故事清晰化,提供给读者/观众进入作品的通道。全剧来回跳跃的六场,实际上可分为两条并行的故事线:大雨年代少爷与医生二人间的诊断故事,大旱年代囚犯家族几代人间的继承故事。两条线索将全部场次串联起来,观众则会随着剧情的深入,依照各人理解能力的不同,在不同场次通过隐埋的暗示发现两条线索间的关联。而在全剧末尾,两条线索合二为一,真相大白。
两条线索间的不同节奏,则成为结构与主题进行关联的手段。在少爷与医生的线索中,三场剧情集中发生在一周之内,矛盾集中在人物关系上;而囚犯家族的线索中,三场剧情跨越数百年,故事集中讲述家族人物的演进历史。如此,作品对细小的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和宏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个体变化,两者都分别给予了关注,并且相互参照,以完整的角度让作品的批判性主题得到更全面的阐释。
最后,两条线索分别采用了代言体(即人物对话)和叙事体作为主要的书写形式。代言体在舞台时间上推进的缓慢、在心理细节上展示的充分,这些特点都与第一条线索以展示个体间关系发展为主的内容相一致;叙事体述说故事的自由与浪漫特性,则提供给第二条线索时间大幅跨越的便利,和在叙述大雨大旱、人类身体变化这些情境时想象力飞驰的空间。
剧本下半部《蟒国》在结构上比《失忆症》要单纯很多,但也是有着深厚传统的。剧本的六场戏实际上正好与日本能剧的“序破急”三段式结构相吻合。能剧中,“序”是缓慢的开场,“破”是繁复的展开,“急”是迅速达到高潮并在高潮处收尾。《蟒国》在故事上以将军与老翁相遇的剧情开场,随后老翁讲述出的农夫与蛇的故事则成为剧本篇幅主要部分,戏中戏在最后部分迅速升温完结,并推动剧情回到将军与老翁的场景,在几分钟内到达顶点并立刻结束。我完全依据“序破急”的顺序处理了每个场次的节奏变化,同时,在能剧表演中,演员动作的复杂程度也会随着“序——破——急”的顺序每部分依次加强,这种表演处理也被借鉴到了《蟒国》的表演中,使得表演也出现了强烈的结构性,并与剧作相一致。
分析剧本结构,是导演的前期工作之一。“文学性”强烈的剧本提供出考究的结构,是给予了导演有趣的创作课题,让导演真正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关于剧本语言的运用
——蟒国剧团编剧沈诗奴
剧本上下两部在“文学性”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失忆症》更重于结构,《蟒国》则在语言上探索更多。
《失忆症》以“隐喻”为主要手法,描写不存在的世界与彻底虚构的故事,相应的,语言方面使用了偏书面化的现代语言。这种选择涉及到了创作者对于虚构背景的态度:在虚构的极端情境下,语言的使用要与日常的语言方式形成距离,它并不追求所谓自然的口语。剧本的当下与历史两条线索中,当下线的对话采用潜台词丰富的、带有部分书面表达的口语;而历史线涉及到讲述,要将虚构背景的洪荒感加强,则以偏诗意化的语言为主。
相较于情节完全虚构的《失忆症》,《蟒国》有它的原型故事“农夫与蛇”。原型故事的广泛基础决定了观众在观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公共性,所以《蟒国》并不像《失忆症》一样将主题埋藏在隐喻之下。《蟒国》采用东亚戏剧传统结构,原型故事与传统结构的结合,吻合了东亚观众的审美习惯,在理解故事上更加容易,语言运用也自然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观众的共鸣不再是创作的诉求,《蟒国》采用古白话写作,加入大量韵文,古今汉语的断裂,使得这种语言的运用造成天然的陌生化效果。同时,这种语言的选择又强调了汉语本身的音乐性和韵律美:楔子部分作为从案头文本到舞台台本的过度,采用韵文描画大量意象来绘制出一个虚构的蟒国世界,短句长句的交替使用强调了语言的节奏感。正文部分则又在描绘不同时空时,为区别人物不同身份也采用了两种风格的古白话,这种赋予变化性的语言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文本华丽繁复的美学追求。
《蟒国》文本的形式本身带有创作者对于文本的立场。在西方社会由现代转向后现代的同时,理性的危机直接表现为文本的危机。由批判文本中心地位来达到批判理性主义的目的,是建立在西方戏剧一直以文本为中心的审美习惯上。源自柏拉图主义的理性主义对于理念、逻辑的重视让戏剧文本成为了西方戏剧的核心。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新古典主义以后,文本的核心地位越来越被凸显。这样来看,就需要正视一个问题:成熟资本主义时期的理性危机是否波及到了我们的社会。那么更进一步需要阐明的是,东亚戏剧的审美丰富性决定了它的文本性只是审美的一个方面,歌舞伎能剧等日本传统艺能主要是身体性传统,而我国戏曲一直将文本性与身体性并重。在东亚戏剧美学土壤下产生的文本,从来不需要顶着专制的罪名去为理性危机献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