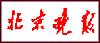刘恒:给人艺大戏《窝头会馆》写剧本太值了

刘恒

《窝头会馆》剧照
今晚,连续一个多月、场场爆满的人艺大戏《窝头会馆》将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落下帷幕。这部由刘恒编剧,林兆华导演,何冰、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徐帆主演的话剧,自9月25日到11月8日的每晚演出,票房火爆,一票难求。票房收入超过一千多万元,打破了人艺的纪录。观众慕名而来,满意而去。
第一轮演出结束,编剧刘恒怎样看待自己一炮打响的话剧处女作?怎样评价合作的导演、演员?剧本演出后有哪些遗憾与思考?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刘恒先生。
观众观感
谭利华:
我是慕名来看戏的。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话剧。没想到话剧的力量这么大。看完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致很晚不能入睡。
李咏:看了这个剧,就一个字:“好”!俩字“都好”!
所有台词都好,我都不敢走神。一走神,一句话就过去了。剧中北京话那个劲儿,非常好。这个剧极有可能成为他们人艺今后的保留剧目,一年排一遍。
李青:
《窝头会馆》表现了人生的困境和命运的怪圈。让我想起高尔基的《在底层》和《小市民》。如果绝望到无奈,变革与新生就会成为时代的必然。“窝头”是一部艺术地诠释了时代变迁的好戏。
唐师曾:
《窝头会馆》是当今娱乐泛滥大潮中罕见的、有历史意义的巨作。那句“我儿子是修铁路的,我要去新中国”的台词,让我泪流满面。
王干:
看了《窝头会馆》之后,两晚没睡好,一直在脑子里过剧中人物命运集。此话剧集鲁迅老舍一身,汇华老栓和祥子一体。当代经典,茶馆续编人艺新技。我还想再看几次,再想想,笑声和泪水如此苦涩地融合,让人灵魂折了似的。 X017
连看了五场 给自己挑毛病
记者:《窝头会馆》吸引人的亮点很多,精彩的语言,含蓄的主题,悲喜情绪的起伏,让观众一下记住了舞台上那几张生动的面孔。观众在肯定刘恒话剧处女作的成功,肯定这部戏“很人艺”的同时,也在情不自禁地和人艺的经典《茶馆》相比较。可《茶馆》是经年累月一遍遍打磨出来的,您觉得这么比公平吗?
刘恒:没什么不公平。看戏的一上来就拿这个跟《茶馆》比,高低都是瞧得起我。打个比方,要是有人拿我跟莎士比亚比,说我不如莎士比亚,还不得乐死我?我的东西就是一窝头,再怎么比,再怎么打磨,哪天真的掉在经典的大筐里了,它也还是一窝头。当然,窝头也有窝头的梦想。虽说都是黄颜色儿吧,往上走能是金子,往下走却是臭狗屎了。我梦想这窝头是金子做的,拿什么抹它臭它都不碍事,真有那份儿造化它迟早会发出光来。
记者:第一轮演出今天结束了,您怎么评价自己的话剧处女作?
刘恒:我对它评价一般,也就是差强人意吧。首演之后,我连看了五场,躲在剧院不同的位置,老忍不住给自己挑毛病。后来就不想看了,越挑毛病越难受,弄得自己很沮丧。其实,我的写作笔记里有许多自我挑剔的文字,近乎自虐,已经养成毛病了。
记者:我听说你认为剧本仅仅及格,是真实想法吗?您到底给自己打多少分?
刘恒:说它及格有自谦的意思,也有自我激励的意思。我当着演职员说过,我给剧本打80分,给导演和演员打90分,给运筹帷幄的指挥者打100分。这件事从酝酿到收获,张和平院长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的统筹能力和驾驭能力近乎完美,给他满分是最恰当的评价。我跟林兆华导演以前没合作过,别人叫他大导我也稀里糊涂跟着叫,今天我明白这“大”兴许就有伟大的意思。舞台千头万绪,到处是障碍,包括看不见的障碍,有前人留下的,也有自己竖的。我目睹了林先生披荆斩棘的过程,他对舞台全局的掌控令人钦佩。
剧本对得起人家,可人家加倍地报答了我
记者:您怎么评价这些演员呢?我发现台上所有人的表演都很投入,迸发了一种艺术的陶醉感,把观众一下子带进去了,剧场效果好得惊人。您觉得意外吗?
刘恒:我预想结果会很好,却没想到会这么好。我不管别人感觉怎么样,反正我是被感动了。我觉得给这帮家伙写剧本太值了!首演的时候,我凑在演员堆儿里跟着谢幕,他们那种眼神儿让我终生难忘。里面有喜悦,还有纯真,热乎乎什么都有。一方面是为艺术而献身,有点儿悲壮,一方面又从观众那里得到报偿,像孩子一样快乐,从两方面来的幸福感在人生中真是不多见!他们也觉得值了吧?我觉得剧本对得起人家,可人家加倍地报答了我,我只能说这是彼此的缘分了。我还想给他们写戏,哪怕写砸了也在所不惜。
记者:您能不能说说具体评价?我的同事有的喜欢何冰,有的喜欢宋丹丹和濮存昕,您呢?哪个演员给您的印象最深?
刘恒:我哪个也不得罪!我都喜欢(笑)。宋丹丹一直夸剧本,走到哪儿夸到哪儿,还拽着老公一块儿夸。我还没吃透剧本的优劣,虚荣心倒抢先得到满足了。但是我必须说,她对剧本的理解,让我有知音之感。我精心观察她在台上的一举一动,说句肉麻的吧,她对表演层次和强度的控制显示了天才的力量。何冰也好,你要说他是人艺一根台柱子,恐怕没人说他不是。他已然戳在那儿,生了根儿了,谁也推不倒他了。濮存昕给人的惊喜最多。我明明知道他下一句说什么台词,可只要他一张嘴,我就跟着观众笑翻了。那种骨子里的魅力是与生俱来的吗?我觉得八成是。杨立新和徐帆也好,有的朋友给杨立新嘎嘣脆的表演排第一,有的把徐帆的气韵摆到最前边去……总之,各有各的好,台前台后都好,凑成了整个人艺的好。戏在台上一旦活起来,那感觉真的是好啊!我有两回坐在二楼的边座上看戏,除了演员的动静,整个剧场鸦雀无声。艺术的美是什么?一伸手就摸到了。
记者:您在某个场合曾经说过,窝头就等于金木水火土加棒子面再加厨子。棒子面是素材,厨子是艺术家,这都容易理解,金木水火土是什么意思呢?
刘恒:这更好理解,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金就是铁锅,木就是笼屉,水是开水,火是灶火,土就是长老玉米的庄稼地……窝头不就是这么蒸出来的吗?一部戏就是一个系统,五行缺一不可,编剧没有理由夸大自己的作用。所谓一剧之本,可以是根本的本,也可以不是。剧本是路线图,但是路线图不能代替长征,在路线图和目的地之间,有许多人付出了心血。我将怀着谦卑之心,向身前身后的诸位致敬。
跟以往慢悠悠相比,快节奏或许是新创造
记者:有个看过戏的朋友说还要再看一次。因为台词量太大,演员语速也快,有的话来不及反应就过去了。身为北京人的她,一再表示是自己对老北京方言以及老北京风俗的贮备不够。但我感到其实这也代表了一种意见。对此,您是怎么考虑的?
刘恒:我经验不足,写台词写上了瘾就不管不顾了,单一角色在单一时间中的台词量往往过于膨胀,给表演出了不少难题。好在林导和演员在节奏上做了处理,效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语速确实快,但是不妨碍台词的生动性,只是有的词汇语音含混,某些重要信息被遮蔽了。如果你们认为有问题,根源在我这儿。不过,跟以往老北京剧目那种慢悠悠的拿捏相比,这回呼噜呼噜吃面条儿的快节奏,算不算林导的新创造?是不是一种别致的风格呢?这个问题,你得容我跟林导再探讨一下。
记者:采访您之前,跟几位同行和观众交谈过,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认为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在第三幕表现得最充分。结尾苑国钟临死之前那段独白很感人。但是,他那句“我儿子是修铁路的”,“我要去新中国”,之后伴有新生婴儿的啼哭声,象征着新中国的来临,这一笔让人感觉有些生硬,您觉得呢?
刘恒:苑国钟的儿子读的是铁道学院,确实是修铁道的。因为前边的戏把“铁道学院”给删了,所以后边儿再说那些话就显得矫情了。我得争取把删了的恢复一下试试。苑国钟弥留之际说的是“我儿子想去新中国”,于实于虚似乎都还说得过去。只有那位新生的婴儿,的的确确缺少新意,跟他有一拼的只剩下从东边升起来的大太阳了。但是,太阳天天升起,人人生下来就哭,彼此雷同得要命,乏味得要命,却也毫无办法。我和张院长曾经长时间讨论,这孩子生不生?后来一想,漫漫人际非生即死,无路可去,爱怎怎,生就生了吧!
票房一千多万 都是真金白银
记者:第一轮演出从9月25日到11月8日,听说票房一千多万,打破了人艺的纪录。这里面有泡沫没有?
刘恒:张院长是一丝不苟的人,哪怕有一点儿泡沫他也不会答应。据我所知,那都是真金白银,是实打实拼出来的货色。票房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票房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这个戏在观众那里找到共鸣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别的追求吗?还有别的更有意义的奖赏吗?没有了。知足了。反正我是知足了。
记者:我能感到您的满足,可是您不可能没有遗憾吧?关于这个剧,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们很想知道,读者和观众也一定想知道……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刘恒:最大的遗憾,是不知道自己的不足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应该怎样克服它。自己的小说和电影有问题,我会掌握个八九不离十,话剧不行!我是真的外行,是真的小学生,需要人来指点。但是没有人来细致地指点你。有人可能是不屑,有人是给你留面子,有人很可能是自己也没弄明白。
总之,夜半临深池,你得自己摸索着往前走。人都是自以为是的,也都喜欢听好话,人家挑剔你,你也未必听得进去。网上有个把骂你的,说你是个大笨蛋,连话剧的主线是什么都不知道,居然还敢写戏。人家骂得也没什么不对,等你想往下听听这戏到底该拿什么当主线,他又一个字都不肯说了。可也是呀,你又没付钱,人家凭什么告诉你真理,还教给你长本事?就算你付了钱,人家也未必告诉你底细,他得给自己留着写戏使吧?我的遗憾就在这里,骂人的未必是行家,可真正的行家是不教人的。那些奇妙的路数,全得靠自己一点儿一点儿去摸索了。我希望自己好运,还能写出好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