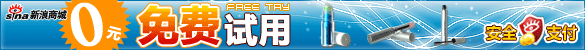|
不支持Flash
|
|
|
自杀的心脏:法斯宾德和德国新电影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09日20:13 环球银幕
 法斯宾德从不忌讳死亡 1986年6月10日凌晨三点,女演员朱莉安-罗伦兹回到公寓,听到隔壁的房间中传出了电视机的声音,却听不到导演法斯宾德惯有的鼾声。虽然法斯宾德很忌讳别人不经允许进入他的房间,罗伦兹还是走了进去,只见法斯宾德赤身躺在床上,已经气绝,嘴里还叼着一颗香烟。就像他最后一个爱的男人阿敏-梅耶尔那样,在极乐的梦中死去了。 法斯宾德死于慢性自杀——他的生活就是一个慢性自杀的过程:长时间毫无节制的工作、暴饮暴食、大量吸烟、过度酗酒、糜乱的双性生活,超量毒品、安眠药、兴奋剂。法斯宾德一生保持着对自己身体持续的摧残。 对于法斯宾德的离去,德国人遗憾地说,我们的心脏死了。 不合时宜者 直到现在也很难理解,为什么道德自律性极强的德国人会如此推崇这么样一位不合时宜的无耻之徒。别人把法斯宾德看成70年代“德国新电影”的心脏,可他从不为别人的要求或者期待而活。每天,他带领他的“反戏剧剧团”在极其简陋的布景里工作,每部电影拍摄不超过15天,在大赚一笔之后就是暴发户式的挥霍,以至于死后没有任何身家。他曾经明确表示不拍艺术片,但他的电影也完全不像好莱坞,他勾画出一个充斥着外籍劳工、失婚女人、势利小市民和谋杀者的下层社会图景,令人齿寒,就像他过的狼狈不堪的日子,没有半点崇高可言。  因为表现了二战中女性的悲惨命运,《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和《莉莉-玛莲》成了法斯宾德最被主流社会称颂的两部电影,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就很热血了——作为“德国新电影”里唯一出生于战后的导演,他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有一部代表着“德国新电影”政治立场的集锦片《德国之秋》(Deutschland im Herbst),讲述左派恐怖分子的三个主要头领于1977年在监狱自杀,很多导演都面对镜头表达了严肃的观点。而法斯宾德似乎对于生活琐事更感兴趣,短片里讲述了他和母亲的关系,以及如何对情人阿敏-梅耶尔发脾气。 拜倒在SM狂人脚下 法斯宾德是一个公认的施虐/受虐(SM)狂人。由于童年时期遭受了被戕害式的孤独和母亲的忽略,他长大后就变本加厉地予以报复,电影就成了他这种情绪的产物。在《佩特拉-冯-康特的苦泪》里,女秘书玛琳爱慕着女设计师佩特拉-冯-康特,默默地为她操持着从工作到生活的一切。但佩特拉从未把她当成一回事。佩特拉的女儿问妈妈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坏,佩特拉回答:“因为她并不值得我对她好,而且这就是她需要的方式。”法斯宾德的母亲安妮塔隐约记得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她总在儿子的影片里出现,其实后来发现那都是些被讽刺的角色。 法斯宾德这样的性格也交不到什么朋友,他的情人、仰慕者和同流者都被他招至“反戏剧剧团”,一直陪伴在他左右。虽然在戏里戏外都遭受他的随意拼凑和摆弄,却一直对相貌丑陋的法斯宾德保持着难解的倾慕,唯一的解释——这群人都是“受虐狂”。法斯宾德已经把萨德—波德莱尔的SM理论发扬广大,用他和他的电影重新定义:虐待,童年时代缺失爱的孩子在长大后企图吸引别人关注的一种极端方式。 这种方式首先表现为残酷。法斯宾德认为“残酷是一种屈从于需要的严格纪律”。他也不相信爱情:“爱情是一种最精良、最狡猾也最有效的社会压迫工具”。其实这些早就都写在他的第一个剧本《水深火热》里(2003年法国人奥桑把它拍成了电影),法斯宾德的所有电影,大多围绕这样剥削式的残酷之爱展开。《狐狸和他的朋友们》里,中了头等彩票的外来务工人员获得了富家少爷的爱情,其实后者是想用这笔钱发展自己的印刷厂;《四季商人》里,丈夫只有决定不再推着货车叫卖,成为在贸易市场摆摊的小业主时,妻子才会更看得起他。 法斯宾德是一个貌似残暴的胖子,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将施虐者的身份迅速转化为受虐者。在惹怒别人后,他喜欢花大手笔哄人高兴;他把一切都做到极致,比如高效率的多产(在17年电影生涯中里拍了摄了41部影片,编导、演出了27出舞台剧),这些都是他自虐心态的表现。而这些又不可避免地与他的性倾向有关,据他的编剧罗兰-史特-拉伯说,法斯宾德“内心女性的成分远远超过他男性的本性”。这种内心的柔弱表现在电影里,就是一些最令人绝望的女性命运。《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现在看来集所有女性虐恋惨剧桥段之大全:丈夫上前线,为了等待丈夫归来无奈出卖肉体,为了丈夫错手杀死情人,丈夫归家后要把她转手给老板以换取前途。最终,玛丽娅-布劳恩选择了一种最具决绝的方式,以开煤气的方式与丈夫同归于尽。爆炸的烟火中闪过了一系列西德历史事件的新闻片段,令人马上对一个所谓的崭新时代产生怀疑。  法斯宾德的电影神经质、敏感、错乱、完全不道德。他受室内剧电影的严重影响,场景简单,制作粗陋;他所信奉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总是用不和谐的镜头提醒观众记得自己的身份,干预和削弱入戏的效果……但是,种种因素都不会影响德国人对他的爱。因为,他那种傲慢的施虐/受虐的性格完全属于德国人,而他同时具有的男性的膨胀和女性的隐忍,也赋予他一种令人拜倒的情感虐待力,把观众玩弄于股掌之上。 人们眼中的法斯宾德,就像他最后一部电影《水手奎莱尔》中那样。奎莱尔冷漠地对待、欺骗甚至杀死他身边的人,但是人们还会不由自主地去爱他。因为他就是那么邪恶。 真死了吗? 一般人认为,当法斯宾德的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就宣布了“新德国电影”的死亡。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德国电影”还活着。一方面,它是公认的最通俗的欧洲艺术电影支系,《铁皮鼓》、《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等经典作品,并不被人当作艺术片而供之于高阁以至遗忘;另一方面,“新德国电影”的几大重要人物还都处在创作旺盛期。维姆?文德斯很早就从德国走向了世界,通过《得克萨斯州的巴黎》到《柏林苍穹下》,再度开拓了公路片关于行走者的含义;赫尔佐格也完全身居海外,把目光转向了记录各种虽死不悔的探险者,《白钻石》讲述热气球专家的生涯,《灰熊人》(灰熊人吧)则是一个动物保护者与野生熊类共居的岁月。 维姆-文德斯和赫尔佐格已经不属于德国,这一切在他们出名的那天就已经注定;施隆多夫留在柏林教书、搞研究,偶尔拍电影,超然化外;人们常常叹息法斯宾德的英年早逝,如果他活着又会怎么样呢?当80年代来临,一个属于艺术电影的好时候又已经结束,快乐到死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至少他可以像自己说的那样,“死亡时才能得到真正得到休息”。 德国新电影 意大利现代主义和法国的新浪潮都在非自觉中产生,“德国新电影”更像是一个政治运动。它有确切的时间地点——1962年2月28日的奥伯豪森,确切的口号——“创立德国新电影”,以及写满数页纸的《奥伯豪森宣言》,并且取得了官方资金支持。它的延续的时间也 最长,从宣言开始到法斯宾德“心脏”的死亡,整整20年的时间。 作为二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新电影”的导演们始终在独裁和反独裁的怪圈里挣扎。面对全民的低落和国土的分离,一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失败的沮丧命运常常成为他们的主题。他们吸收了民族电影的精华——室内剧电影、让-玛丽?斯特劳布的极简主义,尤其是30年代的“表现主义”。“表现主义”以舞台化的夸张光影和扭曲、怪异的意像,营造感官刺激,以心理的恐惧感为美;而“新德国电影”则把这些心理化的感觉放大到具体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中,客观地呈现狂热的背后,是痛苦的思索。 关于“新德国电影”的导演们,有一个经典的比喻体系:  1962年,他带领一群短片导演发起了“青年德国电影”,使德国电影赶上了欧洲现代主义电影的脚步。他的代表作《告别昨天》以一个年轻女孩的遭遇来控诉社会,曾获得柏林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吧)金熊奖。但是从整个电影运动来看,他作为一个旗手的意义更大一些。  在施隆多夫的所有电影中,你可以看到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时空如何延伸。作为一个充满责任的历史学者,他的电影是讽刺的史诗。《铁皮鼓》里,一只马头被从大海里打捞上来,无数的寄居蟹从中爬出,小主人公奥斯卡(奥斯卡吧)的母亲随即呕吐……这象征着德国人已经受够了腐朽的第三帝国思想,更涵概了人类对于未来社会肌体异化现象的反应。  这位公路片大师从一开始坚持“边走边看”的态度。他早期的“公路三部曲”(《爱丽丝漫游城市》《错误的运动》《时间的流程》)呈现了城镇生活中一些看似平凡的奇异图景,缓慢而优雅地剖析了美国文化对于德国社会的影响。  在电影里,他总是近乎变态地去世界各地实现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蛮荒腹地建立文明或者陆上行舟,坚韧到偏执……影片里的狂想历险者就是他的化身。另一方面,他喜欢畸形者的表现主义主题,如《上帝为众人,众人反为自己》,人们想方设法把一个智障改造成文明人,未遂后又残忍地将他遗弃、杀死,充斥着专制社会不可言说的虚伪与阴怖。 心脏 赖纳-维纳-法斯宾德 ……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