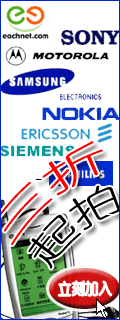如果说电影是导演与公众对话的载体的话,那么即将上映的《周渔的火车》则为孙周提供了继《漂亮妈妈》后再次向大众敞开心扉的契机。虽然“火车”已被媒体预热得似有疾驰而来之势,三位主演巩俐、梁家辉、孙红雷更是相继摆开阵势迎接着接踵而来的记者,但当记者日前见到导演孙周时,他却仍在为影片的最后修改挑灯夜战。虽然用电影与公众对话是导演的职责,但这种方式似乎并不直接,于是有了下面这组孙周与公众的“直接”对话。
评论家说,北村是一个用心灵写作,并视写作为生命的纯文学作家,他有着一般作家所缺乏的超前性与前瞻性,如果你爱过,他的小说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共鸣;如果你还没有爱过,它将教你如何去爱。从他塑造的各色人物的灵魂,你可以看到他们悲剧性的命运,而这些人物的悲剧又都是灵魂的悲剧。孙周说,我与北村开始就很有默契,我很喜欢他这个人,他的小说就像酵母,给了我一个可以重新去培育一些东西的土壤,我们修改剧本的那个过程仿佛是一个与心灵对话的过程。
如果大家看过小说,那么再看这个电影肯定会失望的,小说就像酵母,给我一个土壤,重新去培育一些东西,我与北村开始就很有默契,我很喜欢他这个人。我一直想拍一部很个人化,很纯粹,但却能与心灵沟通的作品。说实话,这部电影我是命题作业,目的很明确,就是给巩俐拍的。小说的确很有意思,但男人的立场不是我想要的,后来我与北村联系,问他可不可以改,而且不用急于给我答复,我给了他三天的时间,三天后他给我回信说应该可以。但真正开始工作时却遇到很大困难,第一稿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当北村改到第四稿时,我们都近乎崩溃了,好像钻进了死胡同,我甚至一直在追问自己……这种状况持续了近六个月。并非作品本身不好,只是没有回答我想追问的东西,但突然有一天,我好像开悟了,写了大纲之后,找到了一位女性作家来改,最后我差不多写了十几稿,那是一个与心灵对话的过程。
巩俐说,《周渔的火车》很时尚。
孙红雷说,影片中的一些手法可能观众一时无法接受。
孙周说,观众看到的时候,我已经改变很多了,而且是根据市场做了调整。如果说时尚那可能是因为我在影片中使用了运动的拍摄方式,因为爱本身就是运动的。
观众看到的时候,我已经改变很多了,而且是根据市场做了调整。说实话,我很陶醉于自己这部电影的第一稿,风格化很强,很个人化,拍电影其实是很任性的。但投资人不干,拍了这么多年电影,我已经很成熟了,能够坦然面对,并将矛盾化解。应该承认这个世界的物化既是好的也是悲剧,就如同世界需要F4这样的小伙子,需要他们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一样。如果说时尚那可能是因为我在影片中使用了运动的拍摄方式,因为爱本身就是运动的,人的本性与文明本身既和谐又冲突,这个悖论是很难调节的。爱是活跃的、运动的,爱情中不如意要比如意来得多,人们对爱情有幻想,这份幻想其实是蛮珍贵的。拍这部电影是当时拍《漂亮妈妈》时就与巩俐约定好的。拍电影是不能勉强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不会哗众取宠,为几亿人拍电影的气魄我没有,我的电影都是有感而发,虽然我也希望自己是周星驰。我不变态,我情理通达,我想我的电影是会有人喜欢的。另外,虽然希区柯克、昆汀都对电影语言贡献很大,新浪潮那批都是如此。但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很善于使用电影语言的人,虽然电影史上也有纯电影的尝试,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载体。
记者问,从《心香》到《漂亮妈妈》,再到《周渔的火车》,您始终不曾脱离女性题材,这种题材的一脉相承是刻意的吗?
孙周说,近几年,中国女性群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自我有了明晰的确认,欲望和幻想有了具体的行为,这种现状的改变让我感动,这种历史转型期普通女性身上的变化是值得记录的,而这也正是我的电影的一个情感来源。
近几年,中国女性群落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性的地位已不再为政治所利用,对自我有了明晰的确认,欲望和幻想有了具体的行为,这种现状的改变让我感动,这种历史转型期普通女性身上的变化是值得记录的,而这也正是我的电影的一个情感来源。我以往的影片,《给咖啡加点糖》、《心香》、《漂亮妈妈》也正是记录了不同时期女性的生存状态,我自己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变迁的历史,记录这个变化很重要。但我有一个企图,就是以女性的角度来看女性,这样会令我的视野变得更立体。一个男人不可能不热爱女人,无论妈妈,姐姐,抑或生活中的女人……每个女人都给我很多,女人的伟大不是没有理由的,她们的经历让我有创作的冲动和欲望,我希望观众在荧屏前看到这些女人时,能够找到自己曾经历的感动,而引起共鸣,并且为这些女人精彩而平凡的生命鼓掌、喝彩。捕捉中国这些年来变化对女人生命的影响,传统和现代的精神在她们身上印下的痕迹,我想表现在这种时代的撞击下女人的命运。
观众说,10年的广告生涯让孙周在商业大潮中已无法左右自己,向市场妥协的无奈更是无法回避,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扪心自问了。
孙周说,其实所有艺术门类都应一起追问艺术与灵魂的真正关系究竟是什么,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是该迎合还是该反对,对此我没有自己的理论,一切都在颠覆,我不清楚自己。
拍完《心香》后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我没做电影,个中的辛苦很多,个性、关心、选择与社会的冲突不言而喻,直到凯歌和巩俐找我出来拍戏我才又回到了电影。我也为在这个时代中能否左右自己而困惑,我们这个时代的导演应该思考一下,我们的作品是否能表达自己,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是物化的,良好的物质条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舒适,这既是好的一面,但也有其悲剧性的一面。物质生活渗透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同时精神也为之物化,在如今不少青年导演依然为纯电影的尝试做着努力,而这对于我来说已显得幼稚,表达自己的方式很多,我也要考虑我的作品投资人是不是满意。电影人应探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艺术,在这个时代中找寻自己所属的位置,创作也会更加主动,有利于我们作品的创作。其实所有艺术门类都应一起追问艺术与灵魂的真正关系究竟是什么,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是该迎合还是该反对,对此我没有自己的理论,一切都在颠覆,我不清楚自己。(李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