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这个让人凌乱的世界 是默奉的圭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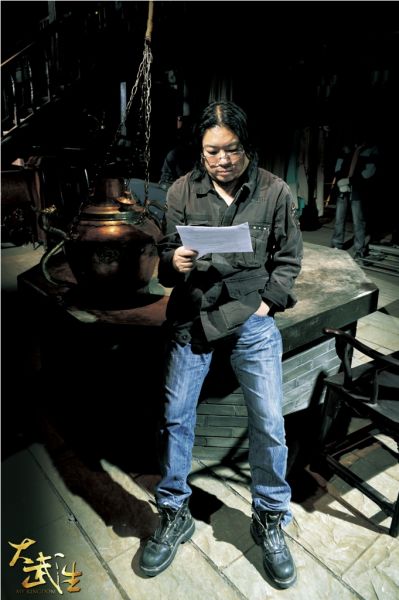 高晓松认真研读剧本
高晓松认真研读剧本
 高晓松片场凡事亲力亲为
高晓松片场凡事亲力亲为
BQ=《北京青年》周刊
G=高晓松
一,这个让人凌乱的世界,“运作与搞掂”成了PR们默奉的圭臬。没有辩解,没有推诿,老老实实认罪,恭恭敬敬道歉反而挽救了高晓松因“酒驾”而陷入的舆论风暴眼。高晓松在堪破“聪明误”后,又将如何打发这六个月,180天的牢狱生活?人身失去自由,心灵飞越羁押,他在里面的所思所得是什么?且听夫子自道。
BQ:2002年,《青春无悔》再版,你在序言中写道“我知道人注定会被生活打败,我知道从37岁到43岁我会左遮右挡陷入苦战;从47岁到53岁我会平静缴械回到被人供养的童年;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看爱恨,诗酒余生。”此番系狱,似乎应验了你的预测。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在事故发生后,你在车内想了什么?此次撞车,对你而言似乎像是“神启”,你接受命运的安排为何如此安之若素?你如何安排在狱中的生活?对于电影后期的烂尾,你如何补救作为导演的担当?
G:我既不是冤案,更不是革命烈士,甚至犯的罪都是低智商低技术笨罪,坐的牢也没啥特别,与万千囚徒一样乏善可陈,生活上没啥好说的,就当穿越回从前过一过父辈清贫清淡清净的日子。不说生活,说说工作和学习吧。
《大武生》后期做完了我才回的洛杉矶,没什么烂尾的问题。就是一点奉旨修改和主题歌的事。服刑犯人可以合法写信打磁卡电话,所以没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宣传,我5月9号那天回国就是准备开始宣传,结果下飞机当天就住进了这里。幸好负责宣传的杜扬多年前就是华谊兄弟的宣传总监,资历深经验够,和我又是多年挚友,也是我下部电影的制片人,她的全力以赴加上演员们的年轻和热情,更有从不爱做宣传的洪金宝大哥也破例带队征战,勉力支撑。我少年入行,二十年来交得一干好朋友,大家平时相望于江湖,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我在各个工作领域救急善后的颇有几个,宣传上也会有大家并肩周旋。剩下的就听天命吧。希望你在杂志出版前看看这部电影,因为我不能说“这是一部好电影”,但你看了,相信你会说。
几年前看过一个纽约犹太人写的《大英百科狂想曲》,把他读大英百科的心得写得幽默睿智,觉得很爽。再加上他说读这套书需要两年,很能修身养性,因此一直有咬牙一读的想法。只是名利场让人凌乱,日日为浮云奔波,本以为这个愿望和我一直想翻译一本小说一样,要到60岁退休才能实现。这回本打算把书运进来,没想到在看守所总共不足千本书的小小阅览室里赫然发现没开封一整套!这是否是你说的“神启”?!
《大英百科》不分类,从A到Z按头文字排序,文史哲理工医混在一起,很有新鲜感,有点像北京人说的“溜缝儿”,把各种知识和常识之间的缝隙各种弥补。我现在才看到B字头,主要是A打头的皇帝国王公爵伯爵们太多了(大英百科不收录足球明星,老贵族们却一个不落),很占篇幅。记笔记也已用光了一根笔芯(里面只允许用笔芯)。
《大英百科》提前18年开看,翻译小说的愿望也开始涌动。咨询了好朋友冯唐,他推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我翻成《昔年种柳》),读了很喜欢,虽然是英译本(马大师用西班牙文写字),但很能感受马大师的魔幻文风,夏日悠长,也就动手翻起来。诚惶诚恐,字斟句酌,不知不觉又一顿菜汤馒头来也。
BQ:很多了不起的人都在监狱中获得生命的升华,比如曼德拉。在11月前的服刑期间,你有何规划或打算?在封闭的空间里,人的思维反而活跃起来,对于人生的终极问题,比如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及人的根本困境等问题,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感悟?
下个电影本来是这个夏天拍,现在泡汤了也好,剧本可以像《大武生》一样踏踏实实改几稿。
我开始写一个诗集,暂时叫《纪传体》。原因是人安静下来后,慢慢想起许多今生只见过一两面的人。有的说过话,甚至发生过什么,有的仅仅在旅路中擦肩而过,听见片言只语,目击浮光掠影。原以为这些都已沉默进人烟人海,没想到坐在木板上竟能一一浮现。于是以几行诗为他们立传。如年轻时的狐狸一路上撒尿标记以为自己还会回来,等老了蜷伏于远方某地,想一想那些不靠谱的足迹。
我现在的遗憾:一是没能看见女儿从三岁半到四岁的成长,那是人间每个父亲万金不换的幸福。二是没能看见一位位观众走出电影院的表情,那是每个立志为观众拍电影的导演的幸福。不过这个还好,还有下次。
至于人生的终极意义,区区几个月Behind the bars(这个比“坐牢”好听,呵呵)恐怕不能妄谈。你说的那些伟大的大师即使不坐牢也能洞穿迷墙,我辈关一辈子坐穿牢底恐怕也只能坐井观天。我只是池中物,有天能上岸看看,已很知足。
二,也许你现在还对《那时花开》里的作为模特的人偶不时出现而不明所以,也许你没有忘记《我心飞翔》里陈道明率领地队伍攻城拔寨就像是戏台上的“三五人千军万马,七八步万水千山”。这些“表现主义手法的腾挪”显然不是拍给大众看的。一个如此文艺的导演,怎么敢去拍商业片?拐点且听高晓松的分解:
BQ:围绕你的第三部电影有两个说法,一是在博客上你曾公布自己“下一部”将讲述佛学,而现在成型的《大武生》,你曾说这源自七年前的构思。我很想知道你在2005年《我心飞翔》后,对电影的认识有何变化?
G:03年拍完《我心飞翔》,去印度待了一阵,清空自己。当时花钱请了个印度佛学教授陪着我,每天坐而论道。某天忽有感,写了个小活佛和小女孩两世交错轮回擦肩而过的故事。回来后发现宗教题材不宜拍摄,于是放弃了。
那时继续导演广告谋生,二勇(《阳光灿烂的日子》《孔雀》制片人)帮我做制片。拍完三星打印机广告,为谢他辛苦请他去巴黎。晚上在巴黎蒙马特山顶第一次给二勇讲了这个故事,在山下怎么想出这个主意已经忘了。当时叫《武舞倾城》。那时的故事还是个艺术片结构,讲的是女扮男装演男旦的女子和武生的绝望故事,几乎全是文戏。当时二勇很喜欢,每次见到我都鼓励我写,我就开始写。
06年通过面试为一家好莱坞小电影公司导演了一部小成本电影,剧本是人家的,我收到导演合约后一个月就开机了,没权力改剧本,又没有终剪权,拍完交活完事,老美表示还挺满意。但我不认为那是我的第三部电影,就像我完全按照企业要求给人家写的企业歌我不认为是我的音乐作品一样。这次经历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开始接触了那边的电影观念和制作流程,二是下决心在洛杉矶定居(之前因为妈妈在美国,所以一直两边跑),从头开始,在好莱坞闯闯。
在美国很努力写了七八个故事,大部分自己写,有两个美国本土故事找美国编剧合写的,到处Pitch stories。认识了一些制片人,有大有小,他们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要求我讲故事的时候不许讲“我要如何如何,我怎么怎么感觉”,而要说“观众会看到什么什么,观众会怎样怎样反应”,主语从“我”变成“观众”。二是不约而同地指出我从前几部电影共同的优缺点,优点仅仅是“知道摄影机该摆在哪”,缺点是一部电影里想说得太多太急并且“畏惧高潮,耍小聪明”。
几年下来,给人做过编剧,做过东方题材电影的历史顾问,更多的是抓住每个业内老战士学习。从工会+保险的好莱坞基础制度到制片公司立项红绿灯系统,以及剧本量化评分指标。从人物模式到故事套路,好莱坞几乎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大家讲得如出一辙。不像在纽约,人人都云山雾罩,以个性之名行实验之实,以对艺术负责之名行对金钱不负责任之实——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并且曾深以为荣。所以说到这儿,你可以说我已经被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洗了脑,我觉得有可能,但要我自己说,是在平和平等平静的西岸待久了,回首在北京文艺圈的全部成长,认识到那些顾影自怜的“艺术”其实来自于急躁放大的匮乏感,一旦匮乏感消失,那些永恒的意义在哪里呢?含泪在凄冷窗户纸上捅几个洞很容易,但如果有了玻璃窗和温暖,人们就不孤单了吗?
BQ:《大武生》的故事构架的主线是复仇,你选用了普罗普功能说里经典的“英雄叙事”框架,蒙难、出走,学艺、出山、复仇;在人物关系上延续了“一女侍二夫”的三角关系,大S的设置非常像好莱坞电影中传统的“美女蛇”……这些商业片的元素,是在你当初构思故事时既定的吗?你同编剧邹静之,制片人摩根间有没有就此做过博弈?这一过程中,你坚持了什么,妥协了什么?
G:到了07年初,在李瑞环的公子李振福家里聚会时,给大家讲了这个故事。李家是京剧大票友,听了这个故事很激动,于是请来了头牌大编剧邹静之操刀。我和邹老师从前不认识,第一次见面就讲故事,幸运的是邹老师也是一位大票友,对梨园掌故如数家珍。接下来的日子,我和邹老师多次在清华东门外的一间咖啡馆畅谈。邹老师用了一年时间,前后写了四稿,为这个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邹静之老师给我的印象是“绵绵不绝”。和他聊剧本我可以天马行空,无论我提出什么狗血想法,邹老师都能圆其说,尽其意。招儿之多,底儿之深,让身为导演者自由驰骋。当然了,邹老师是标准中国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基因与生俱来,他又是京剧大票友,对梨园真实感有迫切追求。因此结构上虽然已经如商业电影般紧凑,但内容还是有很多艺术片的不甘。
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在洛杉矶多次找著名制片人Andre Morgan摩根(《百万美元宝贝》《投名状》《如果爱》《门徒》制片人)谈,他开始认为京剧题材没有卖点,及至读了剧本,兴趣大增。我俩在贝佛利山一处有泳池的庭院里畅谈了无数次,改了很多稿。他要求我按好莱坞规矩画分镜头剧本。我又用了半年时间请好莱坞一位日裔美籍分镜画师和我一起画了详细分镜画稿。摩根仔细看了之后,说你可以导演这部戏了,同时他也正式决定担任《大武生》制片人,并且从海外带来占总投资三分之一的不分账资金,极大减低了国内投资的风险,最终导致这个投资巨大的动作片顺利上马。
09年4月,摩根和我带着剧本和分镜画稿一起回国。摩根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去横店见洪金宝大哥。当时洪大哥正在拍《狄仁杰》。我从没见过洪大哥,摩根把我介绍给洪大哥五分钟后就离开横店回上海了。临走告诉我,我能打动集京剧童子功和电影大武指于一身的洪大哥来做《大武生》的动作导演,就是这个戏能开拍的前提。
我在横店陪洪大哥在现场拍了三天戏,学习武戏拍法,并且见缝插针和洪大哥谈《大武生》剧本。洪大哥给剧本的第一个意见是:武戏不能只要结果,谁赢谁输,谁死谁活不是武戏的要点。武戏是人和人在打,人是什么性格?有着什么信仰?为着什么而战?打的过程中展现什么样的人性?推进什么样的情节?这些才是动作导演最关心的!作为导演,永远不能只把两页纸扔给动作导演,说“怎么打漂亮怎么来”。我听出了一身冷汗。当夜无眠,用了一夜时间把武戏部分全部改写。第二天早晨在洪大哥出工的车边站着读了一遍修改的内容。洪大哥表情开始柔和,又和我在拍戏现场聊了一些细节。过了两天,摩根同志打电话给我,说:祝贺你,你的戏成了!
最精彩的是围观邹老师和洪金宝大哥,制片人摩根讨论剧本。洪大哥大开大阖,一派少林硬功夫,邹老师太极如意,悠长如武当绵掌,老摩根有板有眼,以标准好莱坞回合一拳拳打出,如身经百战拳击高手。三位老师傅三种武功各展所长,我坐在那努力把三派内功在自己经络里融合,有时痛苦,有时走火入魔,有时全身通泰。我之前拍的几部电影都是自己胡练的邪派武功,这次才真正体会到章法与经验带给一部大片的精气神。
每一代华人导演都有自己的武侠梦,她的核心始终是:用最勇敢的方式单枪匹马与不仁义的世界、与不仁义的人、与自己内心不仁义的一面战斗(所谓好莱坞电影三大矛盾: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己)。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长环境和审美参照。作为我这一代人,同时深受东方儒家平衡仁爱和西方追求真理的熏陶,既尊重东方克己复礼的传统,又向往西方以人为本的精神。因此我们这代人拍的武侠动作片,注定会以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受迫于环境传统和情感的悲剧为题。解题的办法有两种:在生活的自由中绽放凋零,或者在生命的自然中获得平静。《大武生》选择了后者——每个人的生活都失败了,但生命在彻悟中胜利了。应该说全片虽然秉持了好莱坞电影的标准结构,但是终点还是回到了东方式的Norm(Norm这个词我觉得英汉字典翻的不够准确可也想不出怎么翻更好,我一直觉得它是东方文化的关键词,就像Truth是西方文化的关键词)。
整个剧本里,我最满意的是“席木兰”这个女主角。她突破了传统武侠片里女主角千人一面的“从一而终”、“单纯不谙世事”“闯祸”的模式,她自由、成熟、勇敢面对人生的所有故事与事故,面对无一可以托付的四个男人,面对凌乱的爱与别离,坦然坚定,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无论爱恨,男人都是客人,无论年纪,男人都是孩子。这个人物其实就是今天的现代女性。把她放到民国上海的背景中绽放,是我在几乎所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想清楚地知道她到底爱谁以及爱的原因——坚持下来的,我坚持女人不应该知道这两件事。我有我内心深处不能磨灭的情愫:男人柔软,女人坚强。所以在我的电影里,《那时花开》是一个女人选择两个男人,《我心飞翔》是一个女人选择三个男人,《大武生》是一个女人选择四个男人。所以在这部戏里,我向好莱坞的男人标准(英雄与信仰)做了妥协,但坚持了我对女人的看法。
我们四位主创在互相妥协融合的基础上,各自坚持了一点:摩根按照好莱坞动作片标准,坚持在“谁干的?”和“怎么干?”之间只能选择一个展开,不能贪多兼顾两样。我们最终选择了一个发力,舍弃了另一个。邹静之老师坚持了梨园的韵味和美感。洪金宝大哥坚持了男人英雄。我坚持了女人强大。最后我想说,全体中外投资人坚持了给够预算,保证了影片呈现的品质。
三,业内人士曾分析姜文首部商业电影《让子弹飞》何以开创票房奇迹,一个细节是姜文对每个场面拍摄前都画了分镜图(尽管得很潦草),而由此爆出的现象则令人哑然:国内很多匆匆上马的电影,很多都没有这道工序!作为两位在气质做派上类似的导演,高晓松这次商业片拍摄上表现出对好莱坞专业主义的全面贴靠。怎么看待这个转变,且听高晓松的分解:
BQ:摩根透漏了一个细节:你在洛杉矶和一位好莱坞分镜画师工作了半年,画了全片一千五百个分镜头。这个功课能否展示一下?据我所知,国内很多所谓大片并没有强调这一流程。通过这次国际合作,结合你之前对国内电影制作水准的了解,你看到的差距或不同是什么?同时,我非常好奇,你过往行事风格的我行我素以及对艺术诉求的极端自我,如何让你把自己划入到这样一个条分缕析科层制化得国际团队之中?
G:好莱坞制片人们面对全世界各种类型各种脾气的导演,自然有克制导演个性(你说的“本我”)又不磨灭才华之道。我觉得他们有这么几招:
一是人性上观察你,看你才华个性和成熟懂事之间的平衡感,有才但偏激的人会被建议去纽约当Film Guerrilla拍Namby pamby(我翻成“为赋新词强说愁”)电影,无才且偏激的人会被建议改行。所以摩根逼我先后改了三十一稿剧本,改到第15稿他挑不出毛病又觉得还能更好(这是制片人最大的痛苦),于是就发出那稿剧本询了一圈演员价钱。收到报价后他告诉我:所有要演X角色的演员都打了七八折,所有要演Y角色的演员都涨了百分之三五十。为什么此消彼长?因为X角色写的好,Y角色没写好不吸引演员。所以给我改Y角色!
剧本改到每个角色都吸引演员打折了,又要求我画全本分镜头画稿,最后开拍前还要我用分镜画稿做了动画Teaser视频,配了音乐,让我剪接并反复让我修改。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折磨,确定我可以驾驭,愿意妥协,并且还有一些小聪明用来灵活坚持(这个他们很看重),才最后决定交给我拍。
二是法律上控制全部版权,签署好几十页的美国导演工会标准合同(我上部电影也签的这合同),用各种法律条款在争执不下时让你就范。三是制作上给你配备老少兼备的团队,既有经验老道的大佬把关,比如洪金宝大哥,英国金牌剪接和澳大利亚资深混录师,平均年龄56岁,防止我四处飘逸(摩根每周都会对我说“Fuck your PiaoYi”)。又有前卫时尚的年轻人比如纽约回来的服装造型指导Gino只有28岁,和年轻的美术指导帮我摆脱武侠片传统的“西红柿炒鸡蛋”色彩,营造全片冷色调、皮质感的氛围。
摩根开拍前三天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你和Sammo(洪金宝的英文名)搭班子?我说因为我的风格偏Cool,洪大哥偏Hot,你想要一部有许多Hot高潮的Cool电影。说来说去,最重要的只有一点——极端自我天马行空和团队合作按规矩办之间最大的区别是“谁是老板”。依靠导演们进化是违反进化论的,只有依靠制度。
BQ:从文化比较视野的角度,电影中出现了由京剧这一媒材相互观照的京沪比较,有中国视野和西方制造的双重对接,关于这一文化产品的气质,您如何来界定描述?
G:我觉得中西对接首先是内在心灵的,其次才是外在形式的。
内在的刚才已经说了很多,摩根是个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他大学学的就是中国历史,从李小龙时代就在香港做电影,十几年后才回到好莱坞。我可以勉强算是个了解西方的中国人,不光是表面了解。我在美国时为了能写美国本土戏,了解美国的大众心理,不但按照制片人们要求仔细读了圣经(好莱坞经典故事的核心其实大量是现代版圣经故事),而且还仔细读了美国中学语文课本,因为大学各学各的专业,中学可是每个人学的一样,塑造出的集体无意识和民族价值观(英雄观爱情观)就是大多数观众的取向。所以在内心上我们已经融合,不需要“对接”。
外在形式上,我尽力突出西方的元素,弱化中国元素。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是这样发挥的:不是你血里流的东西(西方元素)你再努力突出也会打折扣,是你的东西(中国元素)你无论怎么弱化都会处处流露,弥漫于无形。所以此消彼长,最终呈现的样子会是中西平衡的。做流行音乐也是这个道理。
近些年好莱坞电影明显向冷色调,酷造型发展。因此在《大武生》里,我们坚定地追求了冷色调、酷造型。坚决抛弃了传统民国片里上海的旧中国风貌,集中展现上海西方租界的西式元素,以冷色调铅灰色欧洲城市为样板设置场景,展示当时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的西化和时尚。甚至两场激情戏都设置在欧式街头轿车里和堆满橡木桶的红酒窖里。
服装造型更是极尽炫酷皮草冷色风格,由纽约学成来大陆的时装设计师Gino操刀,片中男女主角的皮草时装以今天角度看都堪称时尚,混搭些复古民国元素,穿在帅哥美女身上,站在冷色调背景的旧欧洲场景里,不应该说很西化,而是很西化的上海人最爱说的——很洋。
这部戏与其说是民国戏,不如说是民国上海西洋租界戏,或者我在极端情况下对主创们说的“就当发生在欧洲唐人街”。与传统民国片在视觉上有很大的不同。
BQ:看到了您在狱中谱写的《如梦令》,风格和您最近的《彼得堡遗书》、《杀了她喂猪》截然两判,当然这可能归因于商业电影的要求,但是否可以视作您在创作上的一次回归,对校园民谣风格的重拾?
G: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彼得堡遗书》、《杀了她喂猪》都是从乐器和设备里长出的音乐。我在里面没琴没设备,只能从心里长出音符,所以只能是民谣。
四,从“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老爷子曾在《人间词话》曾如此概括茫茫人生路的进阶。而从“清华三年,生活就是弹琴、打架、踢球”的莽撞少年,到把对投资人每一分钱负责挂在嘴边的商业片导演。已过“知天命”的高晓松,演绎的是否就是人生的必然?“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答案并不在风中飘。
BQ:什么促使你在自己两部电影后,做出了这么大的改变,从文艺片毅然转向商业制作?是书生的憋屈与自尊,抑或资本的诱惑?一个同商业时代格格不入的游吟诗人如何秉持了新的游戏规则?你是如何把天性中的本我和社会赋予的自我协调?讲故事,讲这五年的经历。特别是四十岁后,你如何看待所谓的“知天命”。
G:我过了用显微镜放大自己细微伤口的年纪,又有了家小,对他人的责任感排了很久的队终于排到了自己的孤独感前面,于是对好莱坞的为每个观众而不是只为自己的共识越来越认同。
我做音乐也好,拍电影也好,都是对“艺”的兴趣比“术”大。或者说在“说什么”和“怎么说”这俩问题上,我更喜欢研习后者。我从小一帆风顺,投对了胎、上对了学、入对了行、娶对了婆、生对了娃,所以虽然读书不少,又走遍世界,但是对人和世界的深处始终缺乏了解和敬畏,缺少勇气和坚毅的精神,只是对各种雕虫小技兴趣浓厚。空明和空虚乍一看长得很像,其实每个读书人自己心里清楚。
我三十岁前已经努力体会了各种音乐电影文学大师们三十岁前的伟大作品,那时已经认定自己绝非大师品种。那之后出国也是觉得自己深度肯定没戏了,想从广度上找吧找吧,或者万一逢到奇缘能拧巴拧巴更好。当然走了一圈下来发现还是国内最拧巴,北京就是奇缘呵呵。
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发现“不惑”不是什么都明白了的意思,而是不想明白了,糊涂着挺好。有关艺术电影是不是除了“教堂倒了,人们孤独”就没啥可说的了,已经不愿去主动寻找。四十岁已经过了向生活找茬儿的年纪,而是坐等生活来找茬儿,护住家园,处变不惊,目击流逝,别无他求。
有了这个心态,就可以用第三人称,以更久远的角度写东西了,比如《万物生》,比如《彼得堡遗书》,比如《大武生》。离开了第一人称,也就离开了所谓“本我”和“作者”的感性坚持。剩下的坚持就是理性的坚持,理性的坚持其实就是商业电影的原则。不多设一个符号人物,不多写一场闲情闲戏,对Money Shots(卖点)不节约一分钱,对无动机的虚妄审美不多花一分钱。
我曾经憎恨或鄙视或发誓永不妥协而现在欣然接受的,不光是商业艺术,还有生活的许多。比如对美国、对乡愁、对父亲,比如对爱与等待,岁月和我自己。
我不是游吟诗人,我是随遇而安的游子。
BQ:前两次电影宣发的时候,你接受采访,面对记者,丝毫不讳言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现在你还这么想吗?或者说,对于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如何自处,你又有何新的想法?
G:我依然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我觉得一个人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并且这个审美是从书本中先验来的,这个人就是知识分子。具体到我,如同在艺术上“艺”强“术”弱,在知识上我也是“知”强“识”弱。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还是只有艺之知,没有术之识——只得皮毛。
至于知识分子如何在这个时代自处?我觉得这个时代与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的无大师时代没什么分别——大师扎堆抱团同去同去,政治军事文学艺术,来时如春之怒放,去时无一株残留。人类已经习惯了,下一个怒放期必然会来。我们这代人目睹过上一拨大师的背影,被灿若星河的灯塔们照亮过海面,已经知道要去何方,已经足够幸运。至于到中国,也没有什么与世界不同,既不是世界的宠儿,也不是世界的孤儿,中国人快乐的悲伤的麻木的比例,对知识分子的消费能力,以及无大师时代必然的平庸,与美国也无二致。可能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的时代绝望,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为自己的国家悲怆。其实放眼看看,每一条江水灌满的大海都一样微苦有点咸,能做人类知识分子的人还要等到下个春天。我辈生于平庸,短衣襟小打扮,轻装远行即可。对我自己来说,我不买房不置产,不开公司不市恩义,无论做游子还是做油子,随他去,也算以知识分子自处了吧。不引用先贤名言了,引一句歌词,来自《Sailing》:To be with you,to be free。
(责编: 阙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