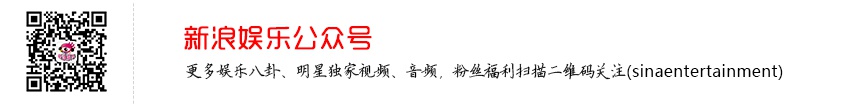新浪娱乐讯 FIRST青年影展今年的电影论坛在7月27日如期揭幕,此次的论坛主题是“另类电影教育”,探讨电影的非典型教育方式,对谈的两位嘉宾是本届影展评审会主席娄烨,和训练营导师贝拉·塔尔。一位是第六代导演中独特的世情观察者,镜头中尽显小人物的爱情与人生;一位是“欧洲仅存的大师”,《都灵之马》影响了一代迷影青年,62岁依然如初,以影像记录真相的贝拉·塔尔。以下为本场论坛的实录:
主题:FIRST电影论坛·另类电影教育
嘉宾:娄烨;贝拉·塔尔
时间:2017年7月25日下午
地点: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李子为:或许,不一定。感谢各位来到电影论坛现场。没有同类,就不能生存吗?对,不能。所以,非常感谢今天到达现场的我的所有的同类们,当然,我知道大家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虽然说耀莱成龙国际影城都是我们的放映主会场,但是我们只选择在耀莱作为电影论坛的唯一的一场,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离酒店比较近。我们每次的准备工作都这么的仓促,这什么团队,我都不愿意跟你们一块工作,嘉宾在这儿都坐着,你们什么玩意,有这么紧张吗,往前多要一个时段,贵一点还是不应该的。所以希望大家理解,非常难,从一个商业电影院里来敲定一个纯粹谈电影,谈艺术,谈生活的一个现场,今天,论坛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今年的电影节的竞赛评委会主席娄烨先生。一位是特别疯狂的,这几天在西宁给人感觉,天啊,什么情况,我为什么要落在他手里来拍片子,就是我们的著名的电影大师贝拉·塔尔。
听说,今天上午老爷子还去游了泳,今天下午一会儿论坛的时候曲线肯定比较优美,今天谈论的主题是电影的另类教育,这两位不论是前辈还是后辈们,大家对他的电影史上的位置也一定认定,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电影大师。有请!还有翻译老师。
还有今年竞赛的副审委员,也是今天这场电影论坛的主持人张亚璇小姐。
张亚璇:谢谢!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人在场来听这个谈话,我非常荣幸能够来主持这个谈话,像刚才子为说的,这个谈话的主题是关于电影的另类教育。如果再做稍微更具体一点的诠释就是教育以及电影非典型性的教育形式,比如电影节。我相信娄烨导演和贝拉·塔尔他们从事了这么多年的电影工作,他们提供了那么多卓越的作品,我想请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谈这个话题。一定会让我们有所得。
娄烨:特别高兴我得到一个签字,就是贝拉·塔尔导演的签字,对不起大家,我先抢到了。很高兴参加这个论坛,我觉得很早之前看贝拉·塔尔老师的电影,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一种味道,好象不多的一些电影是有一些味道留存在那儿,不光是视觉,不光是声音,而是有一种味道,像你在那个地方待在那儿的时候有一些潮湿的气息,这是我现在留下的印象,当然完全不仅于此。我觉得特别高兴,我觉得大家也很幸运,能在贝拉·塔尔老师的指导下拍片,我不知道训练营的同学有没有在这儿,是不是特别疯狂?
贝拉·塔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为我做的一切。要不我们直接切入今天的话题。
张亚璇:因为时间不多,我们直接开始。先请娄烨导演谈一下你的电影教育的轮廓,尤其从电影节的角度,它在你的电影理念的形成,电影理念形态的形成,电影工作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也许可以给一些具体的经验。
娄烨:当时电影学院上课,首先是一些基础的课,大部分的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教授的肯定是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的,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德西卡都是作为基础教育,可能是因为80年代中期,85年进学校的,那时候中国的状况也只能是这样,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是安全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安全的,所以时尚正式开始。
而实际上通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一直到后面,包括安东尼奥尼的那些影片,我们知道电影不仅于此,远远不仅于此。这可能是开始的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感觉是这样的。
张亚璇:我在想,也许我们的谈话可以交叉进行,可以吗?娄烨。刚才问题很大,可以延续很长时间,但是我想,娄烨导演谈一点,我们请贝拉·塔尔也谈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继续,这个问题没有结束。
贝拉·塔尔:我的电影教育开始其实没那么刺激,我其实本来不想做一个导演的,对我来说电影只是交流的一种形式。对我来说现在也是交流和表达的一种形式。
我学习的其实是生活,是人生,不是电影。我也在过日子当中学习、体会。当你对生活有一定体会以后,你才会知道要怎么样表达它?拍电影是什么意思?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你自己消化,再把它表达出来,与人分享,这是在我眼中的电影拍摄。
所以我教电影教了很多年,但是我还是觉得不用特意来学拍电影,这点我们等一下再详细展开。
张亚璇:我们可以边想边听,也许娄烨导演在接着说一说在电影学院可能获得了一些营养,但是这些营养足以支撑你之后的电影工作,还是那些电影的观念,从形态到方式,日后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发展?
娄烨:实际上当时的状况,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反正有很多人考电影学院是因为能够看电影,因为能看到外面放不了,看不到的电影,这是一个原因吧,因为当时的时候,很少电影能够在中国的电影院放映。
接下来的情况是我们上课,放电影,在开始第一年我们发现那些理论课没有人去听,全到放电影的课上,老师特别生气,因为那时候看的电影太少了,我们等于在那儿利用这个机会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电影,各个不同风格的电影,这实际上是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在后面几年才会感觉到你是在学习这些电影,实际上也在学习电影里呈现的那些生活。实际上那时候对生活可能没有什么理解,因为可能太年轻了,或者是怎么样,实际上电影学院的状况,因为这些电影打开了学生的眼界,你知道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国家,他们是这样生活,他们是那样谈恋爱,他们是那样的争斗,这个实际上是四年电影学院快毕业的时候才感受到的,在开始的时候没有特别清楚,现在返回去看电影学院影片,好象是在学电影,可能也像贝拉·塔尔说的在潜移默化的感受生活,不能说是学习生活,因为感受不同的生活,使得电影学习的毕业生在毕业以后能够开始他的第一步工作。
张亚璇:我们理解这样的起点是重要的。
娄烨:不是故意的,但是是非常偶然的幸运,现在看是一个偶然的幸运。还有一个偶然的幸运,那里头看的片子什么都有,有做爱,有暴力,什么都有,这是另一个偶然的幸运,没有太多的限制,而你可以说是限映,也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坏的事,我们这波人出去拍电影老是不过,这也是一个麻烦。
张亚璇:您觉得跟当时的起点是联系着的?
娄烨: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学过来的,所以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就不管就拍了,所以困难重重,觉得特别不公平。但实际上追本溯源,最大的祸手还是电影学院。
张亚璇:我不知道现在电影学院的教育是不是跟那个时候您接受的东西还是类似的。
娄烨:我不太了解现在的电影制作,从我的角度来看,比如80年代,我们这批人,第5代之后的那批人,我们做了很多的拍片练习,拍摄作业做的很多,学校也不管我们,你们自己想办法把这个短片自己作业拍了,无意识当中制造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在90年代初之后的10年,中国出现的地下电影,也就是说,在学校就学会怎么拍地下电影了,情况是这样的。
张亚璇: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想刚才娄烨导演讲的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其实那个时候学院的教育还是强调作者电影理念。
娄烨:对,我们的功课是大师研究。
张亚璇:对,我没有研究过今天的电影教育状况,但是有一个直接的感受,我觉得对于产业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作者。
娄烨: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影响。
张亚璇:所以是完全不同的理念,也让学生获得不同的营养,是一个重塑。但是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讨论所谓的另类教育,我们希望能够探讨或者思考一下电影节这种形式能够在电影教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对年轻导演来说。
我想,请娄烨导演进一步延伸的是你获得了一个有意义的起点,也似乎获得了很多营养,但是在之后的电影工作中,您觉得这些是够的吗?我想,你肯定从不同的途径也在获得不同的营养,来形成自己的电影理念,找到更加成熟的表达形态。
娄烨:读了电影学院你觉得自己懂电影了,可以拍电影了,但是真的工作的时候你发现是零,什么都不懂,既不懂电影,也不懂生活,这是我的感受,就回到刚才贝拉·塔尔说的,其实不是电影学院交给你的,这是之后的感觉,当然会有帮助,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张亚璇:您是在一个生活的现场当中去电影工作,但是这个是可以很具体的,有不同的场域,电影节是其中的一个,跟你的电影工作肯定有直接的关联,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尤其是在中国电影节,尤其西方电影节,国外电影节格外重要,对于这些拍所谓艺术电影或者作者电影的导演而言。能不能具体的讲一讲你的经验,在跟电影节的相遇,有什么样的记忆,是不是有所得?
娄烨:你拍了电影,你没得通过,你看谁要这部片子,自然有外部电影节要这部片子,你去放了,你发现有销售商买你的片子,你就进入它的正常的销售轨道,就是这样的。
张亚璇:我们想听具体的感受,第一个去电影节的片子是《周末情人》《苏州河》。
娄烨:《周末情人》是在被禁两年后去了海德堡电影节,那可能是第一个。
张亚璇:有什么感受呢?
娄烨:当时感受就是电影世界是这样的,特别大,有特别不一样的作者,你会发现你更是从零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地方的导演都有不一样的经历。
张亚璇:当然,但是我们只是讲一讲自己的经历,可能现在我们请贝拉·塔尔导演也谈一下。
贝拉·塔尔:当然电影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如果我想让大家看到我的电影,通过电影节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渠道。因为电影节是一个集合了媒体、宣传、买家所有人的场合,是个市场行为。想得到关注,那么就通过电影节来操作。
通过电影节首先能让你得到更多的关注,获得更好的市场,以此达到更好的海外发行,有时候去柏林,或者戛纳,威尼斯的时候,觉得好象几乎纯粹是一个市场操作。而且是一个很便捷的渠道,因为在电影节会看到你的名字跟所有的大咖并排在一起。这就要说回到FIRST青年电影展,这个就跟欧洲的三大电影有一些不同,电影的起源是青年一代电影创作者更加有活力,没有那么商业化,所以更加有活力。
张亚璇:按我的理解,刚才贝拉·塔尔导演说的是那些大一点的电影节,他们总是想要更加的安全,安全意味着什么?他们总是选那些很大很响亮的名字,这是为什么他喜欢这样的电影节,他想更有活力,诸有此类,有一个对比在里面。
贝拉·塔尔:刚才主持人的问题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在你看来更像是市行为它的教育义在何处呢,8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活跃的时期,那个时候,是真的遇到做电影的同仁一起交流,一起分享,从中得到一些经验。我24岁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时候,真的能在电影节上,比如说安东尼奥尼面对面交流一小时,对于我来说有没有教育意义呢?好象也没有。
我记得很清楚跟戈达尔的会面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说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我那时候才24岁。我跟他面对面坐着,他一直在抽雪茄。我本人不讲法语,当时有一个法国朋友为我做翻译。当时提了一个问题是关于长镜头。他抽着雪茄很久没有回答,最后说他忘记了。我就坐在那儿吓呆了。现在我有点理解他当时的做法了,他也许觉得我的问题很愚蠢。但当时我简直想杀了他。
张亚璇:刚才很有意思的一段谈话。对娄烨导演来说呢,你有没有在电影节有过那些很有意思的相遇,遇到有趣的人,有趣的事。
娄烨:有,差不多。
张亚璇:讲一讲。
娄烨:我们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贝托鲁奇在拍《末代黄帝》,可能是作为交换,要给导演系上课,那时候我们觉得不得了的一个导演给我们上课,后来很久以后,在罗马我见到他,我想了很长时间,想问他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说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拍摄的现场。他的回答是睡觉。
张亚璇:你如何理解这个回答呢?
娄烨:我有点生气,(问)你是不是对付我,他说是真的睡觉,摄影师四小时补一个光,我怎么能不睡觉呢?确实补光时间特别长,哪怕是这样的回答,我觉得还是获得了一些东西。我会跟摄影师说补光时间短一点,不然我要睡着了。
张亚璇:是后来工作时间当中的一个体验吗,有的时候你要等很久。
娄烨:对,确实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时间等的长了,可能演员也不行了,导演也困了,会有这些问题,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你得到的哪怕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信息,都会帮助你思考一些事情,或者重新看那些影片。
张亚璇:你肯定去过无数的电影节,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电影节之行是什么时候?带的哪部片子去的?能够给一点这样的例子吗?
娄烨:去电影节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困难的工作,很难受,但是我告诉自己,去电影节这是一个电影导演的工作的组成部分,所以就这样吧,因为确实可能是需要的。所以,没有特别好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录音师在技术检查的时候要撒尿,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每个导演不一样,当然。因为在终剪来说,对我来说一个电影导演的工作结束了,应该交给下面的工作人员销售这部影片,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影片,我觉得是有分工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张亚璇:因为我们也知道,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学都知道贝拉·塔尔导演他后来也有在匈牙利开一个电影学院,我们请他谈谈电影学校的事情。我想请贝拉·塔尔导演谈一下他电影学校的事情,理念、运作。但是刚才在酒店我们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在开这个电影学校之前,因为政治原因,不得不关了他的制作公司,他作为一个导演的工作好象要暂停一下。我问他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下。
贝拉·塔尔:首先我是在2011年以后就不再导片子了,暂停了导演工作。决定转行做制片人,之前也有过一些制片的经历。之后匈牙利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家对电影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有一些不同,所以我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国家的理解,要么关掉我的公司,所以我就关了我的公司。
关掉公司以后我在思考我之后做什么呢,之前25年我都非常频繁的参与世界各地的工作坊和电影学校的教学工作,所以,也算是一名电影教育行业比较资深的从业者了。我实话实说,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所特别好的电影学校。然后我就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
教育其实对我来说应该是老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教育学生,告诉学生规则是什么?跟你说你必须做什么?给你指引方向,这全都是错的,教育不应该这样来,娄烨导演刚才提到了一个关健词,就是差异化、不同。人跟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样规范化的教育体制下,老师不把学生当做不同的个体来看。
张亚璇:他说在座的所有人都是不同的,但是在老师眼里是差不多的。
贝拉·塔尔:如果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话,教师需要体会到学生的不同。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在波斯尼亚萨拉热窝的电影工厂就是基于这种理念创建的。持续了三年半的时间。我当时决定开一个国际性的电影学校,这个电影学校是建立在一所私立大学里面的,当我们对外宣布以后,世界各地都有学生慕名而来,我们当时的学生有来自日本的,来自韩国的,来自印度的,拉美地区的,美国的,冰岛,欧洲,当你看到一个冰岛的学生遇到了一个日本的同性恋女孩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流会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故事,所以你就会发现世界很大,人跟人真的很不一样。当我看到我面对了这么一大屋子人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丝胆怯。
张亚璇:为什么?
贝拉·塔尔:我应该怎么对待这些学生呢?用怎么样的方法教他们呢?他们因为相信我慕名而来,但是我教不了他们,要是能真的教他们,我需要很了解新加坡,很了解里约热内卢,但是我不了解。由此我觉得我需要更加有同理心,让教学更加个性化,我们从来不讲一板一眼的理论。
张亚璇:所有的都是个人之间的讨论。
贝拉·塔尔:所有的讨论都是基于每个学生不同的背景而开展的。我渐渐了解到了,其实教育不是最重要的,自由是最重要的。
张亚璇:没有教育,只有自由。
贝拉·塔尔:他们得做自己,我跟学生说,现在已经21世纪了,拍电影没有什么局限性,可以拿手机拍电影了,你就放手去做吧,不要害怕,自由一点,不要规则,不要有预设的来拍电影,打破规则,打破局限,这就是我们的电影工厂,这就是我们的电影学校。我的镜头语言,我的电影语言只是我自己的电影语言,不是你的电影语言,你需要建立你自己的电影拍摄手法和你自己对电影的理解。
我发现电影这个词含义真是丰富,每个电影创作者都是不一样的,电影创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都有自己富有个性化的电影语言。于是我就邀请了一些我在电影圈的同仁一起跟我的学生们进行探讨。我很自豪的说当时邀请了30多名电影界的同仁跟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
张亚璇:比如说阿彼察邦来过两次,拉夫迪亚斯是菲律宾的一个电影导演,拍剧场9个小时的作品。
贝拉·塔尔:我刚才讲的不是全部的,只是我刚才脑子里想到的一些名字,这些朋友来到我的电影学院跟学生一起进行交流,让每个学生能开展或者建立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你能想象跟着学生们一起进入到森林开始冥想吗?或者著名墨西哥导演跟着学生们一起游泳吗?
张亚璇:他说所有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导演,各个国家的导演,都曾经在大电影节上放他们的作品,得奖什么的,他用这种方法告诉大家电影的世界有多么的丰富。为什么这个学校持续了三年半呢?
贝拉·塔尔: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不符合大学的结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资金的问题,因为是一个私立的大学,所以我们这个专业是烧钱的专业,学校从其他专业得到的利润,成本,全都花在我们专业身上了。这就是为什么把学校停掉了,但是这个学校是非常不同的学校,不同之处是我们把每个学生当做不同的个体看待,我们同样尊重他们,但他们每个人是不同的,这点我们非常承认。这是我对电影教育的方式和理解。
娄烨: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说开这个电影学院是因为说拍电影和国家的政策不太一样,我想问是怎么不一样?
贝拉·塔尔:因为之前匈牙利的电影行业越发的中央集权化了,我曾为此争持了很久,但是也相信这样的中央集权化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终究会消失,终究会过去,对此我并不是很看重,我更看重的是生活当中的。
开一个电影学校和开一个制片公司有相似的地方,都是为了培育人才,保护人才,挖掘新的项目,挖掘新的声音,不同的个性,我需要保护这些人才,对我而言从来不希望学生也好,同事也好,只给我一个剧本,因为电影对他来说不是词汇,而是画面。
不管是做教育还是做制片的时候,我会看着你的眼睛,试图了解你想说什么,如果你的眼睛能够说服我,我就会尽全力来帮助你。有蓝眼睛,有棕眼睛,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张亚璇:我想问的是,刚才在您的谈话里,您是如此的强调自由,但是刚才也说到了改变,这些改变让你停止了制片的工作,现在也停止了学校的工作,在更早之前,您甚至停止了导演的工作,那么您在之前的电影工作当中是自由的吗?
贝拉·塔尔:我一直是很自由的,这可能是我很幸运,也可能是因为我太不在乎了,以致于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勇敢,从而变得很自由,我相信如果一直很关注一些外在的东西的话,那是拍不出好东西的,所以只有一直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想拍什么,才能拍出好内容。
我从92到94年一直在拍《撒旦探戈》(速记缺失,根据前后文推测为这部电影)这部片子,这两年当中,剧组的同事不断的在跟他说,从来没有一部电影有7个小时,这样是行不通的。
张亚璇:说你疯了吗?
贝拉·塔尔:就是疯了,那怎么样呢?在我之前也许没有7个小时的片子,但是我就做出了7个小时的片子。如果你一直特别关注别人的想法,这样行不行得通,那样行不行得通,就拍不出好的片子。
摄影师把摄影机往桌上一摔说,我不拍7分钟一个的镜头。这之后情况也没有改变,我们还是长镜头加一个长镜头的拍。拍了100天之后这个拍摄还在继续,每个人都近于疯狂。
拍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还在拍同一部片子,所有人因为不知道到底整个故事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大家每天都不知道自己今天要拍什么?但是这有什么关系?摄影师扔完摄影机以后,我和颜悦色的抱了抱他,说喝点东西,两个半小时胶员又冷静下来了,我把他找回来,说咱们看看摄像机有没有摔坏吧。我们一起回到了拍摄现场,修了摄像机以后一直拍到第二天早上5点。
电影导演一方面来说需要非常冷酷,不应该关注别人到底在想什么,同时又要非常有同理心,一定要关注别人在想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关乎情感,我前几天跟人说过,不要用脑子工作,要用心工作。当然最好的状况是头脑和心灵同时工作。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把锁,想打开这个人需要不同的钥匙。
张亚璇:现在轮到娄烨导演了,跟我们说说关于创作自由的话题,你的感受,在这个环境当中,如何协调,如何去寻找到一条道路,让自己能够自由的表达。
娄烨:我先说刚才我听贝拉·塔尔说的,你必须不管别人,但是你又得管别人,这个是电影导演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我深有体会,也是很难做到的。
有时候也很困难,你没法做一些决定,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张亚璇:你也做决定吗?
娄烨:肯定得做决定,但是有些决定没法预测它的未来,或者从另一个角度你不用预测它的未来,不用管吧。不用想太多,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张亚璇:愿意谈一谈跟创作自由有关的话题吗?
娄烨:我不太一样,我老觉得不自由。各种问题,电影审查,没有足够的钱,找不到好的场景,找不到最有力量的表达,时间长了,我认为这是一个电影工作的一部分,也就不是特别在乎了。
张亚璇:但是您认为您最终呈现的拍出来的是自由的电影吗?
娄烨:我觉得如果反回去看,我还是很幸运的,我在一个时间能够拍一种电影,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了。就是这样。因为每个时间想的不一样,在那个时间我居然就能完成一部电影,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了,所以那些不自由都忘了。
张亚璇:都被你克服了,是吗?
娄烨:就是忘了,其实还是有的,只是忘了。
张亚璇: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到提问时间,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听了两位导演的谈话,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有什么问题?20分钟到30分钟可以吗?每位观众只提问一个问题。
观众提问: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娄烨导演,因为刚才听您说,讲到创作和自由的问题,因为我特别喜欢您的电影,也一直在关心。最近有一些政策出台,网络视频上不能出现同性恋,不能出现这个,不能出现那个,我也一直了解到您从开始创作以来,一直受一些政策的影响,我也是一个年轻的导演,对这个事情感到比较困惑和迷盲,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跟我们说一下到底该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
娄烨:我没什么建议。我没主意,没建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唯一可以做的可能是拿起摄影机去拍,拍你想拍的电影,这是我唯一的建议,你去拍就完了。
贝拉·塔尔:每个人都可以拍片子,用啊,用起来啊。
娄烨:要是没钱,先挣点钱,打打工,到公司或者是公务员,但是得去电影检查部门,那是一个特别要命的地方,而且电影审查员是一个特别可悲和可怜的职业。
提问:两位导演好,我非常喜欢两位导演,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我本人是一个电影专业毕业的学生,我现在在一个上海的工作坊教学生,我是坚持一对一的带学生,希望帮学生找到他们自己的声音和风格,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总归有一些基础的东西要教给他们,比如镜头语言,基本规则,怎么平衡,不要教太多让他们自由表达,但是还是要把一些基本的东西传递出来。谢谢!
贝拉·塔尔:我相信刚才我的谈话过程中,已经基本上说到了给您的问题的答案了,我们每个人是不同的,每个学生是不同的,打开每个学生的锁是不同的,大家有不同的情感,一切都是基于情感得来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拍摄我自己第一部片子的时候,我对拍电影的基本要素一无所知,我唯一有的是一个16毫米的摄像机,我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人的脸拍进来,应该把那个人的脸拍进来。22岁的时候拍第一个剧情场片,只有5天的时间。
我拍完每部片以后有一个新的问题产生,当然这个新的问题不能用老的答案来解释,一部片一部片这样拍下来就形成了自己的镜头语言,就形成了自己的电影语言,当然每一部片更加的深刻,越深刻下去,就能越纯粹。当然你也会犯错误,当你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觉得很羞愧,并且从这个错误当中汲取到以后,你下次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其他的人来告诉你,你犯了什么错,他强调的是自己的反省,自己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
娄烨:或者是继续犯错误。
贝拉·塔尔:当然,一定会一直犯新的错误,不同的错误,因为人无完人。
娄烨:刚才说是不是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需要学习,我的看法是根本没有基础的东西,不需要有基础的东西,不存在基础的东西,因为电影怎么拍都可以。
张亚璇:贝拉·塔尔导演刚才谈的时候说了同样的话,没有基础的东西,他就在强调整个创作过程,以他自己为例,他拍出一个电影,他会意识到一些问题,他需要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他在拍下一部电影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没有同样的答案,不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答案,他在强调持续的在电影的实践当中,在自己的拍摄实践当中去思考,去学习,最后他说,这样你就会走的越来越深,你也会越来越纯洁。
提问:两位好,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知道,你们现在都已经拍了很多的电影,从以前觉得自己不太会拍电影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你们觉得你们可以真正会拍电影了,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什么样的感觉,可以给我们分享吗?
娄烨:实际的说,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太会拍电影,每当拍一部新电影,我老觉得我忘了怎么拍电影了,这是真实的感受。
贝拉·塔尔:我和娄烨导演的感受一样,我至今仍然不相信自己是个导演。就像我在开场的时候说的那样,电影创作是一种工具,是表达的一个途径,交流的途径。
提问:谢谢两位导演,我想问一个关于观看自由的问题,现在电影媒介的传播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两位导演怎么看待我们通过手机和电脑来观看电影,而不是进入电影院,还有关于大陆观众经常下载盗版光碟看,两位站在创作者的角度对这个是什么态度?谢谢!
娄烨:我觉得还是手机看电影和电脑看电影和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不太一样,因为感受不一样,我觉得这是无法代替的两种感受。从进入电影来说可能需要在电影院,哪怕自己家里黑暗的环境里面,可能更容易进入一部电影。
盗版问题,我知道它是一个特别要命的事,特别不好的事,但是它又是一个很好的事,因为它能把更多的电影带给影迷,让更多学电影的人看到不一样的电影。
贝拉·塔尔:在这个数字时代,我把这个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跟电影制作有关,现在的电影拍摄作者不是在胶片上拍了。
数字电影不是电影,它有自己不一样的语言。对我来说电影拍摄就是35毫米胶片,数字动态影像就像是电影里的第八艺术,如果我们把电影看成第七艺术,没有看到数字动态影像给这个媒介带来了什么新的语言。
另外一个角度,从发行的渠道来说,35毫米的胶片电影在电影院里放映,当你可以和你的邻座一起看,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存在,这和你一个人独自在家,在电脑上看我的片子或娄烨导演的片子是很不一样的体会。说到盗版,娄烨导演非常好心的还帮它想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说可以让更多人看片,但我的理解是,一边待着去吧,别偷我的钱。所有的盗版商们把你们的钱捐出来给导演拍下一部片子,这才是一个更高尚的行为。
提问:我特别喜欢这次的讨论,我想问贝拉·塔尔导演一个问题,我注意到他的片子里面的环境音和杂音的声音处理一般都会比真实的生活里面的声音要大,我注意到在布列松导演的片子里面也有类似的处理,所以我想知道,导演是怎么考虑电影里的声音处理?
贝拉·塔尔:我之前的5部片都是在棚里拍的,不是现场收音的,我其实挺喜欢可以通过后期增加一些细节,以此使片子或者说声音上表达的更丰富,当你真的听到这个声音效果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你就能感觉到应不应该这样做。电影拍摄任何方面都没有固定的配方。没有固定的1234。
提问:我是一个今年刚高考完的学生,原来是有机会去北电,后来去了上海电影学院,娄烨导演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在北电学习的这几年对你的创作道路有什么影响吗,对于一个电影创作者来说是后天的学习和先天天赋相比哪个更重要一些。
娄烨:每个人不一样,比如说你先学了,或者说后学了,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选择自己的方式,没有固定的逻辑必须要怎么样。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张亚璇:天分重要吗?
娄烨:天分重要,当然重要,当然没有天分也可以做没有天分的事。但也不一定是坏事。没有天分的,我们拿电影做比较,一个有天分的电影不一定好于一个没有天分的电影,这是显然的。
张亚璇:大家对这个回答满意吗?我们就停在这儿。谢谢!非常感谢娄烨导演,感谢贝拉·塔尔导演,跟我们聊这么长时间,感谢大家在这个地方听这个谈话。稍后电影节应该会把谈话整理成文本,我想会的。谢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