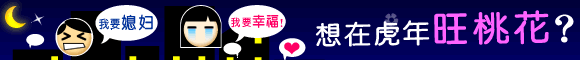对话英国导演盖-里奇:在麦当娜撤了之后
对,就是这个人,拍过《两杆老烟枪》和《坑蒙拐骗》,狂热的伦敦爱好者,开了个酒吧,还和麦当娜维持了一段不短的婚姻……我们也不是那么八卦,但我们对他很有兴趣,于是,我们找上门了。
Tom Chiarella/文
星期五中午。几个顾客散坐在Punch Bowl,盖·里奇在伦敦梅费尔区与人合开的酒吧。大概六个人。里奇进来,穿了一套灰色西装,剪裁讲究,有点紧身的那种,口袋里没东西,这些人里面,只有两位似乎有所察觉。没电视也没音乐,但他们自顾自。里奇从眉毛下面深深瞪了一眼,就像灯光照射的警告:离开。马上离开。人们通常留意这一指示。他毕竟是个导演。
他看起来有点神经质,甚至难受,站在挤过窗户满是灰尘的光柱之中。他好像一幅黑白画。里奇没说话,说得不多;他只是打足精神向助手承认,他有点宿醉,他想吃点早餐。我们出发了,他在街上什么也没说,只是弓着背去往他知道的一个地方。大概十五步,他一言不发。
但仅此而已。从那时起,盖·里奇就没闭过嘴。
你得明白这一点:盖·里奇说得太多了。他很少谈他自己,或自己的电影,或那个著名的前妻。他不想告诉你他已知道的东西或刚刚读过的东西。他不是太有兴趣讨论他做过的事情。大多时候,他想告诉你他在想什么,他就他的想法喋喋不休,长篇大论,偏离主题。当然,有迹可循。例如这些:建筑学对抗理性主义痛苦啤酒相对主义橘子酱。只有跟里奇一起,才有远远比这还少的标点。盖·里奇重复自己。他咒骂,飞快地相互参照,给出不像答案的答案。有时侯,他甚至似乎也感觉到其中的含糊其词。
盖·里奇文化上应有的卖力,在于他是一个吵闹、纵酒、关注自己的41岁富含睾丸酮的水龙头,他是麦当娜的名人前夫,是精力充沛、小有成功的独立电影作者,如《两杆大烟枪》和《偷拐抢骗》,这些电影由一帮里奇类型的人物扮演英国下层罪犯,做着无厘头的精彩事情,从事这样那样的打劫。
这些日子,他刚刚完成一桩有潜力的特许生意的首期工作,一部新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电影,由小罗伯特·唐尼和裘德·洛主演。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找一个拍电影节奏很快很散而且有点费解的人,并把处理一个有着122年历史的故事的关键交给他,而在这之前的制作靠的是细节的微妙处理,靠的是将故事围绕着流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推理头脑?你要问:为什么是里奇?
两壶茶。吐司和橘子酱。他的麦片。“太好了,这个房间。”他说的是餐馆,Richoux,距酒吧不超过三条街的茶室。
“这个地方老吗?”我问。他闭紧一只眼睛,垮着下巴。“不知道。也许100年。也许没有。在一座1000年历史的城市不算老。”我说我喜欢他的酒吧,有250年历史—喜欢我看不到电视机这一事实。
“是的,我们把那些立刻拖走了。”他说。酒吧对他来说很重要,他的首要事情就是置身其间。“可以说,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好时光,就是当我在狂饮之时进行某种形式的谈话。英国人做这个做得很好。但是跟我们在酒吧里面所有这些了不起的臭骂随之而来的是什么?电视机和自动点唱机之类东西。电视位于心智以下。它是次要思维。你可熟悉这句格言:‘跟福气相称,就是跟诅咒相称’?嘿,来点橘子酱。”
里奇过来给我弄茶,他甚至搅了搅。他坐在那儿,衣领敞开,胡子刮得干净,显然很客气,你甚至可以说举止优美,他派着方糖,没有一刻不自然。
时间随着谈论即将上映的《福尔摩斯》而流逝。我看过一些片段。我问,福尔摩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打断别人肋骨、在街头殴斗的扁人家伙?
“福尔摩斯是个绅士,但他也是一个街头小子,可以有点儿邋遢。我觉得这个故事失去了它这一部分的精华。”里奇说。“我喜欢街头生活,但我也喜欢宏伟的东西。能够在这两个世界里面走来走去很吸引我。另外,他是西方第一个武者。”
我注意到,唐尼扮演的眼睛转动有点冷酷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看起来几乎就像得了某种形式的亚斯伯格症。“他为自己的敏锐功能和功能失调所苦。他在社交方面很不擅长。”里奇说。“当然,自闭症的一大幸运,就是它把你的观察能力提升到凡人之上。”
在某一处,当谈话撞来撞去,我告诉他昨晚侦察过他的酒吧,说起酒保怎么要我摘下帽子,一小群醉汉怎么保护我,对着酒保叫喊,警告他们不得把我当做一个吉普赛人那样对待。
“那么说是你戴着帽子?”里奇说。
“你听说这事了?”
“他们今天早晨告诉我的。”他说。“他们说你很听话。”
“我的错。”我告诉他。“那是个好规则。我欣赏规则。”
“当然。”他说。“那是基本的。”里奇念出那个词的每个音节。我现在知道,它符合他心中对基本行为准则所作考虑的每一个成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确定,一切都随着相对和绝对的分离而崩溃,他从七岁以来一直在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格斗,他年轻那阵照看过酒吧,砌过砖,挖过下水道,他喜欢迈克尔·曼的电影,觉得《公众之敌》可能是约翰尼·德普迄今最好的电影,他欣赏一个男人让工作区域干干净净,他喜欢博学胜于专精。
当他的助手溜进来说盖有个被她忘掉的约会,他看着她的眼睛—会不会是在眨眼表示某一哑语—然后对我说:“事情是,我得做点训练。”
我收起我的便笺簿和录音机,伸手去拿我的帽子。“很好。”我说。“你给了我足够多的东西可写。”
“巴西柔术。”他说。“它让我着迷。这是我玩的唯一运动。甚至是我观看的唯一运动。虽然很惭愧。我很喜欢这番谈话。”
我一半在想:我想看他格斗。而另一半在想:我想跟他一起加入某次“酒吧里的臭骂”。“你应该把我带上。”我说。“我们一起。我觉得我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好的同伴。”
“是吗,我也是。”他说,就像那样随和。“那就让我们他妈的把它延后一些。”
里奇在家里一楼有个房间,铺了蓝色垫子,用来练习柔术。热身期间,他指尖着地做了40个俯卧撑,起身做了20个引体向上,然后着地再做40个俯卧撑,这次是以指关节着地。那天,他正跟现在的世界冠军Roger Gracie有节私人课程。
巴西柔术出手快而低,有点儿卑下。这项运动主要是在身体姿势方面取得优势,通过抓扯、扭曲和令人窒息来制服对手。Gracie在房间一头蹲下,当里奇跟他平常的训练伙伴扭斗起来,轻声给着建议。里奇用双膝格斗。躺在地上搏击。他似乎从未停止格斗。(在这之前他研习过14 年的空手道。)他在这方面是个棕带,尽管他告诉我这在柔术世界并未令他更有作为。手指摔破,肩膀推开,双膝、双脚和脚趾戳到睾丸。里奇的颧骨上有了一条深红色的伤痕。
之后,他在他的露天平台跟我一起。他不穿上衣坐在太阳下,他的皮肤苍白,都是创口和瘀伤,他把水浇到头上。刚刚摔打了一个小时,他倒在椅子上,但他的脑袋似乎完全垂在脖子上,他的双肩仍然端起;他似乎十分惬意血液就在皮肤下面流动,就像某个24岁的后生。“我把我这方面所有的本事都归功于空手道,因为他们就他妈的这么狠毒。你要是倒在地上滚来滚去,他们毫不留情。你要是有任何一点疼的表示,他们不会跟你说话。这些男子气概的废话,就是那样。”
当你不想受伤,你的人生就到了一个点。我坐在伦敦市中心的太阳下面,喝着瓶子里的冰茶,馅饼帽在我头上晃到一边。虽然屁股下面的折叠椅有点硬,我大概远远没我想的那么疼。不知怎么,里奇—青一块紫一块,流着汗,依然大声喘气—没有因为我逼他回答为什么欣然接受它而令我尴尬。
“在空手道里,你发现理论上的疼痛是怎么回事。你一层一层经历。”他说。“我过去常常看着人们倒下,肋骨破裂,不能他妈的喘口气,而他们马上就站起来了。他们站起来十次。我明白了界限,疼痛所在的那个地方,不是我想的那个地方。”
他然后猛喝一口水。“听着,我有三句最佳台词。”他说。“第一句直接来自空手道。”
“你是什么意思,台词?”我问。“就像规则?”
“只是台词,真的。教给我的东西。我想,我跟它们一起生活。”
他喝了更多水,然后瞄了我一下,表示对他来说这里面有价值,有投入。“我会告诉你头两句。”他说。“但我不会告诉你最后一句。”
“为什么不?”我问。这似乎是个合理问题。是他把它们提出来的。
“它不可估算。”他说。“这个世界还没为它准备好。”
这让我有点恼火。“我要是哄你呢?”我说。“我要是让你喝酒呢?”
他没怎么考虑。“去喝点酒可能有用。但我现在只告诉你一句。而我永远不告诉你第三句。”他非常认真。“行吗?”我同意了。“好。第一句是这样的:你得以不舒服为舒服。”他说。“那是空手道教我的东西。害怕不舒服比不舒服本身还要糟糕。”
我年纪够大,不必就此提问。“我明白了。”我告诉他。“当你说不舒服,你指的是我所想的痛苦。”
然后他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仿佛为了平衡一切,误把重复当做解释。“痛苦的错觉,”他解释道,“是你不得不觉得舒服的某样东西。”
“那就是为什么你的电影里面有很多格斗?”我问。
他撅着嘴。“不见得。我只是喜欢看人格斗。”然后,他像太阳下一条狗那样脑袋往后一甩。
盖·里奇说起他怎样在伦敦开车—永远向前,转弯冒失而马虎,不注意警告牌,不理会标志,为了更带劲而加速,经过熟悉地方很少走一样的路。那是第二天。一番快速聊天再度延长。每次当他慢下来,他都指着一个地方,讲起一个故事。我们正从他在Ladbroke Grove的健身房回来,从一堂两小时的训练课出来几分钟。里奇穿着便服,还在流汗。
我在讲电影,我真傻。我问起《偷拐抢骗》,我承认那些口音让我一头雾水。只有一个人我真正听得明白,即布拉德·彼特那个角色,那个有意一口胡言乱语的吉普赛人。他我明白。里奇喜欢这个,继续说着吉普赛人,猛敲一下方向盘。“吉普赛人了不起的东西,是他们让你保持聪明。”他说。“他们会偷东西,你可以肯定。但他们明白事情。他们教你东西。有关蒸汽机,有关猎犬,民间音乐。他们让语言广为流传。懂吗?”他说。“宽广。”这是谈话中的时髦词儿之一。我同意他所说。我也喜欢宽广。
早些时候,在他家,他的儿子罗科顺道过来看看里奇给他录的终极格斗冠军赛(UFC)。这是麦当娜的儿子之一,他们两个小孩之中大的那个。他九岁,是个很有礼貌的孩子,从他妈妈那里骑车过来,保镖也在一旁骑着车。罗科漫不经心握握我的手,然后启动他的Xbox游戏机。里奇立刻逼他放开它。他故意说起规则和限度,用一个父亲的口吻。平面屏幕上的终极格斗让父亲和儿子一起观看,叹息,喉咙里一阵嘟囔。这孩子看着他的领先者,听着他的父亲说话。罗科看到他父亲在录像上面,坐在比赛场边。“瞧这个。”里奇说。“这家伙正在用的全是空手道,没人知道怎么对付它。这就是我为啥跟这家伙这么好。”然后他对罗科说—“你看到啦?来来去去,很快。瞧那个!”—后者轻轻哼着表示同意,随着他爹的关心半是微笑。格斗结束了,他们看了几遍致命一击,然后罗科不自觉地亲了亲他爹的嘴唇,再一次握了握我的手,道了再见。外面,里奇站在街上,看着他离开,眉毛扬起。“瞧。”他说,轻声讲述着他儿子骑着香蕉形座垫的自行车摇摇晃晃离去的情景。“瞧他!”他说,急着提醒。“跳过路缘。跳过路缘。好孩子。”
然后里奇把我留在他的房子里,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呆了二十分钟,而他跑去办一件事情。我做了任何作家都会做的事情:我到处窥探。我走到他的厨房,看看满是电池的抽屉,装满昂贵通心粉的储藏柜。我拍了一张他的冰箱内的照片。(饮料很多,乳制品不多,很多铁扒蔬菜的塑料盒子。)餐桌上面,他放了有他前妻名字的法律文件,他的邮件在台上打开着。我没读它们。我拨了拨他的吉他,读了一遍他的日历,点了一通他的iPod里面的播放目录。我把脑袋伸进每一个相邻的房间,并在之前想着,我应该在这里给他一点意见。于是,我撕了一张记事贴,用很大的大写字母写道:永远不要相信一位作家!把它贴在冰箱里装了希腊沙拉的盒子上。
“你太相信人了。”我在车里告诉他。“你不应该把我一个人像那样留下。一个作家可以在二十分钟里做任何事情。”
“没东西偷。”里奇笑道。“那是吉普赛人教给我的另一样东西。他们就是我为啥信不过在家里放任何贵重东西的原因。如我所说,他们让你保持聪明。”
当然,我没想过偷东西。我想有所发现。例如,他的前妻仍未消散的某些迹象。他的iPod里面丝毫没有,可是“边境线”之后麦当娜的流行歌曲我一首也叫不出名字,所以我怎么会真正了解?我决定现在试试,当我们驾车穿越城市,我问起她来。里奇叹口气。“她是个表露者,如果有这样的人。”他说。“一流的表露者。麦当娜让事情发生。让麦当娜跟任何一个23岁的人对垒,她都会比他们做得好,比他们跳得好,比他们演得好。这女人很宽广。”
“宽广。”我说,重复着今天的关键词。
“还有,当然,你听着:我依然爱她。”他说。他吸一口气,驶过一个红灯。要是没人在他前面,盖·里奇通常不停。“但她的脑子也很迟钝。”
离婚很艰难,不是吗?我说。
“你不能对正在离婚的某人说,他们的痛苦是个幻觉。”他说。“我他妈告诉你,我有感觉,我经历过。你也有。没人可以说他没感觉到。”他继续开车,说得更多了。“那是幻中之幻。最大的基本准则是,你需要一点无知。”我们顺着海德公园的顶端扫视,里奇突然说:“我的第二句比第一句更简单。它让有些人不自在。”
“告诉我。”我说。
“第一句是,你得以不舒服为舒服,对吧?”我已懂得领会原路折返,重复,还有他不停看过来带着“你明白我说的吗?”那种意味的眼光。现在这些都是谈话的一部分。我告诉他我明白。
“这是第二句:有信仰很好,只是别相信它们。”
“哦。”我说,看了一眼车窗外面。“我懂了。那可以是我的台词。”
“你明白了?”里奇说。“给我举个例子。”我欣赏这一质疑,我不怕他的反应,即使我说错了。
“嗯,信仰一开始很美。”我说。“但最后信仰必须捍卫。”
“对!”里奇说。“那只是通往绝对的一条路。”
“通往狂热。”
“一点儿没错!”
我们就这样继续前行,在相对和绝对的快乐和惊恐之间弹来弹去,在去他酒吧的路上消磨着时间。
后来,我们进行了“狂饮之时的某种形式的谈话”,如他昨天早上在Richoux所说。
当我们到了Punch Bowl,里奇—还在流汗,穿了一件开领的西装衬衫,在没冲过澡的身上敞开到第四个钮扣—叫了我不大认得出来的某样东西。我捉摸跟着他应该没错。那是一品脱稍微有点甜的冰冻啤酒,我很快喝完,然后叫了另一杯。当我叫的时候,侍者做了个鬼脸。“都像那样有果味吗?”我看着里奇。
“这是一种很基佬的混合啤酒。”他说。“很多人因此被人取笑。但我想打完比赛之后喝这个很好。”于是我转喝淡啤酒,而里奇仍然喝柠檬啤酒。
一开始某个时候,我把录音机放在桌上,让它运行。虽然那天下午在Punch Bowl一切明白无误,但我还得在回去的航班上听录音,以记住当时我看到的情形。那天下午的255分钟录音是些杂音和玻璃杯的叮当声。谈话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垂钓的重要性,梅费尔区的历史,符拉基米尔·普京,酒吧客,他的前妻。我们不时就某一话题热烈争论。他的朋友们顺道过来喝一杯。讲了很多故事。在某一刻,被人激将,里奇逐字逐句唱了一首爱尔兰民歌《通往都柏林的崎岖之路》。人愈来愈多。当游客过来照相,里奇瞪着他的“离开”眼光,变得冷淡。
“麦当娜,当她来到这里,那还是老派的伦敦。”里奇说。“没人烦她。‘喂,亲爱的。你好吗,亲爱的?我能为你效劳吗?’那是很基本的,老派。不管她是谁。她那时是我妻子。”
录音快到结尾,我们进行了一场简短而愚蠢的你来我往,集中在他的另一个日常观察。我们已经谈了3小时47分钟,盖·里奇那时断言橘子酱比果酱好,从仔细观察早餐涂抹推论出他自己的创造性美学。我不记得这番争论了,不论现在或是坐飞机回去的路上。以下就是录音记录:
盖·里奇(GR):它又苦又甜,对不对?你在这里得到的是收缩与膨胀。绝对与相对。别给我果酱!不要他妈的果酱。瞧,我不喜欢覆盆子酱,因为它太酸。我真的喜欢草莓酱,但它有点过甜。橘子酱给你的却是他妈的又苦又甜。
Tom Chiarella:我也可以加上又软又讨厌的橙块果酱。关于那些果皮有些报道,你知道吗?”
GR:你切得厚,你削得薄。现在,你是喜欢削得薄还是切得厚的橘子酱?
TC:妈的。我不知道。你喜欢哪种?
GR:我喜欢的是削得薄味道好的橘子酱。有点果皮,因为我喜欢有点儿苦味。我吃过他妈的每一种橘子酱,我喜欢削得薄的橘子酱。
TC:你是橘子酱之王。
GR:现在,说到Richoux的橘子酱,那是可以感受的橘子酱。我的感性可以感受。我的天性是,我喜欢可以感受的垃圾。我拍的头两部可以感受的电影是《两杆大烟枪》和《偷拐抢骗》,它们可以感受。接下来的两部是不可以感受的。第一部是《踩过界》,唉,每个人都看得很迷惑,因为麦当娜。而再下一部只是概念上的。那一部—那只是纯粹内行才能明白的橘子酱。
TC:你说的是《左轮手枪》。
GR:对。正是这里你可以就一个人的橘子酱说很多。我的上腭真的很精细,它可以感受。我并非说我不会考验你。因为所有橘子酱都在考验你。
TC:杏子酱是可以感受的。
GR:嗯,的确。但是说到橘子酱,它的奥秘里面有点可以感受的东西。所以你瞧,我想创造的是可以感受到一点的奥秘。好了,那就是橘子酱,不是吗?
这家伙是个敏锐的观察者。一个思想者。他很聪明地戏弄一个隐喻,欣然接受他自己的构想的不完美之处,将他的主题推向更宽广的谈话领域。他承认自己的失言,不时笑一笑,而当他把事物分为两样—分为绝对和相对、远和近、非凡和平凡这一模式—那并未让事物陷入可以预知的非黑即白的对立。它只是驱使一场正午谈话形成彼此共享的密码。它给了我们某些东西去思考。很宽广。
这段录音之后不久,我请盖·里奇告诉我第三句,第三个基本准则。他同意了,如他所说,一旦我们喝够了他可能会告诉我。我靠上去,因为我想听。他警告我,他告诉我这可能给我毁灭性打击。我笑了。我俩都笑了。当他拿起录音机让我关掉,他有些笨手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