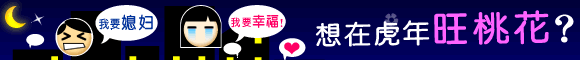十三亿瓶乐百氏--评左小祖咒新版《庙会之旅》
“再见,可爱的小伙子。”左小祖咒在《苦鬼》中向自己的青春告别。“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共产,爱情的唾液,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资产,爱情的拉链”,在《羞辱主义》中他向树枝上撕破的红裙子般的世纪末告别。第一次听到《羞辱主义》是在去树村的路上,祖咒用他在广州买的二手MD机给我听,至今我还难忘——犹如MTV一般——听这首歌时车窗外北京西山褐色的晚霞,那是1999年,NO乐队推出第二张专辑《庙会之旅》。我们驶向树村,舌头他们等着我们开饭。树村,中国摇滚的乌托邦,然而同志,这是庙会之旅,不是伍德斯托克之旅。《庙会之旅》就是世纪末中国血肉模糊的一张脸,请直面它。你永远无法转过脸去,你总忍不住要去舔伤口上的血,祖咒不无悲壮地称之为“对青春的礼赞”,时隔五年,他将《庙会之旅》推倒重来,了断旧债,再一次向青春告别。
那么,请允许我也怀一把旧,怀念我们共同的世纪末。1998年圣诞节前后,NO乐队来广州参加“以音乐的名义”音乐节,《庙会之旅》的歌大多创作于此后,比如《冤枉》就是构思于从广州回北京的第十三节车厢上。五年之后,他再度来广州参加新年摇滚音乐节,新版《庙会之旅》内页出现了他在新年摇滚音乐节的背影。1998年在广州,有观众高声质问台上演出的祖咒“你丫多大了”,祖咒脱口而出:47。但将近六年过去了,他也只有34,还来得及不断向青春脱帽致敬——以前他是决不脱下那顶注册商标般的皮帽的,但现在他无所谓了,乐于让人看清他不是秃顶同志——《秃顶同志》是尚未录制的他的一首老歌——他一直没让我们的脑子休息过。
天真与经验难以兼得,随生猛而来的往往不是精致而是粗糙。这是NO乐队与左小祖咒的分野。《走失的主人》和《庙会之旅》歌曲本身更为出色,更源自本能的石破天惊和直觉的左右逢源,而不是技术尤其是制作层面的老谋深算。只是到了《左小祖咒在地安门》和《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左小祖咒才打磨出大理石的花纹,恶之花赢得了花瓶,狂犬也梳理出每一根挑剔的卷毛。用后两张专辑的技术和经验去重新武装头两张专辑,或许崔健都会有这样的冲动,但第一个这样做的是左小祖咒。但愿《走失的主人》也能重录,但愿舌头、诱导社也能重录,新版《庙会之旅》和他的新专辑相比制作上还有一点差距,但在录制水准粗陋、简直尸横遍野的中国滚坛,左小祖咒已经重树了一个起点和标准。
新版《庙会之旅》只保留了原来三成的录音,当然都是精华部分,比如《羞辱主义》和《苦鬼》中朱小龙的经典吉他和郭大刚的经典键盘,《家父》中Kristian的经典蚊子琴和威士忌提琴,《果皮箱》中胡吗个的经典口哨,以及《羞辱主义》的经典啸吟——这是惟一保留原唱的曲目,像《阿诗玛》和《羞辱主义》这样炫目的歌唱高度今天他自己已难以企及,然而有更多的技艺足以弥补气力。这个人在一开场的《皮条客》中鼓饱腮帮吹奏Kazoo,从第一个怪音便踏上这噪音新长征的不归路,这样的小把戏,包括蚊子琴和口哨之类,正是左氏音乐的亲切新鲜所在。这算不上什么先锋,也不是“地下丝绒”或“音速青年”的徒子徒孙,噪音掩不住民乐小调,这是庙会中杀出的音速青年,再说谁能料到从吉他噪音的深渊会升起十二弦木吉他的朗朗青天,谁能料到噪音新长征的终点却是一曲素歌?
音质鸟枪换炮,丰富的对比和层次感在新版中大大强化。其中最突出的新意是鼓机——鼓机和键盘是“后NO乐队”授左小祖咒两大秘笈——《皮条客》、《羞辱主义》、《冤枉》、《祭日之星》、《家父》都因鼓机而焕然一新,其中《冤枉》更脱胎换骨得令人惊艳。鼓机的强劲气势更符合这张专辑的史诗追求,张蔚作为NO乐队鼓手长于音色和细节表现,力量不是他的优势,那么交给机器来干不是更来劲?和《冤枉》一样,《祭日之星》是另一个堪称化腐朽为神奇的例子,转机也在于打击乐部分,鼓机、印度鼓和中国大鼓的合纵连横使魔幻马戏团般的世界音乐实验丰满坚挺起来。一系列精心微妙的加减乘除带来新的体验,《果皮箱》两把吉他的应和变得清亮跳脱,《家父》加上一点蚊子琴更其迷幻,《除夕》的音效更如贺岁巨片般到最后真的一炮把人轰死。专辑最著名的代表作《苦鬼》和《莫非》也略施手术。《苦鬼》弱化了衬底的噪音吉他以突出朱小龙的主音吉他,从混沌中拨云见日,而《莫非》由鼓机开头改为键盘开头也更为合理。
更令人注目的是《家父》和《除夕》完全换了唱法。《家父》从萧索苍凉变得倔强、愤怒而义无反顾,而《除夕》从一半搞笑变成全盘搞笑,从50%白痴变成100%白痴。此中潜伏着更为险奇的情感历练,还从未有一张中国摇滚唱片包含了如此丰富、貌似矛盾的情感,这是泪与笑悲欣交集的世纪末史诗。活下去,在不义和无爱中活下去,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活下去,除了悲愤的抗争,唯有努力地笑,努力地爱。很少有人能将批判和抒情,将悲壮和戏谑如此融为一体。这是一种伟大的素质,伟大的能力。
美好的一天开始,美好的一天结束,但苦鬼在地狱还有力气赞美吗?据祖咒说《除夕》别名《南方周末》——或许是《南方周末》关于春运民工和春节联欢晚会的报道激发出这首歌,而《苦鬼》不妨改叫《中国农民调查》,当然它也可以是乐百氏的广告歌。新版终于登出《苦鬼》的歌词——中国摇滚最为现实主义的歌词——满腔热血、热泪提炼成那一瓶卖春换来的乐百氏。苦鬼Vs乐百氏,如同地安门Vs天安门,这是他的立场。这个人的作品潜藏着太多的隐喻乃至字谜,比如《莫非》这个歌名和NO乐队的名字恐怕有关,也权作对NO乐队的一曲挽歌;这个人有太多的小把戏,比如新版《祭日之星》开头加了一句“哪里来的汉子,胆量不小”,是先发制人为自己壮胆,《除夕》又来了一句搞笑的“你要小心了”,用戏谑消解了来自现实的威胁。
是的,把戏。如同《苦鬼》中唱的——“我们学会解释自己的把戏”,去工厂里偷一块铁是一个把戏,去李谷一那儿偷一段《心中的玫瑰》(《皮条客》采样)也是一个把戏。我宁可用“把戏”(而不是“艺术”)这个词来破解左小祖咒,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能力,一种将苦难化为赞美、叹息和啼笑的能力。尽管经常表现得像只狂犬,尽管从来不缺乏政治激情,但左小祖咒完完全全不属于上个世纪末甚嚣尘上的所谓中国摇滚的朋克时代,他从来不屑于简单粗暴的宣泄,而听命于艺术和思维复杂性的更高指令。艺术和政治、反抗与赞美并没有混淆。他要的不只是长时间的狂啸,而是经验的丰碑。然而与其说他是摇滚先锋,还不如说是庙会的杂耍艺人,是春运列车上昏迷不醒的醉汉,是边吃桃子边歌哭的扫墓者,是被扔进法院果皮箱的原告被告,是去北方寻找家父的被抛弃的私生子,是用贞操换回乐百氏的亿万民众,是皮条客、流浪汉,是嫖客、婊子,是笨蛋的儿子和脓包的孙子,是十面埋伏的苦鬼——不是十面埋伏的英雄,是“被沉默牵引和失意的人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失血的历史,是坏血的现实,是艰难时世,然而也是义无反顾的歌唱者!这歌声是仰卧在你窗前的最后一颗月亮,是生长在你墓前的最后一棵桃树。
五年过去了,江山还是那一个江山,落日依旧是那一轮落日。《庙会之旅》升级了,而现实继续沉沦,血肉更加模糊。人民需要摇滚吗?还是古装戏?人民喜欢庙会之旅吗?还是隆胸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