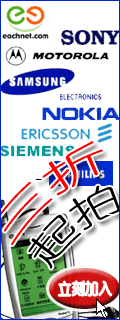|
理查德-克莱德曼又要来了。听说是要举办一场访华十年纪念音乐会。可理查在我的记忆中好象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记得那是70年代末,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被禁锢了十几年的轻音乐在中国大地尚未开禁。但一首《致爱丽丝》的钢琴曲却不知从什么时候、什么渠道进入我的生活,在一些专业艺术院团流传开来。那年,早已厌烦钢琴的我又对钢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此曲轻
松柔和抒情甜美,作为聚会时迷瞪女孩儿的手段那是再好不过了。而且那曲子对于我这个有八年钢琴底子的来讲难度也不算大,旋律也很优美,外行看上去还显得挺牛的。至于这是谁的曲子谁弹的?不知道,谁都不知道。直到几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法国人,叫克莱德曼的弹的。这个名字又让我喜欢。您想啊,克莱德曼--课来得慢。多好哇。这就意味着课间休息的时间长了,玩的时间多了。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那年头,学钢琴的人并不多。我要不是我爸逼着,我才不会学这娘娘腔的东西。学了八年钢琴,我恨了八年爸爸。我更痛恨钢琴。每天得在涂棺材用的油漆刷的钢琴面前乒哩乓啷的砸二个小时。这对于青春年少的小伙子简直是浪费生命!
然而,不知怎么着,也不知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文革中200块钱就卖的钢琴升值了,走俏了,一夜之间又火了。周围那些一年也轮不上二场演出的钢琴家们忙起来了。他们不是又有演出了,而是忙着教起学生来了。买钢琴也在买电视、冰箱、洗衣机之后成为新的抢购点。这下,当年若不是国营企业早就瓦解了的钢琴厂又活了,人们拿着现金在厂门口等着,推出一个,连挑都不带挑的就拉走了。当初琴板上的弦码子得用小锤砸83锤才砸进去,这时候三锤就得活。萝卜快了不洗泥。什么叫质量?谈不上!也没人讲究,因为绝大多数的买主根本就不懂。就知道得买个钢琴让孩子学学,显得对孩子负责。逢年过节的时候在亲戚朋友面前弹段钢琴又体面,又高级。
钢琴在北京老百姓当中从阳春白雪到"人手一个"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而克莱德曼的磁带也象是一夜之间就铺满了大街小巷。到80年代后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几乎家喻户晓。各大饭店是推广克莱德曼钢琴曲的最好媒体。大堂里、电梯里、酒巴里、走廊里几乎无所不在。除了出租车里的西北风、电视里的"可望"风,就再没有能和克莱德曼叫板的了!
90年代了,我终于见着活的克莱德曼了。在首都体育馆,我做为摄影记者爬在台口,用300毫米大镜头一通狂拍。那湛蓝的眼睛,金黄色的头发,裁剪得体的兰色西装,连纤细的手指上的毛都拍的一清二楚。曲子嘛我只记得他弹了几首中国《我爱北京天安门》、《红太阳》和他的《致爱丽丝》。
21世纪了,克莱德曼在中国和浪起来的钢琴风已经不在那么狂热。克莱德曼的浪漫情调也不再那么凸显。然而当年的孩子已有很多人成为了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当年的克莱德曼情歌迷已有很多成为老夫老妻,当年的钢琴厂也合资摇身一变成为名牌钢琴。只有当年的我,依然没有再触钢琴,成为一个听音乐而不懂音乐的混混。陈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