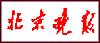《桃姐》:呈现切口 悲喜由你
 《桃姐》剧照
《桃姐》剧照
在《桃姐》背后“发功”的导演许鞍华,用一种插科打诨的语调讲述了这一场本该悲伤的生离死别故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或许她只把这当做一种“对话”自我的途径吧。
有人说,香港电影“新浪潮”导演中,现在只剩下了许鞍华还在坚守最后的“现实主义”阵地。确实,站在2012年往前回望30年,徐克已早是“老爷”,无论是《狄仁杰》,还是《龙门飞甲》,他都用天马行空向好莱坞致敬;杜琪峰也已有些厌倦纯黑帮故事,从《单身男女》到《高海拔之恋2》,都显示对青春爱情的怀念;而吴宇森自从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终身成就金狮奖之后,也用一部《赤壁》正式宣告“倒戈”商业。
从《天水围的日与夜》到《天水围的夜与雾》,许鞍华惯用一种平淡的纪录片手法,不加修饰地把生活的原貌展现出来,如果你感到的是坦然,那么它表现的就是坦然,如果你悲伤,那么它就是悲伤。许鞍华所做的,只是呈现。它撕开一个切口,让你有机会和自己面对面,这种“对话自我”的电影形式,到了如今的《桃姐》,走向了极致。《桃姐》把故事背景置于“敬老院”这一特殊的场景中,不免充斥着对于现代社会反思的意味。“因为我也老了。64岁,单身,开始担心孤独,怕老得太潦倒。”——许鞍华曾如此敞亮地解释她初见《桃姐》剧本的一见钟情。
影片对于现实的不避讳,也把导演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标签稳当落入“实至名归”的噱头,但可贵的是,一切悲伤或者苛责都点到为止,导演只管提供“对话”的环境和场所,怎么说和说什么,都不归她管。影片中刻画过这样的情节——中秋节时电视台带明星来敬老院慰问老人,并大方地发了月饼,但镜头一转,他们临走时又收回了发出去的月饼,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影片没有批判,只是淡淡带过,毕竟,群众有自己的价值观。
影片对于“生死观”的解读,显得异常的冷静,不悲不喜。影片对“死亡”的描摹,采用了陈述性的客观镜头:老人院中一位老者去世后,她的女儿站在画面中间嚎啕大哭,但在画面的左侧,几位老人照常下着象棋、嗑着瓜子。这样的景象可以解读成人心冷漠,也可以理解为生活依旧的坦然。现实中,“生老病死”的客观命题实则充溢着太多主观的不安或猜测,从主旨上说,《桃姐》想要讲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游离在生死之间的故事,但它呈现出一种坦然和笃定,以致观众在看到桃姐的逝去之后并不会心生无边的恐惧或者太大的悲恸,导演这样的安排和处理,也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影片略带阴霾的主题,把一切悲伤点到为止。
如果你看《桃姐》哭了,或许只是因为你想起了你的父母和家人;如果你笑了,或许你从记忆中重拾欣喜的,也是你自己的生活。F10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