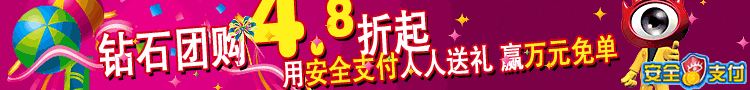
|
|
|
|
《新世纪周刊》:农民导演的无意识记录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4日17:23 《新世纪周刊》
赵一凡 在中国纪录片历史上,由农民拍摄纪录短片是一个新鲜的尝试,他们记录下了自己的生活:琐碎、无计划,但鲜活生动,极度真实 凛冽的寒风里,北京东五环之外的一片院落里,三部新拍摄的纪录片正在放映。2007年的12月29日,对于一些中国农民来说,是一个可以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放映的三部纪录片,作者是三位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的村子2006 这是“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最新一阶段的成果。“村民影像计划”开始于2005年,由 “中国新纪录运动”的代表人物吴文光总负责。活动最终在全国数百位报名者中选择了10位村民,他们来自9个不同的省份,有男有女,年龄从24岁到59岁不等。组织者发给他们必要的摄影器材,并在北京对他们进行三天的短暂培训。 培训之前,这些农民中的大部分没有见过摄像机,不会使用电脑,而培训所教给他们的也仅仅只是机器的开、关、充电,镜头的推拉之类的简单操作。接着这10个人便回到自己的村子开始拍摄,没有主题限制,没有条条框框。 20天之后,他们交上了生平第一次影像作品,无一例外,他们都选择了拍摄自己的家长里短,以及日常生活中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东西。短片的名字有《扶贫款评审会》、《采石场》、《一次作废的选举》、《分地》等第。 由农民拍摄纪录短片在中国纪录片历史上还是一个新鲜的尝试,无论从关注内容、拍摄者、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传播的方式来说,都是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 随后的两年,拍摄与他们的生活同步进行着。他们将摄像机带到了田间地头、结婚庆典,拍家人、拍邻里,拍村民“ 聚赌”、拍夫妻吵架,甚至拍别人眼中的自己。这一次,10人中的王伟、邵玉珍和张焕财完成了他们的第一部纪录片长片,名字都叫作《我的村子2006年》。 吴文光说,片名不是“我们的”或是别的限定词,就是说明记录下的只是拍摄者,是个体眼中的2006年。200 7年4月,这三位农民作者来到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开始对新作品进行后期制作,在第一次作品中就学会“非线”操作的他们,这一次所有的剪辑均由自己完成。吴文光只就衔接和其他细部与他们商量,是个不能缺少的配角。 在有了第一次拍摄经验的基础上,三个人进一步延伸了对自己生活记录的纬度。70到80分钟的片长,是在五六十个小时的素材上剪辑而成的,投入程度可见一斑。张焕财是个地道的关中汉子,整部影片贯穿着热辣直白的陕西方言。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与妻子的对话,而这许多的对话都是在其妻不知道的情况下拍摄的,颇为有趣。“俄(e)给你拍个纪录片! ”“俄(e)不要那个!”“那你要啥?”“俄(e)要钱!你不要再瞎日鬼了,拍那个啥!”“那俄(e)咋才是有成绩? ”“把钱拿回来就是成绩!把娃管好就是成绩!”这种鲜活的夫妻对话,有理由让我们相信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是非对错,没有价值判断。 记录自己的生活 三位的作品中都涉及到了村民的日常消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娱乐活动。男的就是打扑克、往土坑里掷色子,女的就是东家长西家短唠家常,再不就是逢年过节扭个秧歌。对于这一点,有的观众说这反映了农民精神生活的贫乏,但也有观众表达了对这种无计划和琐碎的喜爱之情。“你怎么知道他们不高兴,我看他们挺高兴、挺充实的!” 久居城市里的人习惯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对事物做出评判,但是这些就是村民们最日常、最普遍的生活,无法改变。结婚典礼上,新娘的父亲对到场的乡亲们说:“我也没啥可说的,大家吃好喝好、喝好吃好!”这样直白的语言,背景就是走了调的婚礼进行曲,这种表达很难用主观的标准来判断是贫乏还是充盈。 王伟的片子中,一位村民斜躺在自家的炕头,电视里正播着某段“有中国特色”的新闻,那位农民“嘿嘿”地笑了,黑暗中的观众也笑了,默契的达成就是这么简单。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理解者对被理解的客体应持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这种眼界更有助于了解和阐释,而非站在门外的对文本层面或带有表演性质的打探。拍摄者作为“场”中的一员具备观察的天然优势。 邵玉珍的片子中有一个片段,某电视台的记者去她家采访,让他们讲讲农业税取消后的感受。邵玉珍的老伴儿张大哥在主持人的指导下反复背着“台词”。“我们家种了多少亩地,农业税没取消前,我们家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农业税取消后,我们家的收入又是多少,这等于为我们家节省了多少钱,这些钱就全装在我们自己口袋里了”,电视台的记者示范着。张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被电视台采访也是头一回,在记者的“摆布”下,他努力地背着,然而老是出错,引得观影者频频发笑。而此时的邵玉珍拿着DV在另一端全程记录下了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也就是她老伴儿的真实状态。这成为一个颇耐人回味的片段,被观众多次提及。 表演式的摆拍和客观的记录在同一个时间被呈现出来,纪录片的魅力不经意间被生动地刻画。邵玉珍在提到这一段时说:“我并不是想反映别人,就是想记录一下我自己的生活,我拍别人的初衷是这样。而别人(电视台)是想用他们自己的想法让我做他们的演员,他们已经把那个思路确定下来了,让我按着那个路子走,我感觉挺不舒服的。当初我挺好奇的,我不知道这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拍我老伴的这个,我就是觉得挺好奇的,想把它记录下来。” 纪录片的残酷和无能 对于其他村民作者来说,情况也或多或少有着相象。参与民主建设、发表呼声等大而陌生的话语,也许是他们没有想过的,但在长期地跟踪拍摄中,不经意地完成了对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生态渐变的记录和“文化持有者”本体的表达。 和人们印象中的纪录片不同,这些由农民自己拍摄的纪录片没有主题、没有规划、没有拍摄路径,拍摄技术的运用以专业水准来看也较为粗糙,然而吴文光有意地将这些“原生态”素材保留了下来,并给以鼓励的目光,也许这种无意识、无假设的拍摄也才更加接近纪录片的本源。 “纪录片是残酷的,因为它真实;纪录片也是无能的,因为它什么都改变不了”,用一种冷静的姿态,吴文光坚持着对“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的实践。“记录下来它就有了,不记录下来它就永远也不会有。” 有的事情,我们当下不做,也许以后就永远也不会去做了。也许这些村民拍摄的纪录片对乡村民主这个宏大命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至少多了一种途径让他们说出了许久以来想说又没有地方说的话。是排遣、是呼吁,或者就是无意识的记录。我们对忠实记录历史的人们是否该抱有些许的敬意,无论他以哪种方式、无论那是怎样的语言。
【发表评论】
不支持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