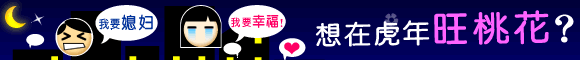文汇报:柏林影节,好大一枚艺术烟雾弹
拿下柏林影展最佳导演奖的《影子写手》,改编自罗伯特·哈里斯的同名畅销小说,像我们早已熟悉的那样,波兰斯基个人的影子覆盖了原作,这仍然是一个疯狂世界里的受害者的故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这个母题是波兰斯基的情意结,从某种程度上说,亦是柏林影展那道 “政治正确”的藩篱——入围,过的尚且是“艺术正确”这道门槛,得奖,就不是(至少不全是)电影本体说了算的。
本届柏林电影节入围名单公布时,人们确实对60岁的柏林影展抱了期待,因为看到若干有趣的面孔,比如温特伯格,比如鲍姆巴赫。这些名字的背后,通常意味着一部有活力的电影。才子们到了中生代的辈分,就像轻易不失手的厨子,唯放心矣。然后呢,然后会觉得影展在获奖名单出现的前一刻就结束了,其后的金熊银熊与获奖感言,是在重复我们年复一年的质疑:评选究竟是垂青,还是垂怜?大约如今做导演,投胎很重要,仍是殊途同归的题材,衬上“挣扎的第三世界”的背景色,就握住了修成“正果”的筹码。真的,在欧洲的腹地,在那名为艺术的目光下,“来自第三世界”所附加的西方偏见,倒成了财富。
玫瑰,还是荆棘?
这次拿到金熊奖的《蜂蜜》,在很多方面让人想起前两年在欧洲被捧上天的《风与时光》。都是土耳其远山里的故事;主角都是孩子,《蜂蜜》是寻父,《风与时光》是弑父,终究是相通的,父亲,是必须要过的坎。两部影片收获的评价也大同小异,无非是“无与伦比的诗意优美”或“土耳其电影的巅峰”,话说得那么满,欧洲人也不怕自相矛盾。《蜂蜜》纵然诗意,而那些过分优美的长镜头,更多是导演个人耽溺于孤独和安静。如果剥除了土耳其的背景,没有了长镜头下的森林和土壤,没有了异国趣味的采野蜂蜜,很难说《蜂蜜》的童年往事比《嚎叫》的垮掉青春更动人。只可惜,全世界已经有太多年轻人能背诵金斯堡,更何况,德国偿不清的心债,是土耳其,不是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
再来说今次显得很委屈的《在路上》。对它最初的兴趣,是因为导演兹巴尼克触及了窒息的生活状态下的男人女人不同的应对态度,两性之间的误解与和解。至于战争终了或者原教旨主义,这些是她出身波黑所不能摆脱的胎记。然而在柏林,包围《在路上》的话题是战争和宗教这些附件,开始时,说这电影长了张标准的柏林面孔;结束时,说这电影就是长得太周正,才遭柏林弃。两番说辞,说得导演里外不是人,冤枉得很。
若说《在路上》是悲剧,拿下最佳编剧奖的《团圆》就是喜剧。我以为,王全安这些年的电影里始终有一股气脉,那就是一个女人在两难境地里的选择——徘徊在伦理责任和情感冲动之间,是承担道义,还是顺从内心?赴台老兵是一个多少有点敏锐的话题,但作为观众,我并不愿意纠结在这个话题上,因为它妨碍了这个电影原本可以抵达的情感深度。而这显然是我的一厢情愿,《综艺》杂志的标题就出卖了影展看客的价值取向:王全安用温柔包裹尖锐。果然,政治话题更能撩拨艺术布道者的神经。《在路上》和《团圆》的一悲一喜像极了一个太简单的寓言:在一条长满荆棘的玫瑰花道上,我们是看到玫瑰,还是看到荆棘?
鲍姆巴赫是又一个处理“男女问题”的行家,人称“当代美国的戈达尔”。《格林伯格》延续了之前《鱿鱼和鲸》、《婚礼上的玛戈》的趣味,仍是关于布尔乔亚阶层好男好女的心理建设,在相似的客厅和书房里,鲍姆巴赫总能聊出点新鲜意思。原以为《格林伯格》和《在路上》、《团圆》是能够三分春色的对手,结果,没有战乱流离、没有信仰冲突、没有一弯海峡,鲍姆巴赫只能做陪客。
最初是法国人在黑海边掀起了罗马尼亚新浪潮,现在德国人也来推波助澜,这就成全了《口哨》。不用辅助摄影工具,不用辅助光源,手提摄影,没有配乐,没有交叉剪辑……关于《口哨》的这些描述,是不是让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是的,在电影美学的角度,《口哨》是道格玛95的门徒。道格玛95,原是温特伯格和拉斯·冯·提尔在1995年提出的顽童般的口号,1998年温特伯格的一部《家宴》,是这一美学风格的登峰造极之作,而后他渐从年少的狂语里毕业,却看着多少晚生走在他的阴影里。《口哨》也没能幸免。弗罗林·塞班在《口哨》里做到的全部,温特伯格十几年前就做到了,甚至走得更远,昔日伯格曼评《家宴》“如果镜头不要晃得那么厉害,就没有瑕疵了”,这评语,是罗马尼亚人只能遥望的。
《口哨》拿下仅次于金熊的评审团大奖,我倒是愿以最大的善意揣测,这是评审团含蓄地在向带着《潜水艇》来到柏林的温特伯格致敬。但是既然正主在,我们又何必看青涩的画瓢?《潜水艇》近乎无情地让看客明白,素简不等于粗糙,克制不同于简陋,而那在暴力和泥泞中飘摇的诗意,更是不可复制的,也是这些年来我们始终放不下温特伯格的原因。
评的是背后的话语权
以艺术为标准还是以政治为标准,影展的这道选择题做的是电影版图上的文章。从日本新浪潮算起,经过了中国大陆的第五代和第六代、香港地区电影、台湾地区电影,经过了伊朗、俄罗斯、罗马尼亚、土耳其等等……柏林影展以及与它同质的一系列欧洲艺术影展的“火”,在电影工业的外围烧了一个圈。艺术影展养活一群在工业环境下生存能力低下的摇篮宝宝,投桃报李,原是无可厚非的——前提是,那些当真是艺术的选择,至少,必须倚重美学层面的垂青。而今年的柏林影展一如既往地让人扫兴,便在于,艺术又一次成了烟雾弹,评的是地域、是话题,最后,还是政治。既是政治的选择,背后就有话语权,这话语权无关电影工业的格局,是塑造世人对工业腹地以外的电影风景的想象——从菲斯·阿金到策兰,从内厄·哈丹到卡普拉诺格鲁,我们是不是要约定俗成地以为,土耳其电影等于没故事没台词和挥霍的长镜头?土耳其电影还有没有第二种面目?上述几人皆是吃着法国学院派的奶水、拿着欧洲电影基金,奋战在柏林、戛纳和威尼斯,把这些新欧洲人捧成土耳其电影的宗师,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人民答应了么?多少年来,俄罗斯人的长镜头让欧洲腹地的影评人欲仙欲死,从《母与子》到《回归》,以及今次的《如何结束这个夏天》,仿佛俄罗斯电影的传承,只剩塔可夫斯基一脉。竟是昆汀的电影让我们想起,还有爱森斯坦呢!又有多少人知道,俄罗斯国内出现过何其多精彩的类型片?若不是东邻日本,发达的美少年文化和影剧产业早就渗透进我们的娱乐生活,不然,要是借着德国人法国人的那扇窗,我们看到的东洋电影想必也是另外一番“艺术”风景吧?
放出艺术的烟雾弹,玩政治标准的游戏,也就罢了;执着话语权柄,玩出指鹿为马的把戏,未免失方寸。这把戏玩得多了,影展的公信也就成了很傻很天真的笑话。话说回《影子写手》,波兰斯基自己的身影交叠着出现,时而是惶惶终日的影子写手,时而是被政敌攻讦的首相先生——奥斯维辛的记忆或风波不断的强暴案叠印在电影里。更有好事的,在这里看到了托尼·布莱尔和伊战的影子。现实的飞短流长让这电影非常地“不单纯”,有些时候,电影恰是因为这点“不纯粹”才格外有意思。就这一点来说,60岁的柏林影展终究值得我们开瓶香槟——为了那些有趣的电影,至于奖项,只当是个余兴节目。本报记者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