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的忧伤》:喜剧并不廉价 意义不止于好笑
 话剧《喜剧的忧伤》剧照
话剧《喜剧的忧伤》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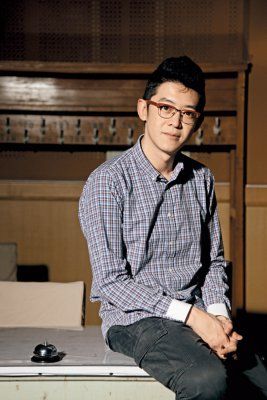 导演徐昂
导演徐昂
今夏京城话剧界最大的热点无疑是《喜剧的忧伤》。这部戏的票房被形容为“疯狂”,离正式开演还有两个星期,各个网络订票点就已经无票可售,“黄牛”坐地起价,每场演出开始后尚有人等在首都剧场售票处期待退票。
戏火成这样,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当然是陈道明。“这部戏能够请到陈道明是充分考量他在商业上的影响力的。”《喜剧的忧伤》的导演徐昂告诉本刊记者。陈道明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从业30年来,未演过话剧,话剧已变成他的一个“夙愿”。迟迟未能成演,是因为他对角色的挑剔,去年“人艺”请他出演话剧版《围城》里的方鸿渐,也被他推辞了。
故事其实很简单,只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新到任的审查官,专门负责审批剧本,缺乏笑神经,最讨厌喜剧,凡是看到喜剧剧本就百般刁难不通过;另一个是专门写作喜剧的编剧,长期和此类审查官打交道,谙熟这个审查系统的种种关要处,身处一个专演喜剧的剧团,以让观众发笑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两人为了一个名为《朱密欧与罗丽叶》的喜剧剧本能不能通过,针尖对麦芒碰到了一起,拉锯战一拉就是7天。
“这两个人都是A型血。”徐昂告诉本刊记者,“这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标准,所以才会有长达7天之久的兜转和推进。”
剧本改编自日本著名编剧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1996年首演于东京。10年后,英国老维克剧团将其改编后在伦敦西区的里士满剧院上演。一个亚洲戏里的冷幽默能被一个老牌欧洲剧团看中,“这很难得”,徐昂说。
改编时,首先是背景设定。“都是‘二战’,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并非捍卫主权,而是向外扩张。剧里的情绪是反战,而对中国人来说是保家卫国,匹夫有责,所以要改变原来的含义。”徐昂说。因此剧中的审查官被设计为一个刚从战场负伤归来的国民党军官,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这样,笼罩原作的一层淡淡的悲剧意味也被取消了,结尾处伴随着《向斯拉夫女人告别》这一盟军音乐的雄壮节奏,编剧走向的是光荣和希望,死亡在这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原作中的命定结局。
剧本结构未改动,挑战在如何保持原剧以文字幽默见长的特色。那句贯穿全剧的“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吧”配上何冰设计的滑稽动作,让观众不断捧腹,却让徐昂绞尽脑汁。“原作的日语台词翻译成中文,是‘裤衩失礼了’,前边是‘裤衩’这种大白话,后边用的是一个敬语,这俩东西凑一起,在日语里听起来特搞笑。但是它里边多少还带点儿自我批判的意思,就是我要向你道歉。”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挑了《雷雨》里的这句词。“有点儿自省,有点儿贫,还耳熟能详,本身又是舞台语言。”
徐昂对戏里许多调侃北京人艺的地方并不讳言,他说:“因为我的生活印记,就是北京人艺。”寻找这些事关北京人艺的印记,也变成了许多人观剧的乐趣:那一窝小黄鸟,是《茶馆》里宋二爷养的鸟;噎死希特勒的窝头,则是《窝头会馆》,据说原本写的是粽子,上台就变成了窝头。“调侃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徐昂在采访中极力澄清,“其实是一种互文,文化生产集团中互相之间其实是共生关系,我们需要这种文化幽默感。”
“互文”这个概念,也被徐昂拿来理解这个戏的本质内容。在他看来,这部剧和剧中那个叫做《朱密欧与罗丽叶》的剧本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实际上写的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版中,他借用《白蛇传》和“梁祝”的典故将其汉化为《许山伯和祝英蛇》,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如果我们把这个审查官和编剧变成一男一女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关系。”他对本刊记者分析道,“如果我们真的分析它的文本结构,你会发现,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也见了7天的面。这7天里,从一见钟情、想要摆脱自己的身份、相互投入对方的世界,到身份重新禁锢和束缚他们,再到外界的强压,最后导致两个人的死亡,结果两人硬性地分离,这本身和这个戏的结构是完全一致的,是重叠的。实际上,这个戏是通过颠覆和解构,形成一个对古典主义戏剧的敬礼。”
一部将近两小时的戏,从头到尾只有两个人,他们之间不断变化和转移的矛盾焦点便成了所有的看点。“审查”无疑是这两个人冲突的来源,许多评论家和徐昂谈这个戏,首先便谈“审查”及其相关含义。但在徐昂看来,“审查是维系我们把这个游戏做下去的纽带而已,要不然,这两人为什么坐一屋呢?”于是,每一幕结束时,都是审查官以审查不合格的名义向编剧提出一个新的难题:“明天,你明天再来。”
在剧中,审查官和编剧都没有名字,以职务互称。这难免让一些人用群体概念去进行解读,而这恰恰是徐昂想要讨论的:社会身份和个体本身,到底哪一种更接近人的存在本质?我们在何时以群体意识对待对方,又在何时以个体意识对待对方?究竟哪一种状态是人们真正想要的?
“职务、社会等级是一个很无聊、但是所有人必须不断参与其中的游戏。比如这个戏里,文运会(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六不五要’,其实是最无聊的东西,哪儿的点心好吃,怎么养鸟,那才是人与人之间最想聊的东西。个体意识这部分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把生活全部着眼于群体意识,就是集体不快乐,集体无聊。”徐昂说。
戏排到后来,考虑到演员的负担,要把时长控制在两小时以内,因此需要删戏。演员问徐昂,要不要把养乌鸦的情节删去。这并不是没有先例,日本人在把这部戏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就将乌鸦的部分全部删节,但是徐昂坚持不删。“这部分吧,就是聊闲天儿,但是你说人的状态,不就是聊闲天儿吗?”他反问道,“我一直想问,什么是正事儿呢?人坐在一块儿聊聊这乌鸦怎么养,这可能才是生活本身的意义。”
陈道明扮演的审查官,不是传统意义上粗鄙的审查官,随身携带的小本上记着莎士比亚,有那么一点儿文化素养。何冰扮演的编剧,也不是一个不识世故的知识分子。二人因为社会职位而势不两立,最终却通过“与审查本身并不相干”的各种碰撞,在剧中发生了奇妙的彼此接近和转化。在审查官披上法海的袈裟做戏的一刹那,与他配戏的编剧甚至坐到了那象征权威的办公桌后面的高背扶手椅上。此刻的两人为了一个共同的戏剧目标,都进入了痴情忘我的状态,剧中审查官喊出的那句“戏比天大”的台词无疑是最好的注解。
“真正接近对方永远不是靠你的社会角色,而是靠你人的那一面。他们两人接近的过程,或者说互相转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两人抛弃自己的社会属性,来完成自己个人属性的这么一个过程。”徐昂说。
结果,《喜剧的忧伤》达到了喜剧效果:演到第二场时做了一个统计,全剧7幕总长118分钟,观众笑场次数49次,其中上半场29次,下半场20次。导演和两个演员都松了一口气。上场之前,三个人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观众到底会不会笑。
原本这个戏打算在小剧场上演,改成大剧场后,舞美设计要改,表演方式要改,演员的心理状态也要改。偌大的舞台,布景无变化,只有两个人,怎样在两个小时里不断保持观众的兴趣?在首演前,一贯严肃的陈道明甚至都不怎么和导演交流自己对这个戏的个人看法。直到演出成功了,他才说,喜欢这个戏一是因为戏里讲人性的那一面,二是它也没影响让观众发笑。
这部戏原名为《笑的大学》,因剧中编剧从属的那个剧团名为“笑的大学”。英国人改编时,将名字改为《最后的笑声》(TheLastLaugh)。唯独在中文版剧名中,“笑”的字眼却隐匿不见了。“《喜剧的忧伤》,这是一个中国式的题目,也唯有在中国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徐昂说,在日本和英国,观众并不像中国观众那样,进剧场前必须有一个可供升华的形而上的主题。“在这些国家,更关注个体的生存状况,不太关注所谓群体生存的状况。在中国,一般一关注就是群体,要不然不构成你关注的合法性。所谓喜剧的忧伤,在这部戏里到底存在不存在,其实我特别不确定,用这么一个看似崇高但很模糊的概念,也是我的一种调侃。”徐昂说,“不过大家都接受了。”
为喜剧正名,正是徐昂想要做这部戏的基本动机之一。笑,是喜剧,不笑,也是喜剧,他反问道:“你什么时候看卓别林的东西真正笑过?”在徐昂看来,喜剧如今在中国已经被妖魔化了。一个专演喜剧的剧团,会被认做是一个廉价的剧团。“但是喜剧本身并不廉价,让人发笑是它的目的,但它的意义并不止于好不好笑那么简单。”他说,“笑不是按摩,而是一种阻断,像布莱希特的间离法那样,让观众自觉虚构与现实的区别,这一时刻,我们认识到自己并不是沉浸在梦里。”
(责编: 柳星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