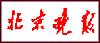评论:回忆音容笑貌挥泪送宗洛
 黄宗洛
黄宗洛
宗洛走了,令人悲伤,令人挥泪,更令人为他生前没有圆上扮演“百怪图”的美梦而深深地遗憾和惋惜。 面对案头的那幅微笑着的遗像,笔者仿佛在与宗洛轻轻地交谈着——
他说:“我演了多半辈子戏,从来不是红花,偶尔有幸配绿叶,多半演的也是一些没名没姓的很不起眼的群众角色。什么警察、宪兵、特务、土匪、二流子……还有那些卖报的、卖梨的、蹬车的、跟包的、扛枪的、站岗的、看门的、要饭的、吹喇叭的……屈指数来,不下半百。”还说:“在话剧舞台上庸碌半生的我,只不过是艺坛百花丛中的一株小草。我对所扮演过的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十分珍视,每个形象都渗透着自己的心血和劳动。”
我说:“这是你的艺术宣言,难能可贵。”
此刻,我忍不住地想起了宗洛当年在扮演《智取威虎山》中小土匪黄排长的情形。小土匪登台总共不到五分钟,台词只有两三句,请看他被解放军打败回到山上的舞台形象如何:先看头上,每一根头发都是立着的,那是打上肥皂再往上梳并且晾干的结果;他通过不断地“变脸”,形成了直眉瞪眼的“惊弓之鸟”;他还把上嘴唇里塞了棉花球变成大包牙,说话囔囔的:左边的耳朵被子弹打没了,他用橡皮膏贴死再涂抹油彩,鲜血淋淋的样子;右臂受重伤不能动弹,临时用一条旧绑腿捆上;手腕上套着几副抢来的金银镯子和几块手表;下边有一只受伤脚却包着原来戴在头上的大耳朵棉帽;腰里女用的绸坎肩里,还别着一杆离不开的抽大烟烟枪……他登台以后就一直跪在座山雕面前不动,然而可以说正是这些“从头到脚浑身都是戏”,正是这些想象力丰富创造出来的细枝末节帮了大忙,征服了观众。
大约他看出我那回忆往事的神情,边赶忙解释说:“过去这种没啥‘油水’的差事经常摊到我的头上,我很少因此闹情绪,从不怨天尤人,也并不因此而颓废消极,无所作为。我觉得这反而给一个演员更多更大的创作自由,可以找更多的难题来磨炼自己演技。好莱坞从前有一个大演员叫却尔斯·劳顿,号称‘千面人’,我从小就佩服他的演技。我的志向不大,告别舞台之前能凑够‘百怪图’,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说:“这是你的美丽梦想,应该心想事成的!”
他又有些激动地说:“我爱春光,我爱新鲜的红花和衬托它的绿叶,我也爱伴随着红花绿叶的生机勃勃的小草。我愿意为它们贡献出自己的一生!”
我不平静地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够了,足够了,这些完全能证明你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话剧表演艺术家。你将一个个本来能让人忽略、忘掉的小角色,演得如此真实可信而又鲜明生动。你充分实践了焦菊隐先生指导的美学主张——‘以少胜多’(登台时间少、台词少)和‘以多胜少’(服装多、道具多)。有人说,‘北京人艺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你就是那不可或缺的‘龙’和‘虎’!”
啊,我突然意识到宗洛并没走,他塑造的各种人物形象将驻留在观众心底,永远不会离去,永葆艺术的青春。
宗洛,我祝贺你又留下来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