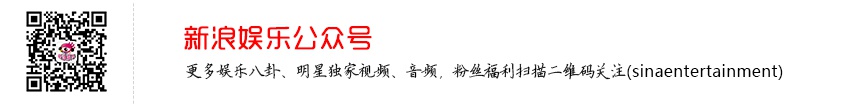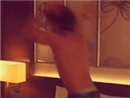《刺客聂隐娘》舒淇
《刺客聂隐娘》舒淇
聂隐娘的形象,诠释着艺术家的孤独,“艺已成,惟不能斩断人伦”,侯孝贤每一次送往国际影展的作品,都像是一场“刺杀行动”,是瞬间光芒,随后又回归孤岛般的沉寂。
不走古风转向写实
侯孝贤在戛纳散场的时候,对记者很不耐烦,一方面是《刺客聂隐娘》(以下简称《聂隐娘》)没能拿到大奖,另一方面则是对媒体的失望。他骨子里清高,向看不懂的观众保持着自己的姿态,这就是“青鸾舞镜”,一种艺术家的narcissim(自我陶醉),青鸾舞镜只见同类而鸣,就像是西方文明中的水仙花少年,夹杂着一种自恋。作为艺术家,侯孝贤肯定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在这条“一个人,没有同类”的道路上,他也渴望着知音,而不是大众的误读、盲目崇拜或者无端诋毁。
聂隐娘的形象,诠释着艺术家的孤独,“艺已成,惟不能斩断人伦”,他们每一次送往国际影展的作品,都像是一场“刺杀行动”,是瞬间光芒,随后又回归孤岛般的沉寂。电影里有几处刺杀,过程都不长,前期铺垫却费了不少笔墨。譬如作为背景音的鼓声就起到了很强的渲染效果,这种鼓声出现过四次:第一次是聂隐娘遵从师命下山刺杀田季安,伴随着字幕出现;第二次是精精儿出现在白桦林之后;第三次则是田兴被发配;第四次则是胡姬差点被纸人谋杀,这一次稍有不同是伴随着一种胡笳的声响,以及其效果的轻诡,伴随着那种雾化产生幽魂效果。
侯孝贤作为一个艺术家,正是陶醉在这样的技术细节里,每一个场景,每一个转折,看似普通,实则独具匠心。没有同类的作者道路,就是以这样的潜在元素制造沟壑,期待着知音解读,发掘他埋下的言外之意。
而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看懂侯孝贤的电影,就像用“东方美学”为其贴标签就是对他误读一样。侯孝贤其实是个深谙西方技巧的形式高手,他在一个时期的观景台式固执取镜之后,恢复了镜头的运动,《聂隐娘》四分之三的镜头都是运动镜头,它纵然运用轨道和摇臂,但因追求运动之“微”,并没有破坏那种静态美。这也造成了侯孝贤的难以归类,比如说《聂隐娘》依赖黄文英的美术,却无意做成costume drama(戏服剧);它改编自唐传奇,却不走那种奇谲幽古之风,而是转向“写实”。
影片中的武打动作,既没有神仙法术,也没有威亚乱飞,侯孝贤把各种交锋都控制在近身决斗的尺度上,最典型的就是片中的两次决斗,虽不复杂,却意境空灵,精精儿碎开的面具,以及师父嘉信公主衣服上裂开的口子,隐喻着一种高手极致的对决及其背后的仁慈。
情节省略制造沟壑
《聂隐娘》的另一个特点,是它蕴含着大量的情节省略(ellipsis),这一次的省略甚至超过了侯孝贤以往的任何作品。我们可以从片尾字幕上看到很多的角色,但在成片之中都被剪除,譬如高捷和戴立忍[微博],这也意味着侯孝贤其实拍摄了很多的素材,初始也很完整,情节亦很清晰。倘若我们再回去读影片的剧本,我们会得到很多的补充,然而在电影里我们很难看到其中清晰的逻辑——倘若你不熟悉它的背景的话。因此这种后期剪辑造成的省略,成就了侯孝贤风格的超验式的链接,这也是他有意造成的沟壑,但是只要你慢慢品读,你就会发现那所有疑问都有某种潜台词为其填充,导演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着这种阐释工作。
侯孝贤于本片的另一个创造,是他用映射着烛光的纱幔摇摆,制造一种水波荡漾的效果,因为这些都是典型的东方古早道具,所以可以算是独创,这种运用丰富着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所阐释过的光学理论,而影片中类似的许多创造性的试听使用,也许得要后来人评价。比较有意思的是,国内观众对这些似乎都不太感兴趣,而是倾向于给侯孝贤贴上“东方”的标签,把戛纳获奖视作一种东方的胜利,在一种无意义的崇拜中实践着叶公好龙的举动。于是《聂隐娘》在隐约之中,仿佛成为一面铜镜,让作者顾影自怜,也让当下舆论浮现略有虚伪的文艺。
青鸾舞镜,既是影片中的嘉诚公主,也是聂隐娘,当后者明了前者的家国大义,她也在自己的人生中作出了选择。这就是知音,高山流水,绵绵无期,成为侯孝贤的共鸣点,以及他在“一个人,没有同类”的江湖走下去的寄托。□灰狼(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