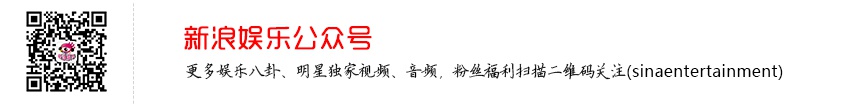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路边野餐》“摩托车回收”版海报
《路边野餐》“摩托车回收”版海报
【文化谭】
电影有时是不需要理解的,它要的只是感受。例如《路边野餐》这样的电影,关心的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些不易觉察的诗意、那些稍纵即逝的灵魂的火花。它们在无意义的漩涡里,勇敢地道出人世终将虚妄的真相。
1 当今华语电影缺“人味”
最近一段时间的观影,在数量上,对华语电影没有以往光顾得那么殷勤。原因种种,但最重要的是,不少有识之士,认为现在的电影,要不不拍,要拍就给1990年以后出生的男女看,他们这么想,也是这么表态,并付诸行动中去的。而我这样的观众,他们是不放在心上的,可由于职业惯性,我虽不看他们的脸色,但得看他们制作出来的“产品”。每次看时,总觉得他们不尊重我还是小事,其实他们也未必看得上他们的那些受众——甚至包括他们自己。
人之为人,还是要点尊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十几年的华语电影,最缺的其实就是“人味”。这些没人味的电影,常让我怀疑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从来没有长大过,从来没有年轻过,当然也从来没有爱过。那么能不能,为一些人所具有的意味、韵味、况味去承制一些电影,为那些不被孤独左右、不愿意把事物一分为二的人去经营一幕延绵的影像、一段描摹灵魂状貌的视听呢?也就是说,能不能去服务那些沉静的知识分子、那些不慕虚荣的电影青年呢?难道他们不是“观众”二字所赋予的一分子吗?难道非要把观众的定义规定到如此逼仄,如此单调,才能毫不脸红地迎来一个满谷满坑的电影盛世吗?
2 毕赣拍出了一种复古的诗意
就我个人而言,《路边野餐》是一种提醒。它虽然打破了中国当下电影的诸多常态,但这个常态实在太容易打破了。这个准九零后的年轻人拍摄的作品实际是一种复古。在电影还是伟大的哑巴的时候、在它牙牙学语的时候,就试着去触碰我们内心深处那与时政、纲常、性别乃至历史无关的事物,去尝试那种超越语言的不是表达的表达。电影有时是不需要理解的,它要的只是感受。就像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说月亮升起来了,惊动了一只飞鸟。这儿没有目的明确的微言大义,只剩下无须答案的广阔天地。这是我个人对诗意本身的观感,而非“诗言志”后成为某类意识形态的工具和帮凶。基于此,你才能真正与《路边野餐》,或之类的电影去会晤,去领受与触手可及的现实平行的另一端“宇宙”。
欧美和日本,从默片到现在,都有大量的去映照非现实形态的光影,去打捞我们的梦境、去探寻我们的潜意识。如布努艾尔的《一条安达鲁的狗》、雷内·克莱尔的《幕间休息》、敕使河原宏的《砂之女》。也包括《路边野餐》所致敬的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阿彼察邦·韦尔斯哈古和侯孝贤。这类电影关心我们内心深处那些不易觉察的诗意、那些稍纵即逝的灵魂的火花。它们在无意义的漩涡里,勇敢地道出人世终将虚妄的真相。在我看来,这是电影,也是一切艺术的最高形态。曹雪芹的《红楼梦》、徐渭的狂草、莫扎特的音乐、塞尚的油画都是如此。
3 诗人与流氓可以毫不违和
我曾在一次座谈中提及,若真想提高品位,“童心”是最要不得的。原初的观影状况,无非是关心谁好谁坏。所以,那些天真尚存之辈所在意的还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而非正邪如阴阳两极般此消彼长;让他们心动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对更艰难的“眷属能否终成有情人”却不愿深究。那些更模糊、更灰色的地带所裹藏的人心之起伏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注目。
拿《路边野餐》里的主人公陈升来说。他有两个身份,即诗人和流氓。人们对诗人这一身份的理解,要不就是因久不见阳光而变得面色苍白,要不就死钻牛角尖而忘了边幅。影片中的这个叫陈升的诗人却以他特有的烟火气,不仅能把诗念出来,更能把诗静静地放在心底。当然这个诗人也有着“混社会”的过往,但比《老炮儿》的那几位,混得更加沉着,也更加艰难。不管是诗人还是流氓,主人公陈升都没有卖弄这两个身份,去炫耀、去生硬地摆弄出一副忽高忽冷的姿态来。这两个身份所带来的宁静与噪动,在陈升这儿,是如人饮水般,冷暖自知。
《路边野餐》最吸引我的,就是这样一位不计虚名的诗人,一位并不想耀武扬威的流氓。若把这两个身份扩大的话,我想会有太多人闪过这样的信念,那便是我要是成为一个诗人或流氓,该多好。而且这两个愿望此起彼伏,并串联起你对生活的全部幻想。我在生活中见识过这样的诗人和流氓,但在中国电影里,真还是第一次看到,但愿不会是最后一次。
4 任何解读都可能是误读
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路边野餐》从《金刚经》里延伸出来的那些玄之又玄的意韵,也无意责难因低成本所带来的硬技术方面的粗陋,又或者导演本身在调动语言上的那些急于求成之举。更不愿辨析墙上的钟,逆行的火车,以及那段不得不提及的长镜头。当然,还有很多影迷颇为关心的,片中哪些段落为现实,哪些又是梦境,以及它们的分界点究竟在何处?在我看来,这些并不重要。也许任何一种穷尽心智的解读都有可能是误读,连毕赣本人的阐述也未必靠得住。对于泛意义上的观影人群,不管你出于何种缘由,观摩到这部疑似有违电影常态的影片,并能获得全新的观影经验,这才是最重要的。而那些有一定观影量的影迷,若放阔心境,进入到那一片潮湿的地带,也就足矣。
就像前文所述,我现在回味《路边野餐》更愿意从最庸常不过的状态里,从陈升的两个身份里,去找寻那陌生的真实。好比那段四十多分钟的长镜头里,所讲述的两段爱情。一个总被人欺负的小伙子卫卫总是紧紧跟随着一个意欲远走他乡的姑娘洋洋,姑娘好像被小伙子的诚意打动,却又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份诚意。又或者是陈升极其熟练地与一女子搭讪,让那女子有了近乎神秘的心动。这两段爱情,一个欲语还休,一个放任自流。就是这些在我们的日常动态里,极易散落的一地鸡毛,一旦与记忆的裂痕、梦境的穿梭、意识的流淌交汇在一处,就能互换些光亮。人生也正是有了这些可为人道或懒于或难以启齿的隐秘,它才有了一副迷人的景观。
当这个长镜头结束时,陈升说“真像一个梦”。有人马上解读在那个长镜头里的洗发妹就是他的前妻,那个小镇青年就是他的儿子。这样的理解也未为不可,只是还是把这部电影的境界窄化了。还有人为老混混这句直露的独白惋惜,好像把全片空灵的意韵坐实了,也就连累到影片的这种强化,具备肢解的味道。我更愿意把这看作一个“幻觉”。一场梦醒之后,我们往往很快能进入到与现实打交道的情境中。而幻觉不是这样,幻觉是置身于现实,但又脱离了他人的教诲和个体的经验。于是,你就在无从解释中,与现实有了一种可堪玩味的十指相扣。按朱自清的话说,在这一刻,你是自由的。
5 电影让人获得陌生的真实
从电影的接受美学出发,电影是服务于人类的偷窥心理的。与《路边野餐》的相遇,在我这儿,也仿佛看到了一个人的隐私,只是这隐私不会给你提供幸灾乐祸的快感。所以,我们就得像保护我们的隐私一样,留存这样具有私语倾向的影片去丰富我们日益贫瘠的电影构成,让我们相信正是那些与众不同的声响,让我们的耳膜不再因习惯而迟钝。
同时,还得承认,《路边野餐》也要求受众,得保持谦卑又异常诚实的心态去接受这项审美训练。我曾跟毕赣笑谈过:《路边野餐》放在任何档期,它的收益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我是不会奢望这类跟踪意识,叩击记忆的影片拥有大范围内的拥趸,即使叶公好龙兼附庸风雅之流再多也不会呈蜂拥而上状。
假如看电影,只是情侣们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虚掷时光的消遣。那么对电影的要求真的不必太高。但假如看电影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声光影像组成的虚拟世界里获得陌生的真实,从而丰富自己的感官并到达心灵。那么就得对那些愚蠢而虚伪的电影保持警惕,而对那些邀你共同求索人生之谜的影像充满热情。
□赛人(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