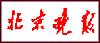|
|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汪良:与金庸大侠过招

金庸
金大侠,金庸。世界名人。其武侠小说,风靡海内外,在华人圈中,谁人不知。北京交通台开始连续播讲他的大作,也算是国内第一。当然也是世界第一。我料别的国家也没招惹金大侠的胆量。
把金庸的书全部播讲一遍,是我的动议,因为我的专业出身是播音主持,最早的名声,也是在中央台说了《新来的小石柱》。1995年五六月间,有台湾的一个出版公司通过中央台的朋友找我,请我把金庸的小说全部播讲一遍。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且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当时我刚大病出院,如何担当得起,所以只好谢绝。事后,有好事者怂恿,说喜欢金庸者遍布全球,值得一干。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痛。我就是什么都不干,专门录书,也要花费三年时间,我当时任交通台台长,交通台又是刚开台,这是不可能的。当我身体康复,精神渐好,工作之余,又想起了这档子事。加上好事者不断鼓动,我不再觉得不可能,慢慢播讲,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总可以吧。说来也巧,有一位在台实习的硕士叫美俊,和金庸有交往,愿当联络人。
为了得到金庸先生的授权,先得取得他对播讲者水准的认可。我采纳美俊的建议,送上我出版的几本书,录十几分钟的作品播讲,再写一封信。说实话,我此前根本没看过金大侠的著作,临阵磨枪,挑一本短的《侠客行》看,这书到结尾处讲佛讲道的,看不懂,着实恼人。但总的说,情节紧凑,悬念连绵,特别是开头,挺抓人。于是我录了开头的一段,作为样品。写信也有讲究,美俊建议,金先生是那么有学问,您的信也不能写得太白,不之乎者也,也得文白夹杂。好像金大侠是一个整天摇头晃脑哼哼唧唧的老书生。其实,这老人家很时髦的哩。我听劝,于是拿出老夫子的架势,就有了下面这封信:
| 庸老大鉴:
中国文学向有武侠一脉,仗剑慷慨,豪气干云。而先生出手,技压群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大侠之名,莫不钦仰。晚生亦然。 捧读先生大作,似见江湖纵马,刀剑争鸣。迷离于情节,感叹于忠义。静夜斗室,思绪飞扬,曾不知身在何处也。 晚生仗敬亭之技,拟将先生笔下之英雄,尽数描摹一通。使每日忙碌之人有随时听讲之便;令目不识丁之人得亲近豪杰之喜。前贤有言:骐骥一跃不能千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期以五年,定可功成也。 所请如蒙俯允,幸何如之! 顺颂安好! 北京电台 汪良 2001年8月 |
这封信的核心是两句:“使每日忙碌之人有随时听讲之便;令目不识丁之人得亲近豪杰之喜”。还有一个请求,允许北京台免费播出。本来,约好了,要在金先来北大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时见面,但我因为恰好去重庆参加一个国内的会议,只得由联络人代劳,把几样东西面交老人家。待我回京后,美俊转达了联络的信息。一个是,先生看了我的书(估计是看看封面),又看了我写给他的信(这个是真看了),说了一句,此人古文功底不错。对我的播讲也挺满意。老人家还说,我还从没有把所有作品这样授权,这也是头一回啊。再有,话自然要说到免费上,这时,在一旁的金夫人大义凛然地说,要什么钱哪,不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善良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善良的女人。金先生遵夫人旨,说:好,你们就和我的律师联系吧。何其顺利乃尔。此时,是2001年。海内外的朋友听说我要开始这个工程,无不欢欣鼓舞,纷纷预订“产品”。
可是,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动,我又忙起来,这事就放下了。我把播讲的打算搁在了退休以后。
到了2007年,交通台的李秀磊台长又忽悠此事,认为该做。说等您退休,那就晚了,别人家会占先。我明白,她是为交通台的影响力着想。可我每日忙碌,如何能完成这浩大工程呢。只能英雄气短,承认现实,那就多请演员。其实,果真都由我一个人播讲,听众肯定会觉得乏味。时过境迁,我们尊重金先生的劳动,先跟律师联系,经过许多的函电往来,终于签订了有偿合同。
合同是李秀磊带记者专程去香港和金庸先生签的。顺便还采访了老人家,其乐陶陶。我没能去,就由去者把以前写给他的信再呈上,请他重温一遍,还把那两句重要的话写成一个扇面送他。金老爷子挺客气,说送我一套书作纪念。可李台长拈轻怕重,说“一套几十本,带着太沉,您送他一本算了”。结果,老人家依言给了我一套两本的《连城诀》,还是小口袋本的,果然重量轻啊。但总算没阻止老人家在书页上给我写字。还有可乐的,有个金庸迷小时候认真画了一大本金庸小说插图,托李台长带去,请金庸在上面签个字。金庸感动之下,不吝笔墨,在画本上以在场的人为目标,大加赞扬,画的真作者“出局了”。更有甚者,李台长等人当场也不予以纠正(估计是不好意思)。回来后,搞得那“业余画家”捧着自己的画本看着上面别人的名字,悲喜交集。
我们花了钱,自然要考虑回报。请演员就不能马虎。因为按合同规定,播讲要照本宣科,不能随意改动,没有说评书那样自由发挥的余地,这对评书演员来说,是一个限制。又因为这是武侠书,顺从人们的欣赏习惯,总应该有点评书的元素和味道。此外,还得有说过长篇的经验。我心里有几个人选,先请曹灿先生吃顿饭,他三十多年前就指点过我,老师、熟人。可他今年76岁了,就想自己怎么轻松高兴,不听我这套。结果白吃我一顿饭。再请袁阔成先生,这是我鞠过躬的师傅,给他一本,老人家说,我先看看。第二顿饭说,没看明白呢。第三顿饭,我这个徒弟说的都播完了,他还那句,还是没看明白。我的忽悠不奏效啊。想想也是,老爷子80的人了,尽管精神健旺,这也是力气活。更重要的是,是他坚持原则。他说的功夫绝对一流,可一辈子没念过,我非让他照着念,确实强人所难啊。田连元先生把书背走了,见面时把书又背回来了,本打算吃完饭就把书还了,也是那句话,“念不了,这个”。可是经过我的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还是答应了:“录一部,试试”。他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和敢于尝试的勇气令人钦佩。《书剑》开播了,虽然如同是演话剧的穿上了京剧的行头,但因为功夫在,越“念”越好啊。谢谢连元先生。
《射雕》播完了,我将尽快开录《神雕》。一部《射雕》花费了我五个月的早晚时间。听完之后,评论自然见仁见智。也有拿我跟各位名家比较的,这都会给我以后的播讲带来启发和帮助。评书长于故事,朗诵长于抒情。评书是自由诗,朗诵是律诗。我自己称为播讲,其实是介乎于二者之间,根据作品不同,展现给听众的有声语言的表达方式自然有别。铁城先生说,听我的像看故事片,听评书像看动画片。还有人说我的是“文说”。这都说明,听众没把我当评书演员,因为我本就不是。
写下这些,也算花絮吧。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更多关于 金庸 的新闻
-
梁羽生生前自谦难胜金庸 称被超越不奇怪(图) 2009-02-02 11:04
梁羽生葬礼悉尼举行 金庸为好友献上花圈(2) 2009-02-02 10:03
梁羽生葬礼悉尼低调举行 与金庸50年交情匪浅 2009-02-02 06:15
梁羽生葬礼悉尼举行 金庸献花圈称“自愧不如” 2009-02-01 16:15
梁羽生葬礼31日在悉尼举行 金庸送花圈提挽联 2009-02-01 15:59
梁羽生葬礼悉尼举行 金庸献花圈称自愧不如 2009-02-01 14:55
金庸:我曾把张纪中骂哭过(图) 2009-01-10 12:29
数风流才子还看香江 历数倪匡金庸黄霑蔡澜情史 2009-01-03 10:41
他们支撑着香港娱乐业:文化诸侯-金庸(图) 2008-11-21 1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