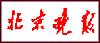专访贾樟柯:未来不必想,过去反需记忆
“我希望我的电影中的人,呈现他们在现实中的困惑与迷惘,或者说对于这个时代的不理解。我也呈现我自己的困惑。我相信,以这种诚实态度进入到电影中时,它会形成一种作者跟现实高度的统一性,也能呈现时代的真实症状。”
贾樟柯,坚守之难
很多的采访都可以在电话中完成,但对贾樟柯,我固执地认为需要一次面对。这种要求,对于处在影片宣传期的贾樟柯来说,近乎一种苛求,所以采访的时间一再被延宕,但也把我变得无比的耐心。等待中,我阅读他的新书《贾想》,连带着重温他各个时期的电影。等待中,我也不断问自己,我真的是要和他交流对电影的看法吗?似乎是,又不尽是。仅就他的电影,一本电影随笔集《贾想》,再加上一本随《二十四城记》衍生出来的《中国工人访谈录》,已经把这些表达得再准确不过,的确如大家所说,贾樟柯是自己电影最好的阐释者。但我私下认为,贾樟柯还是一个思考者,倾听者,他借电影记录社会,让我们听到了中国当下被遮蔽的声音,并留下一片沉默地带让我们回味。看过他的《二十四城记》,我想到了几个词:“起于记录,止于倾听”,《二十四城记》中有贾樟柯的克制,他避免着对这些复杂的人与事做评论,尽管这被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没态度,而我很想知道,没态度的背后又包涵着什么。
提示一种事实,并传达一种对世俗的尊重,是贾樟柯不同于中国任何一个导演的地方,也大概是陈丹青所强调的“贾樟柯,不一样的动物”的意旨。但是贾樟柯式的悖论同时又在:他关注普通人群,又被知识分子环绕。他努力沿袭一种人文电影的传统,但又必须放它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博弈。他的电影多为知识分子关注,但又难免被过度诠释。所以,在我看来,他的坚守之难还包括,如何不受过多的精英意识影响,从而保留自己对世界那份可贵的直觉。坦率说,这是我最想从贾樟柯身上感受到的,也是采访最想要的答案。
为什么我的电影没有态度?
孙:看《二十四城记》很感动。感动于你的倾听,一个即将消逝的工厂50年的历史,普通人的个人史,我能体味个体的隐痛中,历史难言的部分。更重要的是这种诉说,并没有一种讨说法的感觉。我认为,这里有对当事人的尊重。他们选择了承受与消化,同样很了不起。
贾:讨说法。或者说弥补与关注,并不是这部电影的意旨。我想记录的只是存在本身。当然拍之前,我也会有预设,但真正面对他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有些是采访过程中认识到的,即他们与自身命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很诚实的,更能还原一种复杂的历史状况。实际上他们当初支援三线建设,有非常理想主义、赤诚的一面,他们选择集体生活,也有激情在。不能因为后来体制给人造成伤害,就去否定这些。的确是时间让他们把很多挫折自我消化了,变成一种日常。大家坐在那里打麻将,聊天,而这种消化的状态也是我们应该记录的。旁观者可以认为这是牺牲,但是他们会认为这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他们是这样转化的。
也有人批评这个电影没有态度,认为工人是麻木的,牺牲者没有反抗。首先,我不认为他们是麻木的,你说一个女人一月只有二百块钱,还要供孩子上学,她能麻木吗?她太不会了,生存危机是下一分钟的事,她首先要想出对策。而不是像知识分子说的那样我先要去讨说法。这种自救的能力让人敬佩。
孙:其实拍一个电影不可能没态度。我觉得《三峡好人》《东》那一部分,艺术家刘小东的一句话,最能代表你的态度,“艺术并不是要试图改变什么,艺术就是把它表达出来。并且希望通过我的表达,能给他们一些任何人都有的一种尊严。”我看他带着礼物给那些贫穷的孩子,一个爷们儿自己先哭了,然后你又拍了周围人的反应。那些人也不直接上来问:你到底为什么哭啊?他们就静静地留他在那个状态。我相信,你在《中国工人访谈录》中说到“其余的,都是沉默”,就是这样一些瞬间。也是你作品中最动人的瞬间。
贾:沉默的时刻也是惊涛骇浪的时刻。它代表一种共通经验,不讲出来,类似于一个人跟你说着说着突然说“你明白了吧?”认同现实的复杂性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沉默就代表了这种认同,就是说,谁也逃不脱这样一个处境。这是一种群体处境,甚至可以说,正是那些沉默时刻,使这种处境不那么个案化。
沉默的背后
为什么没有救赎?
孙:再回到你作品中的沉默。我认可你作品中的沉默,但也有人认为,你的作品没有救赎的力量。影评人王书亚,经常从宗教的角度解剖中外电影,他说《三峡好人》,“贾樟柯的电影有足够力量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相,却缺乏一个真正的超自然异象,说服那样的生活仍然值得选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事实上,我是没有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的人。通过后天学习当然可能明白许多宗教的道理,但是它不是我的日常。不是我直觉的反应。也不是形成我人格的重要元素。
孙:那有人会说,这是作品中的缺失,你应该补上这种东西啊?
贾:但我更希望在我的作品里,作为作者,是一个诚实的形象。有段时间,我常困惑于我们对文艺作品的美学评价,“这是一部非常有力的电影”。好像是美学评价的高指标。到我自己,我希望是只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电影中的人,呈现他们在现实中的困惑与迷惘,或者说对于这个时代的不理解。我也呈现我自己的困惑,以及教育上的缺陷。我相信,以这种诚实态度进入到电影中时,它会形成一种作者跟现实高度的统一性,也能呈现时代的真实症状。
孙:这是你的坚持。但我看你现在每次出现,都是被精英围绕,前一段还和许知远做对话。你身边那个知识分子场太强烈了。我担心你会被同化。
贾:那天和许知远聊天,我说我跟你是正相反的类型。他中学一毕业就上北大,读大量东西,然后开始行走,想用身体接触这个世界,我是一直用身体在接触最基层、最民间的中国社会,23岁才开始读大学,有系统地学习一些东西。我相信我最主要的精神来源还是现实本身,日常生活本身。有一种艺术家是看了一千部电影然后创作一部电影,所构筑的电影也是电影世界里的世界,我避免这个。你说的担心对我并不存在,因为所有理论的梳理都要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之上。如果掌握了现实,你会自有判断。
表现平民,精英关注,到底谁在关心《三峡好人》?
孙:但有的知识分子可能不喜欢你这样沉默。他们希望你明确态度。我觉得他们在你身上的认同感,远大于对张艺谋、陈凯歌。所以我也能看到在你身上的悖论。即,知识分子更喜欢谈论你的电影。《贾想》一书收录了你一个演讲,解释为什么要把《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放,你说想知道“在这个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会关心三峡好人?”但从票房看,还是关心黄金甲的人多啊。这是不是一种错位?
贾:艺术并不直接作用于某种人群,艺术首先作用于每个“个人”。就每个个人来考察,悖论是存在的。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的电影所关注的人群,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消费能力。许多小城市小县城连影院都没有。但是反过来,任何作品最后都会形成一个公共意识,这种意识本身会起作用。比如这些年我们如果悲观地看,可以很灰心,因为一切的改变都太慢了,但也可以很欣慰,因为改革毕竟带来话语空间的拓展。有了这种拓展,我的电影中那些被遮蔽的现实,就有可能被揭示出来。
孙:到底哪些你觉得是在公共意识层面最被遮蔽掉的?
贾:我认为是贫穷。我的一些服装界朋友老在谈论临门一脚,我问什么叫临门一脚,他们说,中国已经富裕到只差这一脚就变成全球老大了。从他们看,这可能也是一种现实,比如我今天坐在办公室和你聊天,明天坐飞机出国,一个汾阳小子混到今天,也可以说我崛起了,大国也崛起了。但是贫穷又是多么现实的存在。对于贫穷的提醒要不要存在,同样需要,至于说它究竟提示给穷人、富人、知识分子还是政府官员,很难分清楚,但至少通过我的拍摄,得到一种关注,或者一种信息的强调。从这种角度,这种努力是有价值的。
以艺术正视这些贫穷,也并不是为给穷人做按摩。好像今天我揭不开锅了,看了《三峡好人》,就找到了解决方法了,或者得到了安慰。艺术绝不是这样,它就是一种提示。在一个公共空间里,我们是不是强调了富有,遮蔽了贫穷,遮蔽了落后,强调了进步。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创作的目的,最终不是服务于我们所写的人物,看他们和这个作品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解救关系,而是这个作品本身能提供什么资讯、什么观点,或者就是重复一种声音。因为我觉得自己从来不是多么洞察世事的人,但是能够重复一个看起来不合时宜、但其实无时不刻不去意识到的东西,这也很重要的。
关于自我与未来
孙:很早以前看过你一个短片叫《狗的状态》,呆住了,几分钟的片长,一下子就能体味到你的挣扎。现在你拿奖无数,也好像四处有你的声音,你觉得那只麻袋里的狗,它把麻袋咬破了吗?
贾:你很难说,咬破一个口,会不会被重新塞回去。
孙:至少大家觉得,《二十四城记》公映,就是一个尺度的突破。
贾:但是涉及到对我的工作规划,一些我个人感兴趣的题材,还是会受限。所以我有随时回到地下的心理打算。
孙:那你如何定位现在的自己。有些人觉得你浮上地面了,好像就不是独立姿态了,也差不多会完了。这种小年轻的激进看法也是有的。
贾:我是一个从来不喜欢姿态的人。主流的姿态是一种姿态,非主流的姿态也是一种姿态。所谓独立的姿态也是一种姿态。如果精神变成一种姿态就麻烦了。
关于我的未来,我觉得是不需要考虑的。首先我不觉得电影是我一直要从事的工作。刚拍电影时,经常被问,电影是你的生命吗?是你的信仰吗?我的回答是,它不是,它怎么能取代一个人那么珍贵的生命?它怎么可能成为人惟一的信仰。生命有很多可能性,电影也就是你找到了一个喜欢的表达方法而已。未来啊,乐观的一面看,它是不用多说的,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忘记的主题,就像《二十四城记》讲到的那些,是需要被记忆的。
孙:《任逍遥》那张碟上有句话我特别喜欢:“我越来越认为,一部电影的好坏,不是因为它说出了多少真理,而是包涵了多深感情。”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贾:还这么认为。因为电影也好,文学也好,最终还是感情的结果,呈现的还是情感,而不是首先是什么思想。
孙:这个情感不该单被理解成爱的情感吧?
贾:所谓诗意的情感吧。比如迷茫、苦闷、忧郁、爱、都是情感一部分,愤懑、激情都是。 采访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