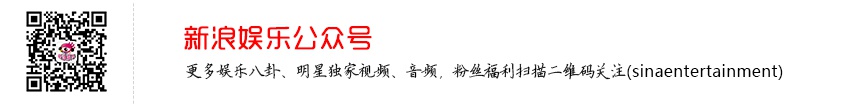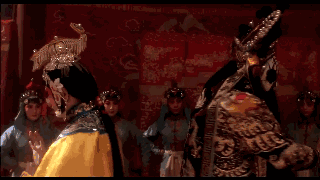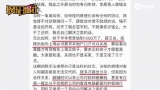作者/姜东瀛
 张绍刚
张绍刚张绍刚老师曾经对着2005级中国传媒大学的电视系同学在他们大三的某节课堂里,锵锵有力地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和窦文涛认识很早,那会儿我们混在一起就说,将来哥儿几个‘苟富贵,勿相忘”,他用重音拖延了这六个字,紧接着若有所思补充道,“他可能现在不记着了都”,这是2007年秋季学期的真事儿,用脑袋担保,张老师绝对说过这个话。
 张绍刚、李诞、池子
张绍刚、李诞、池子十年后的初秋,已经通过某大会,开辟了事业新边界的张老师,在网络和电视上,继续强化他的优势风格:把课堂上本来经年累月擅长的“吐槽教学法”,正式转型确立为不再盛气凌人的平民“吐槽”主持术,收获喜人。
 窦文涛
窦文涛而那一厢,窦文涛同志则驰骋在中国电视史上形态最为简单的三人谈话节目,用时十九年,其传播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铁打的他,流水的意见领袖和新闻热点当事人。
你就说吧,不管从王蒙到许子东到刘少华的老中青三代“评论员”,还是梁文道、余世存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再到自由作家查建英,教犯罪心理学的李玫瑾,教艺术史的曹星原,这些不同的极为健谈的学术女杰,甚至是争议人物徐晓冬,只有锵锵请不来的,没有窦文涛那自来熟访谈功夫拿不下的。
 窦文涛与他的《锵锵三人行》
窦文涛与他的《锵锵三人行》凤凰卫视的谈话节目矩阵,多年来说话招人听的,状态稳定不会把天聊死的,头牌大概只能是窦文涛。这不是对鲁豫、许戈辉做什么褒贬对比,因为她们的节目形式和议程设置确实没有窦文涛讨巧。
屏幕里语言交流的世界是两个人的,超过三个人就不见得有什么真诚了,而真诚有的时候作为一种节目上的思想输出,并不能让每个人都get到愉快,相反,常常给人的感觉是尴尬而不适。
窦文涛在三人架构的电视谈话里,可以作为中转站,有效起承转换、调节纠正三个人谈话中的情感错位和枯燥无趣。他不需要对他谈的话题真诚,事实上他屡次在节目中承认,他能上节目聊的事情,掀起的话题,跟他的关注点,他的偏好甚至是他性格骨子里的思维方式都不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
他在节目里表现的话题掌控能力,对别人的迎合适应能力是清奇的,他拒绝正经,讨厌崇高,有的时候语言组织的特别市井。从电视主持人必须说精准的人话标准上,高端观众们顿时有种莫名的跃跃欲试的快感,觉得自己比窦文涛的口条都利索,归纳都要更有档次。
然而这种感受纯属SOME TIMES TOO NAIVE,涛涛的节目你可以说它懒,不求新不求变,跟不上时代,一天到晚瞎白话,但是你真见不着“TOO YOUNG TOO SIMPLE”的硬伤。
为什么见不着低级错误,他有专业主义洁癖,这是另类的电视手艺人情怀,不是廉价的激情,是难以名状的执着。
锵锵暂停前的最后一天节目我看了,忘了起什么话头,他讲到本质上,他与他父亲一样,喜欢琢磨一件事儿的精度,从设计到执行上,哪怕再简单,也要在落实上较较劲,做出纯度上的美感,就算这个美感只有他自己感知,他自己欣赏。
但矛盾的就是,他做的节目追求的是一个广度,什么都要聊,所有的热闹都要蹭。我发现在他节目里有一个现象可循,一讲到社会问题个案,他就自觉不自觉地带着嘉宾往民族性劣根性这个沟的方向上聊,一讲到公民意识觉醒,一讲到做事态度,一讲到习惯与规则,他就常出惊人之语和神来之笔的辣耳朵金句,有时伴随贱贱的笑,小机灵小包袱的捧哏,也不比于谦[微博]差。
以上种种,在我理解,就是一种朴素的情怀,窦文涛这种人你让他情感外露,不如杀了他。
 2016年窦文涛圆桌派分享会
2016年窦文涛圆桌派分享会我听一些师长讲过,窦文涛在珠江经济广播做主持人那会儿,就玩儿过“许三多”式的逆袭,从基本什么都不会,甚至在珠三角的人文环境里,嘴都笨到比棉裤腰子还松,依然能干到吃“开口饭”,奋斗到门面担当,走进大老板的视线里,这背后是怎么样的经历跟悟性,煎熬与折磨。
他跟白岩松、崔永元一样,可能是从广播流向电视里最成功的六零后媒体人之一,但是武汉大学毕业的窦文涛又和广播学院这一流派的男同行们不一样:他在节目里表现的状态起伏波动公认最小,韧性有目共睹又最顽强。
不管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传统电视媒体盛景有多热闹,挣钱走穴开副业的机会多么繁旺,他独处一隅,把玩打磨他南朝北国、天文地理的谈话内容产品,入世又出世的分寸感和节奏点神准。纷纷扰扰,世态更迭,他的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盘节目带布局的那个固定午夜时段内,经久不息,风雨中稳坐。
天下没有无不散之节目,锵锵三人行已成年,十九岁离家出走,不见踪影一段儿也无大碍,归与不归,全凭造化。
节目组也都没把话说死,微博里说的“暂停”“后会有期”就是在给这节目铁杆社群以念想。窦文涛今年五十岁,天命如果既知,最好的归宿就是顺其自然。
我还记得,少年时,并不知道锵锵三人行为何物,就从广东那边的娱乐杂志里,比如对《还珠格格》平面报道居功至伟的《广州青年报》里,经常看到窦文涛的版面,曝光率能渗透到东北小城的,那个年代,也没几个生活于香港的大陆文化人。
在我心里,九十年代末,他就是和赵薇[微博]前后脚成名的,这如果是个共同记忆,他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不只是一个节目所能承载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