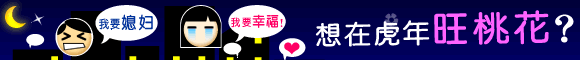独家对话黄蜀芹:《围城》是我父母那代的故事

黄蜀芹
导演黄蜀芹
黄蜀芹:《围城》是我父母那代人的故事
采访手记:采访黄蜀芹前,工作人员反复强调黄导身体不好,时间一定要控制,虽然聊起来,有些时候黄导的思维会短暂停顿,但整个过程中她回忆起《围城》中的经历,黄 导的兴奋我们还是能清晰的感受到。《围城》是黄蜀芹父母的故事,交给她拍摄,有了深刻的延续性,听她回忆那时候的故事,对于自己作品的深爱溢于言表。
围城往事:不知道《围城》是什么
主持人刘杨:90年之后都是在拍电影,当时怎么会在90年拍电视剧,而且是这么轰动的《围城》呢?
黄蜀芹:那个时候80年代末期,像我这一茬所谓的导演没有真正拍过故事片。80年代末期开始,好像对我们这一茬实际是中年的人有信任度了。然后让你们拍电影。所以我们就想拍,我在80年代后期的时候已经拍了4部电影。《当代人》、《青春万岁》、《童年的朋友》。我就是在《童年的朋友》,我方的军队过黄河,我们在黄河边上,气势很大,护医院的小孩怎么把他们运过黄河这样的场面。在那个时候,忽然有一个长途电话,说是上海来的。正好天气不好不能拍,一直搭着他们的车到延安这座城市有一个小小的邮电局听长途电话,长途是从上海打到西安来找我。说我们现在想拍一个电视剧,叫《围城》,你回来拍。我说什么?我这里已经在打仗了,还叫我拍打仗的。就那么无知,不知道《围城》是什么,我就这么愚蠢的问的,因为都是老朋友,他说不是的,不是的,你来看。这是真的情况。说明我们当时的简单化,很有热情,但是很简单化,在那个时候。他叫我去买,那天下午我还是不能出工,那个天不适合拍我们那个电影,在黄河边上只能睡大觉。后来我想有睡大觉的时候,我让摄制组给我一个车,反正都不生产了。到延安市去,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我就进去看,有没有这个书,两本小绿书,绿颜色的。
主持人刘杨:上下册?
黄蜀芹:不是,一共两册,《围城》就这么点,我一看绿的封面,就那么一个封面,干干净净,我说还有吗?他说还有一册,我说两本都要。一共就两本,我就拿来了,后来又到黄河边上去,我躺在炕上就开始看。
主持人刘杨:当天下午回去就开始看了?
黄蜀芹:对。连续好几天,天不好,我给看完了。我才知道我们的知识结构原来有多单薄。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不知道小说还能写留学生的故事,怎么一步步陷入中国的平庸的大网,人生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这种,就知道《围城》是这样的。原来在我们的知识结构里都不具备的。我一直在说,我是躺在延安的土炕上看的《围城》,来理解它,来了解它。这很奇怪的,一直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好奇怪。我也很幸运,怎么会能够给我一种思考,完全太不同的情况。
主持人刘杨:对比很强烈。
黄蜀芹:但是让我同时去感受。这种都跟以后拍摄的角度或者说是我希望怎么来表达,这些人的生命,我觉得都有关系。这都是我最早接触的《围城》。
主持人刘杨:当时是不是在你眼里是不是对比很强烈的画面,一边是延安这样的画面,另外一面是这么充满小资情调的?
黄蜀芹:不是的。这样就有是非了,那个时候的人有他们的奋斗和苦恼。比如说在革命时代,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苦恼和奋斗。我觉得情况是不一样,规定情景是不一样的。但是人生都有它的相同之处,就是怎么表达,这有时代因素,又有人的阶层,都有。世界是很丰富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文化观比较简单和单一。
主持人刘杨:电视剧和电影的创作理念?
黄蜀芹:都一样,我们这代人受的文化教育本身是比较单一的。YES或者是NO,没有中间非常有丰富色彩的生活,缺乏表达。我一直在想,几十年的文化教育的单一化所造成的一种悲凉。
主持人刘杨:后来看完就很喜欢,就决定去拍了。
黄蜀芹:看完了觉得可为。但是能拍不能拍,我不是这个阶层的人,我不是审查者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题材是可为的。尤其我自己想到一茬知识分子是这样的,比如我爹妈的路线跟他们是一样的。
主持人刘杨:很有现实性?
黄蜀芹:不是现实,是30年代那个时候,抗战初级阶段开始,我爹妈的过程和《围城》人的过程真的很像,上一辈人跟《围城》所表达得那样人他们是同龄的。我们50年代在新中国长大,还不能深切懂得这个。但是像我父母跟《围城》的人是一样的,到英国去读书,那时候不兴到美国,都是到英国,那时候《围城》的人也是一样的。完了回来之后,上海的租界里面待着觉得不够好,不能为国家做点事,就跑到四川。我爹妈是戏剧学院,戏剧学院从上海就迁到了四川,我们就留学回来自己两个人跑到四川去,进入他们的戏剧学院,一本正经去教学,但是看不下去,跟《围城》里的人一样的,看不惯那些人,又回到上海,很迷茫。我当时一想是这样的,没想到有这样的小说。
主持人刘杨:一下子眼前一亮。
黄蜀芹:心里就一动,怎么跟爹妈的路程是一样的,那就说是有一批知识分子是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动乱和日本侵略要进来了这个时期,是一样的。我为什么叫蜀芹,他们在四川怀孕的,在上海的租界里面生下来,跟《围城》真的很像。
围城往事2:骂大街把我那个演员给弄走了
主持人刘杨:注定了您一定要拍摄这样一部作品?
黄蜀芹:我当时没那么想,我当时想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不是我一个人,是一批人。我们是又一代知识分子,我拍《围城》是40岁左右,跟我爹妈比起来是一茬知识分子。我就觉得豁达认识了,对这个作品有认识了。它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中国知识分子是走过这样一条路的。
主持人刘杨:那时候去拍摄,选角等等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黄蜀芹:我比我年轻的人更能接受《围城》,当时英达留学回来到我家来了一次,到底怎么我忘了,英达跟我说,黄导演我们拍《围城》好吧,我还说,打仗的叫我拍,那时候很盲目,对这个东西没认识。那时候没有这部作品很热,大家都抢着看,没有,很寂寞的一本绿绿封面的小说。他们两位深信,相信朴素,他们的书不会看上去眼前一亮,都是绿绿的,两个字。
主持人刘杨:怎么会选这两个主角,那时候看起来很年轻。
黄蜀芹:我觉得陈道明本人性格比较丰富。又有很认真的思考的,但是也有好像混在里面的那样的。他两个都有,一个是表象的,一个在内在的,这个很难的。
主持人刘杨:很极致。
黄蜀芹:不是每个演员都这样的。起码我在他身上看到他有这种因素,有了可以多一点,要少一点少一点。有的是可以,就怕你没有。
主持人刘杨:那时候陈道明对自己的角色是怎么理解的?
黄蜀芹:我基本上人都齐了以后,我就说咱们不要去理性分析,我就相信表演主要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感觉。你对这个人物的感觉,我觉得是这样。当然他们很用功,都看小说,所有的人进了《围城》组不用功是不可能的,大家都很虔诚,都很努力,但是我不能造成压力,看书看书,这样会坏事的。他们自己做了很多功课,这个我是相信的。所以大家在热爱这本书的前提下,大家都很用功,是这个气氛,而且对这两位作者很尊敬,因为这样的小说真的跟我们以往看到的中国小说真的不一样,反映的阶层不一样,写的方法也不一样。小说里面呈现出来的人物真的不是我们经常可以在文章里面看到的。
主持人刘杨:您会是在现场很严厉的导演吗?
黄蜀芹:我不骂人,也不在现场训人。但是我从演员他们反馈给我,导演你不要两个眼珠子总看着我,我害怕的。我说我不看你,看谁呢。
主持人刘杨:有一种威慑力。
黄蜀芹: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对我挺好的。
主持人刘杨:当时这个戏拍了有多久?
黄蜀芹:100天,开机100天。
主持人刘杨:三个多月?
黄蜀芹:对。我们一共才10集,你想我们1集花多少时间。
主持人刘杨:精磨出来的戏?
黄蜀芹:也不是,我第一次拍电视剧,我以前拍电影。演员走来走去都是有内容的,不许一个人空着手,不是拿着东西,就是挑着东西,不能马虎的,这基本上都做到了。
主持人刘杨:当时拍摄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很困难的事情,解决不了的事情?
黄蜀芹:上次什么事情把我都弄的哭了,反正挺欺负人的。我记性不好忘掉了,就是演员的档期,另外一个组,骂大街把我那个演员给弄走了。我觉得很不讲理,我碰到的电视人这样蛮不讲理的挺少的,我对人挺客气的,一般人对我挺客气的,但是就有这样的骂大街的。
主持人刘杨:当时有想过《围城》造成那么大的反响吗?
黄蜀芹:没有。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过,这个知识分子的太狭窄了。
主持人刘杨:小资?
黄蜀芹:小资什么的是一种阶级电影。太文雅,太知识分子腔调,收视率会不高的,不会受欢迎的。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不那么好看。但是后来所以播的时候,收视率很高的,但是很喜欢看的。我真的才松口气。
主持人刘杨:黄导您从80年代开始拍这部戏,之后拍了很多的电视剧,一直到90年代,一直到今天,您觉得电视剧发展到现在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呢?
黄蜀芹:我觉得它丰富了。原来我们的文化思想比较单一,但是现在丰富了。这是很好的事情,每天晚上8点钟,大家有东西看,而且比较丰富。而且观众也训练出来,知道哪个好一点,哪个弱一点,这是一种审美的培养,这很重要。现在比20年前真的是好多了。要看到进步。
主持人刘杨:现在您的后辈来参加会的有200多位导演,有这么多的导演,您觉得哪一位,或者是哪一些你比较看好,觉得他们的题材您是最喜欢的?
黄蜀芹:我觉得今天来的都不认识。
主持人刘杨:很多都不认识了?
黄蜀芹:也不是。我觉得就是一代有一代的,这里面学校、学院做了很多努力、培养,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说科班科班都没用的。还有所有演员的努力,包括编导的努力,我觉得在这些年里面,文艺作品,如果有10%是好的就了不得了。这个东西一定是多数是会有不足,但是就有一些是比以前的不一定是自己的,或者是说那个氛围下的作品。就是说只要比那个时候进步一点,我觉得就是很了不起的。
主持人刘杨:老一辈的导演,对现在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建言?
黄蜀芹:我看的时候,从来不挑剔,就是以一个观众的平常心看。当然有的还不错,有的不好我也跟别人一样转台。我觉得观看一定要有一种好的心态。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专家,我从来不那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