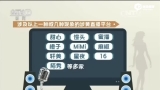陕西人艺版《白鹿原》
陕西人艺版《白鹿原》
电影版《白鹿原》 放大“田小娥”惹争议
2012年2月,王全安版《白鹿原》获得了第62届柏林电影节的摄影银熊奖,这也是影片公映后时常被夸奖的部分,广袤天空下大片金黄的麦田,配上高亢嘹亮的秦腔,带有厚重时代记忆的关中面貌真实呈现在银幕上。王全安曾自豪地说,德国摄影师卢兹用“最大的克制”,展现了麦浪、牌楼、祠堂、皮影这些陕西风俗,是影片摘下银熊奖的一大原因。
当年国庆档前夕,这部王全安署名编剧、亲自执导的《白鹿原》,上映没几天就面临网上网下一面倒的质疑声。反对观点集中在,王全安将50万字的厚重小说凝结成了一部《田小娥传》。
156分钟的内地公映版本里,与白、鹿两家有关的线索人物集体消失,尤其是“神仙”地位的朱先生,和理想主义化身白灵的删节,让许多原著粉不满。相较之下田小娥戏份有超越白嘉轩、鹿子霖势头,而宣传期突出的大尺度情欲戏,也与原著精神相去甚远。这一版本改编最为诟病的还是剪辑混乱,有人观影后表示剧情缺乏连贯性,结局定格在日本人飞机来到白鹿原上空,十分的费解,小说里白孝文、鹿兆鹏、黑娃为代表的新“原上人”经历生生被这一版无视和省略了。
对于“田小娥传”的说法,王全安有过辩解,他觉得外界“先入为主”了,50万字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得有所取舍,他这部电影是有几条主线并存,上映后观众的感受是“因为影片后半部分被删去了半小时”。
电影版白嘉轩饰演者张丰毅,也曾谈起了他对影片的看法。张丰毅说拍摄时众人对剧本达成了共识,“白鹿原人民在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带领下,遇上了大变革的年代,他们怎么样一起克服困难,繁衍生息,进而生存下来。
但导演的处理是,田小娥的爱情线进来后,把整个主题冲散了,爱情线变成主线。”
友情提醒一下,《人民的名义》里“沙李配”早在5年前就在王全安版的《白鹿原》实现了,吴刚[微博]饰演的鹿子霖逮着机会就算计发小白嘉轩。
话剧版《白鹿原》:有最正的陕西味
剧中演员全说陕西话,曾是王全安版《白鹿原》宣传点之一。话剧迷却都记得,第一次全员说陕西话的改编作品,是林兆华执导的北京人艺版《白鹿原》,本月底到广州献演的陕西人艺版,更是原汁原味。这一版本里,演员绝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陕西人,加上语言老师的培训,剧院里听到的白鹿村方言(蓝田话),“味道极好”。
孟冰身为两版话剧的编剧,从初稿就定下了改编基调:保持小说基本格局,主讲白鹿两大家族的恩怨情仇,以白嘉轩“巧取风水地”开篇,用倾倒的“仁义白鹿村”牌匾、老年白嘉轩伏地大哭作结。
孟冰受访时说过,原上出现的众多人物,删减哪一组都是伤害,无法尽情展开,那就保持线索。因而不论是北京人艺版,还是陕西人艺版,上一代人的代表白嘉轩与鹿子霖,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白孝文、白孝武、白灵、鹿兆鹏、鹿兆海,还有副线上的黑娃与田小娥,灵魂人物朱先生,每个角色身上都有戏,短短几场也频现闪光点。
不过两个话剧版本前后相距十年,孟冰在陕西人艺版剧本创作上,对2006年的北京人艺版剧本做了微调,精简了人物,将村民整合成古希腊戏剧里的“歌队”形式,他们跳进跳出转变身份,既交代了时代背景和主体事件,也打破了陈忠实之前所担心的时空限制,不少观众看完陕西人艺版,都对这一精巧设计竖起大拇指。看过两个版本的观众还发现,陕西人艺版里,鹿兆鹏与白灵的爱情故事更贴近原著,在白灵主动之下,带着共同信仰的两人最终从假夫妻变成了真夫妻。
舞台设计上,两版话剧各显心思。北京人艺版实景搭建了一片黄土高坡,有真实的尘土,也有真实的牛羊。陕西人艺版团队深入考究后,突出再现了祠堂、牌楼、窑洞这些带有关中地域特点且符合人物阶层的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知名度很高的华阴老腔,正是被陈忠实推荐,出现在北京人艺版《白鹿原》才大放异彩的。即将在广州公演的陕西人艺版,对老腔使用十分克制。
最出彩的两处是田小娥死后化蝶,以及剧末白嘉轩伏地大哭,没有过多搅扰剧情,而是能够渲染和增强整个戏的压抑感,这也是主创团队最想达到的效果


































































































 网友偶遇黄晓明baby
网友偶遇黄晓明baby 伊能静儿子正面照曝光
伊能静儿子正面照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