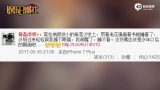《白鹿原》海报
《白鹿原》海报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由作家陈忠实的巨著《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式上映了,虽然经历了停播风波,但时隔一个多月后,终于顺利再次回归荧屏。尽管目前是一片叫好却不太叫座,收视率一直被《欢乐颂2》、《思美人》等压着。但电视剧的精心场景布置和情节设置,都比较好地展示出《白鹿原》原著中所有的一些内涵,而且无意中以更集中、更好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在电视剧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这些故事背后,反映了中国国家权力的下放与乡土社会秩序的逐步瓦解,以及这过程中二者的冲突,以白嘉轩、鹿子霖,还有他们下一代白灵、白孝文、黑娃、鹿兆鹏、鹿兆海等在历史洪流之中的沉沉浮浮,书写了个人在时代列车面前的渺小和无力。
晚清以前的乡土社会秩序
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农业社会当中,属于宗法血缘社会的范畴,宗族管理着广袤中国的社会基层,同时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环节之中。据学者秋风所概括的:“宗族是乡村社会中最为重要的自治性组织,它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并且源远流长,至少从宋明以来高度平民化的乡村社会,就是以宗族作为治理之基本单位的,以祠堂作为宗族公共生活之中心的。”这个过程中,由于国家政权基本上只能通过乡绅阶层向基层乡村渗透,而从未实现对乡村的直接控制,因此有了秦晖教授概括的:“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之说。如此,中国的社会结构便一直是一个相对凝固的社会形态,在学术术语上,有滕尼斯所说的“有机的团结”,以及费孝通所说“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显著的特征。
这些特征,在《白鹿原》中就体现:在祠堂是一个无上神圣之地;乡约成为白鹿原人际关系中最为核心的规范;族长白嘉轩的有无上威严,是乡约的维护者与执行者;白嘉轩与鹿三之间虽然有东家长工身份的区别但却形同一家;新媳妇必须明媒正娶地娶进门方能进入祠堂否则就难以在村庄里立足,而鹿三之子黑娃和田小娥只能居住在村外破窑洞里等等。而族长白嘉轩就是典型的中国乡土中的乡绅,他正如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描述:“绅士是一个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它所承担的许多重要职责包括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管理范围,从意识形态的引导到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以至于进入行政职责的范围。”“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团联合征税等许多业务。”这一方面,在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修祠堂、设立乡约碑管束乡亲、请私塾先生教化村民、处理裁决村里纠纷、带头维护宗族利益等等,都是白嘉轩作为乡绅的重要体现。
但在辛亥革命之后,朝代更替,新的权力格局诞生。在白鹿原中,也随着高喊着“革命”的鹿子霖剪掉辫子成为了白鹿原上第一保障所乡约,形成了族长之外的二元权力格局的一端,这也揭开了国家权力渗透的乡土社会的开始。在这个随后的过程中,黑娃娶田小娥,闹农会、率众砸祠堂、当土匪(这也代表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村民们在鹿子霖的撺掇下要求白嘉轩下令修庙“震鬼”未遂后,村民威胁另选族长等使得族长权威削弱。百灵以死威胁要进城学新学、黑娃对父亲鹿三、白孝文对父亲白嘉轩的反叛,也意味着新的价值观对乡土秩序与文明的反叛与冲击,这种民间内生秩序力量的反抗招致了更大的混乱。同时有革命思想鹿兆鹏对父亲鹿子霖反叛,也反映了新思想的搅动。乡土社会秩序的崩盘与国家权力的渗透,就体现在这些被放大的电影情节之中,这些事件与行为,一步步地撕裂着原本凝固的社会形态,严重地冲击着原本的平衡秩序。
然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社会的动荡更使得这种摇摇欲坠的乡土社会秩序更加岌岌可危。不过此时虽然情形不容乐观,但就如在《白鹿原》中显示的,代表着野蛮权力的军阀队伍进入村庄抢粮时,排长也要用武力威逼族长白嘉轩拿起铜锣吆喝村民交粮才能实现,另外,作为官职的“乡约”,外来赋予鹿子霖的权力,实际作用并没有族长的权力大,鹿子霖搞不定的事情都得请白嘉轩出山。这两个场景显示出了族长为表征的乡土秩序,深植于乡土社会之中,即使在国家权力渗透之时,依然生命力顽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并没有彻底被终结。
城市化下的乡村社会
不过,从1949年以后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化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下的国家权力第一次全面深入乡村,取缔了乡绅阶层和宗法制度,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控制。原先的阶级划分转化为政治等级,贫下中农、富农、地主等政治身份通过血缘遗传而标签化(黑五类)、政治化(剥削阶级),原有的身份秩序完全被打乱,随之而来的乡土社会秩序的完全瓦解,乡绅彻底被改造或者“革了命”,宗祠、族谱、族规等乡土社会的事务与事物,被当做封建糟粕予以“破四旧”。所有人成为公社社员。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是他们的生活轴心,持续地接受思想改造,再加上城乡二元机制,牢牢地锁定了整个乡土社会的流动性。
再接着,改革开放以农村改革为先锋,包产到户的实施,以及之后更深入的改革,社会控制已经松动。巧合的是,同样一位作家路遥,和同样获得茅盾文学奖,也在去年被搬上荧屏的《平凡的世界》,正好是这一段承上启下的故事。《平凡的世界》的开始,正是这个改造后的情境呈现,同时也以局中人的叙事,呈现了整个农村权力建构的过程,这就体现在田福堂的权威形成与崛起,以及金家人因为地主成分,长期被田家人压制,低人一等,传统乡土秩序被彻底改写了。在《平凡的世界》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了两条前后分别展开的主线,前一条线是孙少安背后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孙少安的多次被批斗为矛盾冲突点,展示了农民与土地的生死依存关系,最终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全社会都出现“权威倒置”的现象,在农村更加剧的呈现,但正是这种阵痛式的权力交接,解放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后一条线是孙少平这个第一代“农民工”背后对于社会流动的松动,刻画了户籍制度与城乡二元的区隔,从农村人奋斗到城市人过程,贯穿着孙少平的前半生,他所畅想和追求的走出去的理想,以直到最后拿到了城市户口,成为煤矿工人而抵达。
随着迁徙和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大量如孙少平一样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接受了市民化,在身份上由纯粹和传统的农民,向具有了更多现代性的“农民工”或“新市民”转变,二代农民工很多人已经实现了个人的现代化,个体上已经与城市居民没有明显的区别了,真正地实现了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言的“农民的终结”。从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到政策明确反对与引起社会恐慌的“盲流”再到自由迁徙“新市民”,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这是一种巨大进步,但从对原有社会的冲击角度来说,其冲击力也是空前的,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吞噬了大量的乡土空间,而乡土社会之主角毅然决然地出走,已经宣示着乡村已经被出走者遗弃,乡土秩序已经被瓦解,乡土文明已经被淡忘。
而《白鹿原》让我们又有机会重新审视其背后的乡土文明,可惜原上也早已没有那个牌坊,原上的老房子、遗址早已无存,乡民们亦纷纷外出,成了厨师行业的主力军,空留老幼在村子里,恰似给落日的乡土文明,抹上一层绚烂无比的晚霞,在晚霞的绚丽之下,白鹿原的热闹早已成追忆了。如今乡村凋敝,中国乡土文明在很多地方几乎消逝殆尽,除非它被重新改造,以一种风景观光的方式,如同遍地的农家乐一般。
乡土文明在现代社会仍有价值
乡土社会之不存,乡土文明将安附?传统维系乡土秩序的各种乡俗民约、家法族规等规则面临解体,乡土生活秩序已经几近瓦解,乡土文明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已成明日黄花。如同《白鹿原》中反复出现这样的镜头:一座中式牌楼远远竖立在大片麦田中。它像一个隐喻,隐喻着中国乡土文明在旷古的忧伤中,沦为远方的记忆与模糊的想象……如今白鹿原包括广袤的北方地区等,其乡土秩序已经消解,宗族等乡土关系已经式微,在中国北方各地,宗祠等已经很少地方能够寻觅到了。
尽管“乡土社会秩序瓦解与乡土文明的终结”的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人为是抵挡不住的,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地固守与迷恋那些必然要走入历史的传统。但在很大程度上说,乡土文明又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如今,这种文明的消逝是很多人心中的不舍。
因此,随之时间的推移,情况又悄然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今天的城市和乡村,正在匪夷所思地互诉衷情:乡村为了接近现代化,满眼都是钢筋水泥,这是半拉子的城市化,而偏远的农村地区,则像是一个个被掏空的鸟巢,里面的人都飞往城市。而另一面,乡土式生活,在城市中,依然开始有回归趋势了,如在城市大造别墅,只为营造乡村的味道,以及郊游农家乐与农家菜(仿佛代表着有机绿色)的流行。虽然这种乡土式生活有些只是城市中产阶层消遣方式,但是这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文学与社会学的想象力:时间一直在证明乡土文明,恰恰是我们的文化记忆中最坚实的部分,仍然对中国当下生活秩序和生产关系产生深层的重要影响,仍是中国文化的根基。随着城市化与现代化一些内在的弊端的显现,人们也到了反思的时候。
诚然,礼治秩序尤其落后与不人道的一面,比如在鹿兆鹏被逼与娃娃亲冷秋月成婚、不容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上。但总体来说,其对中国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时值至今,在南方的一些地方存在,诸如福建、广州等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这就体现在国家基层权力运行中,都时刻受着这种乡土的特性影响,宗族关系在村民选举以及村民自治中,有着重大的影响,乃至在现在的城市化生活中,建立在乡土文明之上的文化也在时刻影响着中国人,比如同乡意识等,还有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虽然已经被弱化为简单的象征性节日,但其背后依然是显示出传统社会秩序与乡土文明的重要意义。
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中,特别重建中国底层社会秩序时,如何有效地吸收中国本土的知识与传统经验,来建设一个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社会与文明国家,以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能够有更丰富的多元化生活的可能,有更多的传统文化与精神的寄托。
乡土文明与本土治理经验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尊重乃至借鉴传统,在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中,吸收本土知识与地方实践,变得尤为重要。如果能够结合乡土中国的实际,尊重与吸纳有效的乡土社会中的一些伦理与习惯,无疑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已有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了,在广东、福建等南方地区,宗族关系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至于一些学者提议“把宗族纳入村民自治架构”。美籍华人学者蔡莉莉也曾证明了在同样的经济文化条件下,有宗族的村庄和没有宗族的村庄,其公共设施存在很大的差别。由此可见宗族背景一直以来都对于农村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如此看来,解决中国基层的社会转型与建设问题,应充分释放基层的自生性,尊重乡土社会中基本的伦理与文明。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中,要结合中国乡土社会自己的本土经验、知识与地方实践,构成符合自身的社会以及政治文明结构。这一点,香港、台湾等地社会建设,在构建现代政治文明的同时,并没有斩断或排斥乡土文明与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基本伦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中彻底否定自身传统的激进主义。这些成功的经验,已经给予了乡土文明的意义一个很好的证明,并使其成为了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保存较为丰厚之地,不禁令人欣慰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