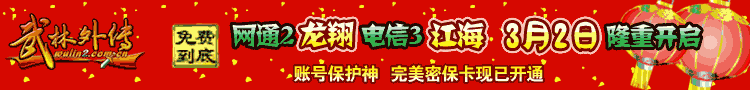
|
|
|
原来阿尔巴尼亚也有文学 也有这样的文学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03日09:06 南方都市报
康慨 记者,北京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T·S·艾略特 血仇的法典 在伊斯梅尔·卡达莱写于1978年的小说《破碎的四月》中,卡努法典统治着阿尔巴尼亚荒凉的北部山区,几百年来,对于家族血仇进行着一丝不苟的规定,从复仇杀人的方式,尸体的摆放,到吊唁和葬礼,以及事后要上交给法典监护者的“血税”,无一不在其严密掌控之内。 “卡努”(Kanun)显然与“Canon”(教规、正典,如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理论著作《西方正典》)一词有着相同的希腊/拉丁语源,而我最初以为,它只是博尔赫斯式的百式全书化的文学杜撰。但我错了。我找到这部法典的英译。它由一位名叫莱克·杜卡季尼(LekeDukagjini)的王子创设于阿尔巴尼亚北部和科索沃,自15世纪起延续至今,即使在17世纪阿尔巴尼亚皈依伊斯兰之后,其口传文本和具体实施也仍然得以基本保存,而在社会主义共和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结束之后,卡努法典的文化又有日渐兴盛之势。 卡努显然来自既非基督教,亦非伊斯兰教的某种异教传统,且很难不让人把它和巴尔干地区绵延不绝的仇杀历史联系在一起。世代寻仇和相互杀戮,就像一个永不失效的咒语,施加于这一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之上,正如卡努牢牢掌控着山间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宿命。 “我是个来自巴尔干边缘地带的作家,长期以来,此地都因人类恶行而污名在外——武装冲突、内战、种族清洗,凡此种种。”2005年,在获得得首届布克国际奖后,卡达莱表示,“我的祖国阿尔巴尼亚也属于这一地区。” 血仇条款是卡努法典中最具恶名的部分,但或许也最能引发艺术上的“死亡迷恋”。在卡达莱的小说中,故事发展的第二条线索描写了一对新婚的作家夫妇:巴西安·沃普思和娇妻迪安娜,他们离开了首都地拉那,前往卡努治下的山区作蜜月旅行。 “你将逃离现实世界,前往传奇世界,那是一个史诗般的不可能再存在的世界。” 巴西安写过一些关于北部地区的半悲剧半哲学的作品,一路上,他不断地给妻子讲着卡努。“那是一部真正的关于死亡的宪法,”他说,“它是这个世界现存的最值得纪念的宪法之一,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应该以制定出这样一部法典而自豪。” 他引用了一句著名的山区谚语:“活着只是因为死亡在休假。” 非同凡响的风格 即便卡努法典在历史上真的存在,但在卡达莱的笔下,《破碎的四月》仍然与现实主义相距遥远。它虽然好读,却不一定好理解。 尽管我们大致能看出来,故事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但作者仍然有意模糊了时代背景,抽离了人物具体的社会关系,加上卡努本身的不合常情,远离现实,都促成小说成为含义复杂的隐喻。 在作家夫妇出场之前,小说沿着乔戈料理杀人后事的单一叙述前进,讲他穿过茫茫雪野,前往“欧罗什的库拉”缴纳血税的孤苦历程。这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卡夫卡的《城堡》。而巴西安和迪安娜经历旅行,却渐行渐远的过程,则更为隐晦。卡达莱写了两人之间围绕着卡努的大量对话,多少有些海明威式的,一方喋喋不休,另一方心不在焉,印证着作家的脱离现实,以及两人的貌合神离,又将妻子推入对杀人者的浪漫幻想之中。 蜜月旅行临近终点的时候,迪安娜突然消失了,只身一人进入了禁闭着男性杀人者的庇护塔。丈夫焦急地四处寻找,当她终于走出,尽管衣妆完整,眼中却是一片空洞。这是小说中的最令人费解之处。她是去寻找杀人者乔戈吗?还是仅仅想以这样一个出格的举动,来报复丈夫对她的忽视呢? 此前小说中多次提及,卡努法典规定了“嫁妆子弹”的存在:“新郎在新娘试图离开他的时候,有权杀死新娘。” 巴西安没有这样的子弹,也没有得到答案,甚至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 “而你,你自己,你要去什么地方?片刻之后,他问自己。孤单地在这外邦的高地上,在这如幽灵般阴暗飘忽的人群间,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卡达莱和霍查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一统阿尔巴尼亚文坛天下的时代,卡达莱这样的作品能够出版,本身便是一个奇迹。 从20世纪50年代起,阿尔巴尼亚的小说、诗歌和电影作品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但卡达莱的作品不在其列。他本人是历史专业出身,作品也多以古史为依托,借古喻今,为此一度遭到该国文艺主管机构对他沉迷历史和民间传说、故意逃避政治责任的批判。 1998年,在接受欧洲一家电台的采访时,卡达莱曾说过,在阿尔巴尼亚,“有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真正的文学,类同于伟大的世界文学,有其杰出的遗产,第二种形式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他不是第二种形式的御用作家,但也没有被归入对立的一方。从他本人来说,更不是恩维尔·霍查生前的反对者。 1936年,卡达莱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靠近希腊边界的山城吉罗卡斯特,与战后统治该国数十年的霍查同乡。霍查喜欢拜伦,也曾经喜欢作为青年诗人的卡达莱。他们两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便是对法国的良好感觉。 国内的东方出版社版曾于1993年出版过南斯拉夫人佩罗·兹拉塔尔所著的《霍查政治传记》,其中写道:法国是“一向好斗的恩维尔·霍查最不想与之吵架的国家”。霍查曾留学法国,曾努力以法国为榜样来制定阿尔巴尼亚第一部宪法,早在打游击时就十分敬佩戴高乐,一向为真正了解法国的历史和文化而自豪。“他和法国人建立了很好的文化关系,巴黎文学界曾极力推荐阿尔巴尼亚现代作家伊斯迈尔·卡达雷的小说《死亡军队的将军》(拥有最多的外文译本)获诺贝尔奖。” 1985年霍查去世后,卡达莱甚至投书法国《世界报》,抗议该报刊登的反阿尔巴尼亚言论: “毫无疑问,你们的记者有权对某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对某个国家主张的思想和它的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然而,我觉得,当一国人民处于悲痛时刻去侮辱他们,如同贵报的文章那样,是不光彩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有摆脱苦难的悠久历史,因此他们很懂得为了什么而感到痛苦,如何表达和为谁而忧伤。恩维尔·霍查的名字无疑地已扎下了根基,植入新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和建设。这就是决定他的个人的伟大和对他深切悲痛的东西。”(《霍查政治传记》,第428页) 上文提及的《死亡军队的将军》是卡达莱出版于1963年的小说处女作,于1992年以《亡军的将领》之名在中国出版,但并未让我们牢记作者的名字。直到2005年他获得首届布克国际奖之后,这位早已移居巴黎的阿尔巴尼亚作家才重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宁死不屈》和《第八个是铜像》的善意的怀旧者来说,《破碎的四月》很有可能大大颠覆我们遥远记忆中的观感:原来阿尔巴尼亚也有文学,也曾有过这样的文学。 谁是伊斯梅尔·卡达莱 去年6月,阿尔巴尼亚作家和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Kadaré)赢得了首届布克国际奖。卡达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成名于霍查时代,但卡达莱并不是当时阿尔巴尼亚官方最欣赏的作家。1990年10月,阿尔巴尼亚政局激烈动荡之际,他获得法国政府的政治庇护,移居巴黎,并很快开始用法语写作。 早在1964年,《世界文学》11月号刊出了李定坤所写的访阿记录——《和阿尔巴尼亚作家们在一起》,介绍过这位霍查喜欢的诗人。他的诗作,后来也有零星中译。他的小说《亡军的将领》1992年曾在中国出版,由巴尔干文学专家郑恩波翻译,收入作家出版社的“作家参考丛书”,但由于印数只有2500册,故内地读者对他所知始终不多。台湾地区则在几年前出版过他的小说《欲望金字塔》。 近年来,卡达莱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颇高。虽然只有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94万元)奖金、首创之初的布克国际奖,尚不能与诺贝尔奖相提并论,但这应该是这位出身南欧小国的作家赢得全世界承认的重要一步,相信从此以后,他也会很快为更多的中国读者所熟悉。 (康慨) 伊斯梅尔·卡达莱作品 《破碎的四月》 3月17日,青年乔戈枪杀了科瑞克切家的泽夫。此后,在为期30天的贝萨(休战)期满之前,他暂时不会遭遇命中注定的下一次伏击--被科瑞克切家的另一位复仇的正义者杀死。乔戈的4月因此被截断:4月17日之前,是苟活的日子;之后,是注定的死亡…… 《亡军的将领》 《亡军的将领》是卡达莱的成名作,书中写到一位意大利将军,在战后回到阿尔巴尼亚,收集当年战死在此地的部下遗骨,这桩痛苦的使命,几乎令他神经失常。他意识不到的是,自己也早已成为一具行尸走肉: “几万具士兵的尸骨埋在地下那么多年,等着他的到来,现在他总算来了,好像一个新的救世主,带着大量地图、名册和准确无误的方位,这些东西,可以让他把他们从泥土中挖出,奉还其家人。别的将军已经率领这些无尽的军队,走向了失败和毁灭。而他却在墓地之间奔波,寻找这个国家里的每一处战场,将它们复原……” 《亡军的将领》后来拍成电影,由意大利明星马尔切洛·马斯特洛亚尼主演。 《音乐会》 1988年,卡达莱在法国出版的《冬末的音乐会》,被法国的《读书》杂志评选为当年法国最佳小说。此作以多少有些荒诞的笔法,嘲讽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一群傲慢的上层官僚,正是他们对友邦大国的指手画脚,破坏了与中国的关系,也深刻描写了中阿关系对当时阿尔巴尼亚普通人生活无处不在的影响。此书的英译本《音乐会》(TheConcert),还使用了一幅高大的陈毅元帅塑像照片作为封面。 (康慨) 图: 《破碎的四月》,(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著,孙淑慧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1月版,18.00元。 曾导演过《中央车站》和《摩托日记》的沃尔特·塞利斯(WalterSalles)将《破碎的四月》故事搬到巴西,拍了《太阳背后》。 英译本《音乐会》书封。 |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