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当教授大学会“文学”起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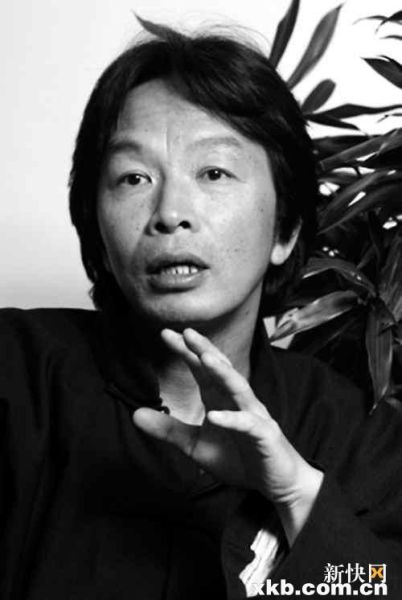 |
 |
 |
去年5月,刘震云正式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此前,阎连科已先于他跨进这所大学的校门,坐到教授的“交椅”上;同年9月,二月河出任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年末,王蒙也接受聘书,成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和讲座教授;而早在数年前,王安忆、马原、莫言、梁晓声、王刚等也纷纷步入高校……这些著名作家在万众瞩目之下进入大学,将给僵化的体制内文学教学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学校、学生又将如何接纳他们?追踪他们的校园遭际,探索其中的文化意义,或许正是时候。
当前大学生难以接纳作家式教授
执教中国传媒大学的王刚,第一节课就挨了当头一棒。
那天,他在课堂上谈起契诃夫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等文学经典,并穿插着聊起自己在意大利诗情画意般的经历,最终却“失望”地发现,台下竟然沉寂一片,“他们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
此后,他作为教师代表到外地招生,在问及面试者都读过哪些书籍时,他们竟不约而同地举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变形记》、《老人与海》和欧·亨利的小说。但稍加考察,他便发现,这些学生几乎没有读过原著,而只是通过策略培训班的“参考答案”,对这些作品做过简单了解。
对文学经典的陌生,对非灌输式教育风格的不习惯,使得当下在校大学生接纳作家式教授相当有困难,这是作家们始料所不及的。
同为人大文学院教授的阎连科对这些学生深表同情:“在最可以读书、最需要读书的时候,他们在应付考试。如果花很多时间读《红楼梦》,也就没有时间把分数提上去了。”所以,这些学生尽管考上了大学,进了文学院,对他们来说,文学依然是“奢侈品”。
作家如何引导大学生转向文学
“今天的老师要想发出微弱的光,都很不容易。”王刚渐渐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他所面对的不是一帮文学青年,相反,其中很多人对文学既无兴趣也无准备,他们更倾向于接受能立竿见影或有“笑果”的东西。
学生们对老师所推崇的经典提不起兴趣,对自己的作品和“偶像”却珍爱有加。几经琢磨,王刚从这里找到了渠道。从此,他在课堂上会冷不丁地把学生请上讲台,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会选择他们所追捧的《失恋33天》或东野圭吾的作品,由此来讲述自己的剧作经验和文学理念。在大家竞相“燃烧”以后,他才试探着带领他们体悟契诃夫、托尔斯泰的魅力……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梁晓声更愿意采取“劝”的办法。他对学生直言,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我们重点开发了理性思维和记忆的脑区,相当一部分人的感性脑区,还处于睡眠状态,“这一部分脑区在人脑中是相当宝贵的,像矿藏一样,像礼花一样,中文教育就是要把它开启,一旦调动了这种想象的能力,你们会感到非常愉快。”
刘震云应对的办法却是“骂”。面对学生的质疑,他会毫不客气:“如果你们想稍微有点出息,一定要把过去的思维模式转过来,这样才能更接近刘震云,更接近孔子。”他提醒学生:“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闻一知一。鸡鸭为什么不能同笼,鸡犬为什么不能相宁?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本身需要教育。”
大学要给人文留下呼吸的空间
长期以来,文学院没有作家,文学渐渐变成了教授口袋里的教案,变成了教材上条分缕析的知识点。“在大学校园里,已经多少年没有沈从文的影子,没有张爱玲的影子,甚至萧红的写作,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但现在的情况可大不一样了。”阎连科提醒到,因为作家的到来,“文学”在校园里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也许我们从文学史上学到的作家今天看来并没有那么伟大,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他的写作却可能更有意义,作家常常会讲被文学史忽略的东西。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不同于教材的、更为新鲜的视角。”
阎连科也认为,人文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让人去感受,而不是量化;让人去一天一天地养成,而不是一时一刻就立竿见影,“人文是要流到血液中去的,而不是穿在衣服上,正因为要流到血液里,所以不能量化,不能一眼就看到底。所有可以立竿见影的人文,一定是荒谬的人文。”
事实上,由于长期惟量化指标、尤其是惟论文马首是瞻,当下大学的文化生态已然出现很大问题。而更由于考评体制的限制,如今,只有格非、曹文轩等数位学者型作家能在大学立足,而更多的人,在此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文学院里应该有文学,这正是我们当初引进作家最基本的动机。有创作经验的人和有学理思考的人结合在一起,可能会使我们的文化生态更加活跃和丰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说。
“如今高校的教学氛围,太需要激活一下了。”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战军认为,“将作家引入大学,而且,并不将其纳入统一的评估体系之内,这将有可能打开一道缺口,给人文留下呼吸的空间。” (据北京日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