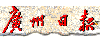|
|
|
傅聪纪念傅雷百年诞辰 独奏音乐会5月广州登场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28日10:23 广州日报大洋网
 傅聪将在广州开钢琴独奏音乐会 1908年,一个哭声特别响亮的孩子降生在江南望族,长辈们给他取名为“雷”。他日后成为当代伟大的翻译家、文学评论家、音乐鉴赏家。作为翻译家,人们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译介的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可是,这些都不及他的另一个身份著名,那便是“父亲”。 他的儿子对古典音乐有着先天的狂热,21岁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奖项,如今被称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肖邦的最佳演绎者”和“钢琴诗人”。 这对父子便是傅雷与傅聪。 5月11日,“纪念傅雷诞辰100周年傅聪钢琴独奏音乐会”将在星海音乐厅登场,傅聪将以他善于雕刻细节的手在乐声中描摹与父亲永远相通的那颗“赤子之心”。 父亲 暗夜永别成绝唱 1966年9月2日夜,傅雷、朱梅馥夫妇留下遗书,双双自缢。多年后,作家陈村写过一篇名为《死》的文章。他和傅雷住在同一条江苏路上,生命中有十二个年头和傅雷的生命重合,却始终没有见过这位译匠。陈村曾在图书馆借阅《欧也妮葛朗台》,但那本书没有封面和扉页,没有译者的名字,他也不知道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就是译者的家,小小的花园内曾种满怒放的月季。在书房里,傅雷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翻译《幻灭》,用精致工整的楷书为儿子抄写6万字的《艺术哲学》,写几十万字的家书。所有的一切都在那一夜停止了,花园内的月季被粗暴的手连根拔起,书房内的山水画和条幅撕成碎片,践踏在无知的脚下。 慷慨悲歌、刚直不阿,是傅雷性格中最具识别性的要素。同时代人说起傅雷,总是“孤傲如云间鹤”。作家郁风一次和傅雷辩论,反驳不倒,情急之下,说傅雷是“老顽固”,而傅雷郑重地、一字一字地说:“老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傅雷在精神道德上是有“洁癖”之人,正如他所强调的“classic”,不仅仅是古典,还带有使他自豪的最优秀、最完美、第一流。 傅聪说:“2004年我在以色列的卡梅尔剧场看话剧《安魂曲》,那位受尽苦难的老太太梦见自己已故的父母,在梦中看到他们正坐在阳光下欢笑,于是便迫不及待想加入进去,忘记所有的过去和将来,只要现在这欢笑的一刻,和他们在一起……那也是我多次梦到过的。” 爱人 三次婚姻漫随流水 父母双亡的剧痛、远走异国的惶惑,在傅聪后来的日子里,化为三段感情的失与得。 他最初的姻缘令人羡慕:迎娶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爱女弥拉。这段持续了十几年的婚姻,终因“东西方人秉性差异太大”而和平结束,两人所生的儿子凌霄现在新加坡,经营洋酒公司;傅聪与韩国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的第二次婚姻只维持了3个月便告失败,之后他遇见了自己现在的夫人卓一龙——原籍厦门的女钢琴家,当年从香港考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钢琴系并留校任教授。如今,两人已携手走过30多年的岁月。两人所生的小儿子凌云则住在伦敦,刚拿到伦敦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不久。 傅聪夫妇的寓所在伊斯林顿——伦敦东北角的名流社区。“我家里有五架钢琴,现在只有两个人弹了,我们各自有琴房,平时只在早晚吃饭时见面,家里有佣人,杂务都不必操心。我夫人有时做些园艺,她那片玫瑰园就在我琴房的窗下。”天气好的时候,傅聪夫妇俩也会一起出门,开上20分钟的车到牛津大学散步。 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简单的生活,然而傅聪也能理解如今许多年轻人对功名的渴求,“欲望也并不全是负面的,它也能推动人做成不少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你首先需要有清醒的头脑。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的来临,你能享受的物质快乐会越来越少,到那时,很多事情自然变成了不必要的。记者龙迎春 通讯员刘悠扬、乔雪阳
【发表评论】
不支持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