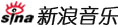|
|
痛苦的信仰:继续痛苦穷摇 升华坚定信仰(图)

痛仰主唱高虎
文/刘颖 摄影/高虎
是不是应该表示遗憾?或者感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痛仰”乐队的主唱高虎已经离开北京去了云南。这并不是一次满心欢喜的年度休假。实际情况是,高虎已经负担不起他在北京通州区住地的房租,他选择去消费水平低于北京的云南“避难”。“有朋友在那边,正好也静一静,整理一下我的新歌。”高虎这么说的时候,没有什么表情,声音很低,与舞台上的他判若两人。与此同时,从10年前“痛苦的信仰(听歌 blog)”乐队组建伊始就陪伴高虎的江苏同乡、贝斯手张静已在此前退出乐队。据另外一位江苏籍好友私下透露,年过三十、没有工作、没有成家、生活压力、家庭压力……这些显然“敦促”张静选择离开没有给他带来基本保障的、他当年用青春和理想去投身的摇滚乐队。
确实要感慨!——这两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摇滚圈“复兴”现象。全国各种音乐节不断、北京各种演出剧增,有时甚至一天有三四个都非常值得看的演出“大撞车”。“老”到崔健(听歌)、何勇(听歌)、张楚(听歌),“中”到谢天笑(听歌 blog)、苏阳、万晓利(听歌),“青”如“刺猬”、“赌鬼”、“后海大鲨鱼(听歌)”……满眼的乐队都“走起来”了。“老”人有各种活动、演出养着,“中”人签约了有“风投”资金当后盾的公司、拿到了工资,青年新人甫一亮相就能迅速圈起一票铁杆歌迷,而且他们大多有固定工作甚至家境殷实——一切似乎已进入良性循环。但,大多数不代表全部。甚至可以说,表面不代表真实。高虎刚刚发行了“痛仰”新专辑,10月25日在星光现场办了爆棚的演出,没过几天他就去了云南“避难”。“我一直都在透支度日,而我再也不能伸手向亲戚朋友开口了!再也不能!”高虎离开前接受采访时这么说。11月1日,苏阳参加了“你在红楼,我在西游”的主题演出。之后,他向公司同事借了几百元——因为他自己没有足够的钱买火车票回银川。Joyside给匡威拍了广告、又去香港进行了巡演,但“荔芙唱片”的员工表示,主唱边远依然穷困潦倒……
在音乐方面,有一些听众,特别是之前喜欢“痛苦的信仰”的听众对“柔化”的新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表示反感。他们认为“痛仰”已经像了许巍(听歌),失去了地下状态的血脉贲张。他们可能是只看到“痛仰”们在舞台上的风起云涌,不知道他们在生活中却是天差地别的艰难。与少部分歌迷的反感相对,更多的听众则对这张新专辑交口称赞。其中,新歌《西湖》更是得到了很多非摇滚听众的关注,并且在北京音乐台等的广播节目中被多次播放。对于这首歌,高虎解释说:“当时去杭州巡演,但演出、接待、环境都不太好。匆忙赶往下一个城市前又匆忙去了西湖,发现同样也不是想象中那个样子。于是就写了这首歌。”在最初把乐队定名“痛苦的信仰”时,似乎就有一些悲剧式的命中注定。而高虎此次放弃了过去的怒吼方式、抒情唱出的“再也没有流恋的斜阳,再也没有倒映的月亮,再也没有醉人的暖风,转眼消散在云烟”似乎也是他们当前状况的一个印证。
对话高虎
许巍变平淡了,汪峰(听歌 blog)变主流了,谢天笑变柔了,如今你们也不再“硬说”,改温情歌唱了。一些歌迷对这种改变不能接受……
这其实挺自然的。在思想上,至少两年前,我就开始觉得做音乐应该让路走得更长一些。你知道吗,之前我们的《这是个问题》和《不》,我们家里人都不愿意听。白居易写诗会自我要求让不识字的老婆婆都能听懂。我也希望有一天能让我的家人和更多的人都能听懂我的音乐,让摇滚圈外的人也能接受我们的音乐。
在小环境上,我这些年本身听噪的东西就很少了,更多听电子、雷鬼、Trip-Hop以及其他的风格类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关于大环境的,就是我想跳出摇滚这个小圈子。摇滚乐队很容易慢慢变成一个小圈子,慢慢地大家一起封闭自己。当年我从霍营搬到通州,就是想跳出圈子。我更多时候更愿意跟普通人接触,他们不一定听摇滚乐,但却有着更多的生活内容,交流的话题范围也更广。
宗教性的东西也给了我影响,我虽然没有皈依,但大乘佛教关于“大爱”的一些教义让我思考了很多。今年8月8日我在MAO演出后,一个人送了本《圣经》给我,里边还夹了张纸条,写着“感谢你一直用生命去做音乐”。当时我看了之后就感觉在自己绝望孤独的时候,这根神经还是有人牵着呢,还是有人关心你的。我也一直在听鲍勃·玛利的音乐,他在得了癌症后依然通过音乐去散播那些温暖的东西。这也让我知道,那种操起拳头、竖起棱角的方式其实不如温暖的声音有力量。
“痛仰”之前的音乐、歌词,那种口号、煽动性几乎就是你们的标志性内容。可新专辑的音乐、歌词转变这么大,甚至开始诗情画意起来,有的人就会觉得你们不摇滚了。
我觉得真正的摇滚,就是在每个时期都真实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而不是僵化于某一音乐形式,违背内心去做“摇滚”的样子。之前我们的音乐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前十几年生活、感情的总结。在我们最需要表达的时候,我们用那种方式表达过了,就足矣了。我不想让这些‘标志性’像商标一样贴在我身上,不希望我永远带着商标去上路、做音乐。
之前我听音乐、做音乐,还是很追求“最新的”、“时尚的”、“跟世界同步的”。我也知道,做《不》那样的音乐,听众都喜欢。而且我们做这种歌非常快,可以做上一批。但这对我们来说没有挑战性。你看U2( 听歌)、“红辣椒(听歌)”这些真正的大牌都是敢于颠覆自己的。如果现在我们还做前两张专辑那样的音乐,就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我们精神内核的东西,只是把一些元素“拼”成一首歌,那样的话我们自己也会很累。
听歌)、“红辣椒(听歌)”这些真正的大牌都是敢于颠覆自己的。如果现在我们还做前两张专辑那样的音乐,就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我们精神内核的东西,只是把一些元素“拼”成一首歌,那样的话我们自己也会很累。
不少听众都惊讶于你新转变的柔一些的唱法。你是受了谁的指点吗?
这种唱法对我来说等于从头开始。刚开始唱的时候我也很怕周围的人笑话。但慢慢地他们说一些歌听了很喜欢。鲍勃·迪伦(听歌)的嗓子也不是很好,但他会找到他的特点。其实这么唱也是经历了一系列影响和“自我改造”的。在2007年我们乐队成员各自远行的途中,我去了我出生的新疆。到乌鲁木齐的时候,一些玩音乐的朋友聚在一起,喝酒之后每个人都唱一首歌。轮到我,我突然觉得我唱不出来!特别难受。我觉得我心里很空,我发现我心里没有我最想表达的歌曲。所以才想在新专辑里进行改变。
后来我又去了英吉莎。一个朋友带我去了一个水库,在那露宿了一宿。我们钓鱼、弹吉他、喝酒、唱歌。但我感觉我的声音只是“哼”出来,怎么也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么“大”。我原以为,我在城市待得太久太压抑了,总怕大声会影响到别人。但我到了野外还是放不开,我的内心还是在封闭着。
我继续上路,又去了西藏、尼泊尔、云南。在2008年的大年三十,窗外是一片烟花和过年的热闹,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拿出我这几年积累的素材,抱着吉他开始写这张新专辑里的歌。这时候我知道我的那些疑虑已经过去了,唱歌不是音量的问题。在今年迷笛上,现场我看出来新歌的煽动力比以前弱,但这没什么。我就是想让更多人感受到一些新的东西,别老是在那撞来撞去的。音乐其实也可以舞蹈、甚至可以静静地待在那欣赏的。
其实我现在也会接到说我唱得不是特别好的反馈。唱歌我确实是野路子。但我觉得摇滚乐不是成为很有天分的歌手再去做的东西,而是你拿每个时期最真实、最好的东西去尽力而为,是随着我做音乐一点一点往上走。我从来不认为某张专辑是完美的,它只是特定时期的一个记录。所以目前我可以接受我的唱法。
2006年《不》全国巡演的时候,你们的状态还是暴躁、激昂。2007年你们各自独行。2008年你们就以一个新的状态出现了。就像新专辑的封面,哪吒不再像《不》那样含恨、怒目。而是双手合十、闭目、宁静。给我们讲讲哪些关键点导致了这些变化的发生?
去各自远行,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女朋友提出结婚,我却拒绝了。我不想多说这件事,反正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全身心去做音乐这条路。写歌不能空在家里去创作,需要找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决定去远行,也许会很辛苦,但可以让精神真正放松下来。
在新疆家乡,我爬了天山。以前我的家乡是个工业小镇,现在已经衰败了,两万人的工厂现在只剩下六七千人。后来我又见了几个叔叔阿姨,还去看了我的小学,碰见了我的一个同学,他已经完全是一个中年人了。这让我突然想起当年我们一起玩,一起激动地买来“唐朝(听歌)”的磁带,一起查电视台什么时候放他们的MV,然后去找有录像机的同学录下来,大家一起一遍遍地看,一起激动……这些似乎又让我清楚了我想要什么。
然后我去西藏,搭了一辆油罐车。全程1500多公里,只有200公里是柏油路,剩下的都是各种颠簸的土路。我们开了三天四夜。这一趟是我永远难忘的经历。无尽的山、无尽的黑夜,一二百公里才能见到一辆车,瞬间就开过去。快到西藏的时候,我们遇上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风沙,当时我就想起“唐朝”的一句歌词“黄沙漫天”。虽然路途挺苦的,但我在北京时浮躁、喧噪的心却平静了下来。
还有鲍勃·玛利。在树村的时候,就有朋友给了我一套鲍勃·玛利的专辑,但我听了几首觉得不喜欢。后来在霍营,有一次我听到了《No Woman No Cry》的现场版,当时一下就把我原来的概念都颠覆了。我发现我很自以为是,但其实是盲目和错误。现在我对任何音乐都不会很武断地去下定论。
不过到现在,鲍勃·玛利的歌我也只会唱《Three Little Birds》,但每次看歌词,心里都还是暖暖的。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不是金属、朋克,而是鲍勃·玛利他们那些温暖的歌曲让我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大爱的力量才是更包容、更有力量的。我现在做这样的音乐,就是想带出更多温暖、感动、向上的东西给听众。力量、对抗是外在表现,如果你更内敛一些,反而能影响更多人。此外,莱昂纳德·科恩、“皇后”乐队、鲍勃·迪伦也都是对现在的我有影响的大师。
最后,有什么关于大环境、关于未来的想法要说吗?
在中国做乐队太难了,很多东西跟当初的想象完全是两码事。有很多音乐之外的事要去解决。我们一直坚持独立制作,一方面是想有更多音乐上的主动权,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因此绊住了手脚。一个人其实做不来那么多事情,精力毕竟有限。其实我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只管音乐这一块。因此我们也跟一些公司有过接触,但目前还没有结果。
在中国做摇滚乐,只有第一帮“老炮儿”的生活能自给自足,余下绝大部分还是穷摇。越是这个状态,人越压抑,表现的东西越都是绝望、无奈、愤怒。但这绝对不是摇滚乐的全部。我相信坚持,我们内心还有不会被击倒的东西,它才是我们生命永远所在的地方。
我觉得之前我荒废的时间太多了,从今年开始我想认真地做些东西。鲍勃·玛利、“披头士(听歌)”他们都写了几百首歌,为什么我不可以?我觉得中国乐队的作品不论是量还是质都还远远不够。我有幸选择了摇滚的生活,我还有很多内心的东西要去表达,有很多很好的旋律在我脑海中,我还要把它们唱出来呢!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相关专题:《音乐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