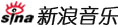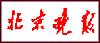|
|
女高音吴碧霞14日走进国家大剧院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12月14日将在国家大剧院举办“归来·碧霞2008”独唱音乐会,这是她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马里兰大学留学两年后,首次归国“汇报成绩”
从2003年起,吴碧霞在国内外举办了30多场个人独唱音乐会,出版了十余种个人演唱专辑,被誉为“中西合璧的夜莺”。但就在她事业的黄金时期,吴碧霞出人意料地推掉了演出,在2006年去了美国继续深造。在跟随两位国际著名声乐教育家玛拉斯和卡门教授学习过程中,吴碧霞逐渐摆脱了民歌、美声这两种音乐形式的束缚,回到一种最自然的状态,用心去歌唱。
记者:你已经在国内赢得了那么多赞誉,为何突然要去国外留学,几乎从零开始奋斗呢?
吴碧霞:我觉得学习得远远不够。如果我哪天觉得唱歌没有什么难的,只要抓住几个要点就行了,这意味着我要进入一个非常模式化的状态中。过去很多东西要靠别人介绍和自己想象去获得,但亲身体验就不同了。也许只是聊聊天,也许只是走在美国的马路上,坐在地铁、餐馆里,这些东西都是音乐的源泉。
记者:在歌唱方法上,国外美声与国内美声、民歌的演唱,有没有本质冲突?
吴:没有,一点儿都没有。在这一过程中,我甚至感觉到一种对自然的回归。当我们学习声乐唱法学得太多的时候会有一种束缚感,这也是我一直想要挣脱的东西,想找到音乐的自由。原来我常常会想:现在我正在唱民歌,或者现在我正在唱美声。实际上这种不断在你脑海里强调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束缚在捆绑着你,阻碍你往前走。歌唱本身并不需要我们去区分到底是民歌还是美声,它仅仅是歌唱。
记者:在国外演出你是以民歌演唱为主还是美声演唱为主?外国人是怎样看待中国民歌的?
吴:都有,我觉得外国人挺喜欢中国民歌的,因为我选择唱的也都是艺术性、可听性都很强的经典民歌,如《小河淌水》、《兰花花》、《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别意难》等,我在美国学习时的老师卡门特别喜欢《小河淌水》,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有一次卡门邀请他的牧师朋友们到他家做客,晚宴后我给他们演唱了这首歌,唱完每个人都流下了眼泪,他们觉得中国音乐太美了,这时歌词已经不重要了。
记者:通过和国外的音乐学习,您认为中国的民族音乐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创出自己的品牌,都需要做哪些努力?
吴:外国人虽然喜欢中国音乐,但他们对中国音乐了解得太少,甚至有很多偏见,认为民族唱法的发声是挤的、捏的、靠前的,美声是宽的,民歌是扁的。要想改变这样的偏见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问题。我记得在马里兰大学进修时,那里有个小戏剧厅,有天晚上有场京剧演出,人很多,我等到上半场结束才进去。当时舞台上演的是京剧《三岔口》,后来又演出了用幻灯片制作的皮影戏,我的第一感觉是一种荣耀感,随即感到的就是心酸,因为京剧演出放的是伴奏带,道具简陋,演员的动作也多少有些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但这些“拓荒者”如此条件下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做着积极的努力,但这不是在西方开一两场音乐会就可以解决的,是每个人不计代价不计成本的付出。
记者:你快乐的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你与众不同的笑声,像唱花腔一样,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笑特别吸引人?
吴:我从小就是这么笑的,记得12岁在民族宫大剧院演出,唱《一个美丽的传说》,在演唱过程中台下鼓了12次掌,我高兴坏了,也完全放开了,忘记了自己是站在台上表演,大笑起来,把台下观众都逗笑了。1991年我和邹文琴老师去青岛演出,在火车车厢里就听见我一个人在那儿笑。直到现在我笑的时候也特别随性,笑完了才意识到别人都注意我。
记者:前几年举办30多场音乐会,有人说这样挺傻的,为什么不走多上晚会这样的“捷径”呢?
吴: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这话说起来挺吓人的,但这确实是件神圣的事。我觉得自己最光彩也最具个人魅力的时候就是在舞台上,和观众面对面时。我也许是国内举办个人音乐会最多的人,确实很累很辛苦,嗓子运用不得当还会伤身体,但我还行,我挺扛造的。回想起自己的30多场音乐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虔诚的苦行僧,每个音乐会就是朝圣路途上的一步,但只要心中有梦想我就很快乐。
记者:周日的音乐会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吴:这次音乐会将依旧延续我以往”中西合璧“的风格,半场中国作品,半场外国作品,打破艺术之间的壁垒,演唱施特劳斯、伯恩斯坦等人的通俗作品,绝大多数曲目是中国观众不曾听过的,还有作曲家孟勇的新作《雪花》,是专门为这场音乐会创作的。
本报记者罗颖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更多关于 吴碧霞 的新闻
-
吴碧霞自嘲脸皮变厚 14日走进国家大剧院 2008-11-25 00:00
吴碧霞归来独唱大剧院 延续中西合璧风格(图) 2008-11-24 14:56
花腔女高音吴碧霞将在大剧院办独唱 2008-11-17 22:52
图文:开幕音乐会洋溢中国情-高音歌唱家吴碧霞 2007-12-22 22:30
2007北京新春音乐会主要演员-吴碧霞 2007-01-10 18:46
辉煌中国-辉煌民歌版块吴碧霞简介 2006-12-08 20:01
《唱山歌》:吴碧霞《知己》专场 2006-07-31 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