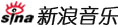|
|
2月13日情人节前夜 沙子乐队MAO专场(图)

沙子主唱
时间:2009年2月13日,周五,9:00pm
演出乐队:沙子 SAND Band
票价:50元
沙子”的态度
改变现实不是我们的任务
“沙子”敢于称自己是艺术家,同时坚定地认为艺术家没必要改变现实,这不是艺术家的任务,而且没有任何人的任务是改变事实。艺术家的任务是观察生活,记录现实和表现现实,但艺术家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只要你有一颗敏感的心,愿意去观察生活,把它反映出来,你就是一个艺术家。
杀死传统因为好的传统死不了
从小到大,我们接受到的所谓的传统是经过筛选的传统,是不完整的,是故意制造的假象。你在背叛这些传统教育的时候,完全可以踏踏实实,彻彻底底地根本不用考虑任何责任地杀死这些东西。因为所有有生命力的东西,一个人也好,一代人也好,是杀不死的。你不用担心好的传统被扼杀了,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扼杀它。
三种人和三种物质
“沙子”乐队的灵魂、主唱刘冬虹认为世界上有三种人:奴隶、奴隶主和革命者;世界上也有三种物质:狗屎、金子和沙子。狗屎想要通过努力成为金子,而沙子则成了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它是唯一可以从本质上超越自身价值的。的确,“沙子”的音乐一直贯彻着这个充满野心的想法。
生理摇滚
很多人说摇滚就是叛逆的精神,是某种形式上的东西,刘冬虹挺不屑于这种看法,他觉得摇滚就是一种“摇”、“滚”的感受,就是你身体上所能感到的巨大的快感,或者是在快感来临之前的一种非常原始、非常本质的“蓄势待发”。
我们不“噪”
“噪”就象女人画在脸上的油和粉,客观地说,那是刺激,但是简单到了让人很快就厌烦的地步。“重”与“不重”并不重要。音乐很“噪”并说明不了什么,从音乐中传达出来的那种真正的律动感让你永远能想像到人与人之间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亲密的感觉,有些东西越慢,越深,越能表达所想要表达的情绪感觉,重音乐和重感觉是不同的,有些音乐很慢很轻,但给人的感觉却更深更透。
去所有的地方演出
“沙子”喜欢去所有的地方演出,在体育场里演,在酒吧迪厅里演,在大学里演,还盼着在大街上演,在火车上演,在公园里演,跟马戏团一起演,还准备文艺下乡。只要是能有听众的地方就可以演出,只要没有什么破圈子。按北京话,他们管这叫去四处“浪”。
有关“沙子”的声音
“在别人以为他们已经消失的时候,‘沙子’逆向找着了摇滚的正根儿。他们同那一些音乐语言贫瘠的人不太一样,不在姿态上使劲,而是把乐队弄成了一台创造出能量的发动机、听得见呼吸的活体,这话说起来挺容易,可是你扳着指头数数,还真数不出几个这样的中国乐队。歌词?你说是喊口号容易,还是过脑子的有生命力?”
—— 郝舫(著名乐评人)
“那期节目我刚放完‘沙子’的歌,就有人打电话来提意见,结果《新音乐杂志》从那期起就从直播改成录播了。可是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放‘沙子’的歌。”
——有待(著名新音乐节目主持人)
“第一次认识‘沙子’是在约两三年前,那时‘嚎叫’还开着,有一天晚上‘沙子’来演出,这是他们首次来‘嚎叫’亮相,我和观众对他们都不熟悉,但当音乐一响起来,我就喜欢上他们了,与常到‘嚎叫’演出的乐队不同,他们无论从气质上,还是从音乐上来讲,都显得很特别。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形:小屋里站了三四十名观众,大家全挤在舞台前,没人跳,没人喊,就那么静静地听着,不是音乐不吸引人,而是太让人关注了,我注意看了一下大伙儿的脸,他们全都在目不转睛的盯着台上表演的沙子,那种专注的神情
......我想,那天晚上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沙子’震住了。”
——吕玻(京文唱片公司总监)
“几年前在方庄的一个酒吧有场演出,我坐在外面和朋友聊天,当时没什么名儿的‘沙子’正在里面的台上演出,那时他们各方面还不成熟,有个朋友开玩笑说:‘这可真是一盘散沙啊。’那时我也是第一次听‘沙子’的作品,但我跟他说:‘你们都没听出来,其实这支乐队的有一个特别棒的吉他手,他弹的吉他是我所听到的国内吉他手中最有感觉的。’”
—— 祖咒(中国另类音乐的代表人物)
“2000年,《星星落在我头上》是我唯一愿意自掏腰包买的中国摇滚乐专辑。”
——开寅(影评/乐评人)
“有一天刘欢过来找我,跟我说最近听了一首歌特棒,名儿也挺怪,叫‘膏药’......”
—— 高晓松(著名音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