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小珂》到《再见 乌托邦》 如果不叫摇滚

何勇的精神状况极不稳定,长期服药,时不时仍需要入院就医,前一年他总共只有三场演出,何勇有时候会想找滚石要点钱:“这么多年唱片一直卖着,彩铃什么的,一分也没给过。” 图/盛志民

窦唯在影片里拒绝说话 图/盛志民

“中国摇滚乐教父”崔健很清楚,市场并不那么需要摇滚乐 图/盛志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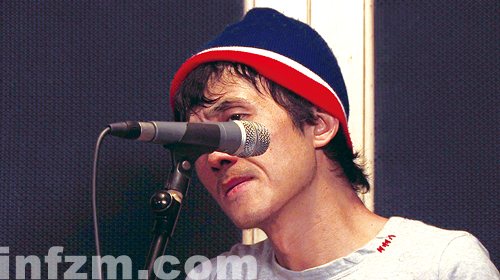
张楚从1997年出版《造飞机的工厂》之后自闭8年 图/盛志民
我一直以为他们开着凯迪拉克
“二十年前他们发明了刀子歌,二十年后他们分别死去或者进精神病院,为合约跟乐队闹翻,也许愤怒如往昔但大势已去,不得不承认过去是个乌托邦。”一个香港网友充满激情地在博客里写下了《再见 乌托邦》的影评。
南方周末“影响力·全民乱拍”计划里,导演盛志民的纪录片最终定名《再见 乌托邦》。这部影片最初构思时曾名《寻找小珂》。1996年,曾经是“做梦”乐队吉他手吴珂从摇滚圈朋友的视野里消失。很多人都记得这个英俊的男孩儿,记得他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的造型;关于他的下落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他死了,至今也有人说他还活着。
在小珂的父母那里,并不存在第二种说法:他走了。1996年9月7日,小珂的母亲永远记得那个日子:“24岁,本命年,还差几个月。”这一天她从自己的录像店回到家,儿子已经离父母而去,他吞服了过量的镇静剂“曲马多”。
吴珂的父亲曾是中国录音总公司的音乐编辑,崔健的《一无所有》磁带就是他负责出版的,儿子跟着父亲出入录音棚,认识了许多乐手。1989年夏天,在长安街东延长线的八王坟,只有16岁的吴珂哭着求父亲,要搞摇滚乐。父亲答应了,给他找了吉他老师。为此他至今自责:“还是我害了他。”
在跟随采访过何勇、张楚、陈劲等摇滚乐手之后,影片的录音师有点受不了:“他们怎么这么惨?真难受。”“你以为他们会是什么样?”盛志民反问这个自己也弹金属吉他的“80后”。“我一直以为他们应该是开凯迪拉克,戴大钻戒,跟着几个小弟……”
3月25日,《再见 乌托邦》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准备好来看愤怒摇滚青年的人们不知所措,观影者后来在日记中写道:“这片子超出我预期。它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摇滚乐纪录片,自我、嗑药、叛逆、激情、反政治等摇滚主义的热血画面集体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失落、失语、反省、商业文化、产业、互联网经济、全球化等关键词,社会价值已随社会发展变迁,理想主义已逝,摇滚年代不再。”“影片中出现的人物都是我的好朋友,当年红磡让他们到了顶峰,而十几年后我又把他们带回了香港。”盛志民在红又专放映会后,告诉观众:这并不是一部谈摇滚的影片,这其实是一部讲述改革开放三十年代价的影片。
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10年
离世之前,小珂染上了毒瘾。父母辞掉工作,守着他戒毒,最后还是失败了。他的死是因为用药过量还是有意自寻了断,不再有人知道。但沾染毒品这件事,他的朋友们却或多或少要联系到“做梦”乐队的解散。
1991年底,离开“黑豹”的窦唯与陈劲、吴珂等乐手组建了“做梦”乐队。一年后,“做梦”乐队解散,直接原因是窦唯签约台湾滚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
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带来的这个厂牌陆续推出了《中国火》系列、《唐朝》专辑和后来代表“新音乐的春天”的“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张楚。1994年12月,“唐朝”乐队与“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来自北京的新音乐空前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创作力。“魔岩”也因此成为中国摇滚乐的一面旗帜。
但在轰动背后,却是唱片公司与摇滚乐手之间一笔说不清的烂账,和至今未能完全化解的怨气。“我看到每一个乐队,都没有好的器材,没有良好的资讯环境,没有外在的市场,没有财富的吸引。每个乐队都用生命,产生出强大的爆发力,而且风格各自不同。我觉得九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张培仁这样回忆他当年在北京遭遇的摇滚激情,而对唱片公司而言,这当然也是一座未经开掘的音乐富矿。
滚石唱片自称对中国摇滚乐的制作投入是不惜工本,一般用几十万成本制作的专辑,在中国的摇滚乐,他们舍得花300万。另一边,却是签约乐手抱怨合同不公平,报酬不合理。甚至到了2008年,当何勇与电台DJ张有待在鼓楼东大街一家餐厅见面,何勇还向张有待打听张培仁的消息,想通过他向滚石唱片要点钱:“这么多年了唱片一直卖着,彩铃什么的,一分钱没给过。”前一年他总共只有三场演出,“怎么活啊。”
另一个问题,是“魔岩三杰”的签约。窦唯、何勇、张楚,都有各自的乐队乐手,但唱片公司坚决只跟主唱签约,这给乐队带来程度不一的伤害,比如“做梦”的解散。但“魔岩”也是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据说当初签约“黑豹”乐队的公司,因为窦唯离开乐队受到不小的损失。
小珂的迷失,究竟是否跟这样的伤害有关,已经无可对证。盛志民的电影,倒并非要在这个话题上刨根问底,事实上谁也说不清楚。受访的音乐人大多强调着那个年代的纯真,同时重复并不新奇的论点——原本单纯新鲜、自然茁壮的中国原创摇滚乐,突然遭遇来自台湾的、圆熟老练的唱片业体制,那不是揠苗助长么。1992年正值“南巡”之后中国社会掀起“全民下海”的浪潮,本来“没有财富吸引”的摇滚音乐人似乎也被高高托到了浪头上,但是严重呛水。“我们受到的教育里,是不懂得这些的。”何勇说。“那时候谁知道唱片业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只有你进来了才知道那里头的沟沟坎坎。这是个过程,也得有点牺牲。”小珂的朋友说道,小珂是这样的牺牲吗?
中国不需要摇滚?
“摇滚中国乐势力”的高潮过后,“魔岩”的境遇并不好。张培仁离开大陆的“魔岩”回了台湾,说是赚三年钱再回来,但终于没有回来。到新千年之初,这面猎猎旌旗竟然消失了。
张楚从1997年出版《造飞机的工厂》之后自闭8年;他的成名曲《姐姐》也是他最大的困惑:“那是一个文学作品,你们非要问它的真实性,问我和姐姐发生了什么。唱了这么多年你们还没明白我是在唱什么,那我就不唱了。”何勇的精神状况极不稳定,长期服药,时不时仍需要入院就医。窦唯不再歌唱,甚至不再诉诸言语,这部纪录片当中他是惟一不说话的受访者——他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不适合用任何语言阐述自己的态度和认识,只提供了2007年南方巡演的画面和声音作为他的发言。
在影片中回顾15年前香港红磡的演出,会令人恍惚:所谓“摇滚中国乐势力”,是当真存在过,还是一场梦?
除了崔健,这些乐手如今只是默默地生存,曾经在台前的退到了台后,仍然留在台前的,大多时候也只重复着十多年前的老歌。“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受理想主义教育的,艺术肯定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上的,当理想主义没有了的时候,那艺术他妈的就没有了。”乐手陈劲和马培的断言。“当年他们是比电影、绘画都牛的,现在反而是被扔到了最底下。”盛志民说,“唱片业毁了,他们只能靠演出。但是他们又贵。毕竟红过,不愿意将就,他们一般都希望有好的乐器、环境、调音师,这都要花钱。这样的状况其实二十多年过去还是一样:最赚钱的方式是拿一盘伴奏带,一个人就来了;你一来六个人,演出商得管六个人的吃住、乐器、调音师……小地方做不起,大地方演出也没那么赚钱。”
窦唯稍显例外,他离开摇滚乐转向新的音乐类型,在南方,200元一场的演出他也愿意去,他认为自己应该走动着、演着。这样的价钱,常人一定难以置信。
2008年秋天,崔健在北京工体的演出,变成了怀旧歌曲大联唱,变成所有人感动自己和怀念自己青春的一个活动。那情形看起来跟罗大佑、周华健的演唱会没什么不同。“跟他自己真正要表达的东西没有关系了,在他的新歌里他要说的话,已经没有人要听。”盛志民说。
崔健多年来独自为“真唱”摇旗呐喊,正是为歌者身后的乐手争取权利,但市场始终钟情廉价的伴奏带方式。这位“中国摇滚乐教父”很清楚,市场并不那么需要摇滚乐。“摇滚乐的审美根本就不被接受,批判在中国的历史里边就不是美。”崔健说,“这是几百亿中国人——不是一代人,一代领导——几百亿中国人的文化思维方式。”
乐评人金兆钧在1993年就说过:“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极端的浪漫主义,不是现实的批判的摇滚精神。为什么呢?中国人刚刚开始挣钱。如果中国没有大的变化,老百姓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先追求钱。追求钱的过程中,人们不会过分的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松和享受。”这个刚刚开始挣钱的时期显然很长,远未结束。
在北京一个汽车交易市场,小珂的父母开了一间汽车用品店,安静地过着两个人的日子。一个短暂的、不平静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他们经历过巨大的磨难,但像很多人一样,从他们平淡的脸上,你什么也看不出来。
影片的最后一个受访者——在北京排练场打工的17岁小孩面对镜头,语言中充满了各种商业的词汇,合约,宣传,彩铃,版权,独家。他似乎已经适应了目前的商业环境,回到熟悉的家乡,他跟儿时的伙伴一起来到秘密场所,抱着吉他,充满虔诚地用粤语合唱了Beyond的《真的爱你》,他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强调: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做更主流的东西。
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发自北京
网友评论
相关链接
- Metallica将以“黑色专辑”阵容登上摇滚名人堂 2009-04-02 14:17
- Metallica新老贝斯手一同亮相摇滚名人堂(图) 2009-04-02 13:37
- 英国摇滚乐队绿洲首尔办演唱会连唱30首(组图) 2009-04-02 12:12
- “瘦人”登场!老牌摇滚劲旅加盟草莓音乐节 2009-04-01 16:06
- RADWIMPS放开躯壳 让摇滚曲肆意飘渺(图) 2009-04-01 12:13
- 宝黛揭秘:另类黛玉喜欢听摇滚 2009-03-31 02:19
- 独家:摇滚乐队X JAPAN队长谈访四川灾区(图) 2009-03-30 22:23
- 摇滚频道每周新碟碟报(3.16-3.29) 2009-03-30 17:57
- 左右乐队上演爱英伦爱摇滚不插电专场(图) 2009-03-30 16:47
- 摇滚新贵左右乐队09专场: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2009-03-30 16:08
- 龙宽摇滚品冠受不了 遗憾暂别《节节高声》(图) 2009-03-30 1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