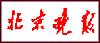音乐产业生存越来越难 养得活别人却养不活自己

在昨天,光线传媒举办的“挺音乐”反哺歌坛发布会上,音乐人、音乐公司再次将这一场所当做表现不满、发泄悲观情绪乃至绝望、愤怒感的窗口。目前,流行乐坛的低迷情绪非常强,大家普遍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音乐人、音乐公司感觉在各项制度上,特别是版权保护上受到了冷落,处于一种绝对不公正、绝对弱势的地位。现在不仅仍然缺乏资金维持,连表面上的风光,拥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也不复存在。而这一切还发生在不断有版权保护政策出台的大背景之下。
事实上,一家唱片公司可以从一张唱片中获得批发价的20%至30%的版税,词曲作者获得5%至7%的版权,唱片公司与词曲创作者还可以从公共场所音乐播放费中获利,这一范围包括出于商业目的在公共场所播放音乐的如电视台、广播电台、酒吧、商场等等。在演出中,词曲作者也应该得到版税收入。此外,在出版乐谱书籍,在广告、电影中使用音乐也要支付版税。在新技术领域,出现了网络、手机下载音乐的模式,比如,苹果模式、中国移动的模式。在亚洲地区,还有卡拉OK、KTV消费市场,也会为唱片公司与词曲作者带来版税收益。
按理说,这些政策与法律不会使音乐生产最重要的唱片公司、音乐人处于目前这样的辛酸、贫困状态。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从中受到真正的保护,也没有从版税中真正分到多少钱。
比如说,KTV收费领域,唱片公司曾寄予厚望,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有上百亿收益的版税来源,但结果却是极度的失望。在钱柜上缴1000万的KTV版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分配比例:由文化部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权管理协会(音集协)授权收费的天合公司一家就拿走50%的管理费,音著协再拿20%,音集协再扣除10%作为管理费,真正分给唱片公司的就只有20%,20%也就只剩下200万元。最终除去国际四大公司,一些民营大公司就只能分到少得可怜的版税。比如,大国唱片的姚谦称1年公司只得3000元收益,只是台湾收入的千分之一,而大陆KTV市场比台湾大100倍。拥有李宇春、朴树、郑钧、田震、老狼等众多音乐版权的太合麦田,只从中收入1000元,最后,公司拒签了这批版税。这样的分配以及这种分配结果,不但让唱片公司心寒,更让他们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有文章称音集协是强制性音乐高利贷主义者,有律师认为应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高晓松自嘲地说,在自己100%的版税中,真正能收到的只有21%,就好像警察帮你抓小偷,最终只把21%交给你,其他就是出警费一样,我肯定还得感谢。
比如说,中国移动的手机音乐业务能带来每年200亿的收益,但只有20亿拿来分配,而这20亿是由中间商与唱片公司按5比5分成,但实际分到整个唱片业的也只有2至3亿元。
再比如,百度的流量20%以上来自音乐,但每年给唱片公司的钱少得可怜,百度成为整个唱片业的头号公敌。但在整个唱片业以及单一唱片公司的法律诉讼中,百度一直是胜者。
在这个月,徐沛东、谷建芬都透露,电视、广播免费播放音乐的时代年底就要结束了。在目前,在广播中播放音乐,广播电台不但不向唱片公司、音乐人支付费用,近几年反而向唱片公司索要大量广告费或打歌费。就在这一利好消息公布之后,唱片业又在担心,因为,又将成立一个收费机构,收费的不透明、管理费的比例,最终的效果仍然不能令他们乐观。
在内地的文化产业中,电影产业,电视剧产业都已大大领先于港台,但是在流行音乐领域却是非常的低迷。一切应该使市场、行业利好的因素,最终却导致别人发财,而行业萧条的局面。高晓松就说,音乐行业养活了数百万的卡拉OK从业人员、互联网工作人员,养活了不少行业,但最终却养活不了自己。而另一些唱片公司更悲观,也更失望地表示,唱片公司、音乐人一直在吃残汤剩饭。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不但不被重视、参与其中,甚至在政策中都不是被考虑的对象。就像各项版税的收取,最后有利于版权方,还是为自己分肥很难说。
目前,唱片业的音乐人大多处于一种为生存而做音乐的无奈状态。比如,音乐人郭亮就表示他很忙,但大多数工作是为电视剧写音乐。李泉公司的经理也表示,现在还想用好乐手,做好唱片的人越来越少。高晓松认为,由于生计问题,不少音乐不是在雕刻美玉,而是在精雕鹅卵石。
现在,大家都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就如同何勇《垃圾物》中绝望、愤怒地呐喊“到底有没有希望,到底有没有希望”。光线传媒的王长田、太合麦田的宋柯都一直希望整个唱片业团结,以一个团结的行业协会的方式去争取权益。宋柯认为,组成行业协会是维护行业权益的通行做法。王长田也介绍了他们在电视领域建立协会,与电视台进行维权谈判,与广电领导部门沟通,伸张自己权益的做法。王长田还表示,他将第一个表示支持电视、广播付费使用音乐的政策。同时,将与新浪推出一个“反哺歌坛”的计划。王长田也表示,他希望所有在音乐中获利的行业都参加反哺歌坛的行动。
本报记者 戴方 D073
高晓松:音乐行业养活了数百万的卡拉OK从业人员、互联网工作人员,养活了不少行业,但最终却养活不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