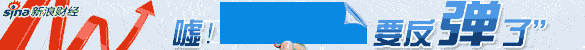乡愁,最美丽的民谣在回家

林生祥和罗思容
文/马世芳
林生祥
4届台湾金曲奖得主。1998年,客家青年林生祥开始思考音乐的社会文化意义,而后决定返回家乡高雄美浓镇,组成“交工乐队”,加入著名的美浓反水库运动,这是他其后音乐生命历程的重要起点。10年来,林生祥融合了客家山歌、八音、歌仔戏、恒春民歌、西方摇滚、非洲节奏,乃至冲绳三弦音乐的曲风为华语世界积累了全新的流行音乐创作经验。事实上,真正的重要性在于,林生祥和他固定的作词人钟永丰将社会议题与民谣音乐进行了完美结合。
罗思容
她的音乐同样是一个奇迹。40岁之后才开始音乐创作的罗思容是台湾乐坛少见的具有独特创作气质的女性唱作人,也是诗人、画家。她从客家话独特的语境中寻找富于文学性与音乐性的创作语汇,也以直觉、素朴的性灵为本,创作歌词充满丰富的灵思、童趣。正如台湾乐评人马世芳所说“听思容唱歌,彷佛目睹一树晚开的香花缓缓绽放。”
卑南族歌手陈建年曾经是这么唱的:
乡愁,不是在别后才涌起的吗?
而我依旧踏在故乡的土地上,
心绪,为何无端地翻腾?
他的乡愁,来自父亲的叹息:这片地,原本是我们的啊。于是,乡愁不再来自地理的距离,而是心理的距离了。
我也有我的乡愁,尽管我也依旧踏在故乡的土地上。我是台北人,在这座城里出生、上学、工作、成家。然而,对于这座城,我总缺少一分唤它“故乡”的情感——所谓“故乡”,理该是一处腹地更深邃、南风更熨贴、天空更高远、水色更温润的所在,不是么?
然而,在林生祥和罗思容的歌里,我看见了那既远且近的故乡。尽管我一句客家话也不会说,尽管我从来没有去过美浓:
细妹你看,那中央的大山
搅着白云翻来又转
细妹你看哪!那转弯的河流
驱赶大水波光潋滟
细妹你看,那挂云的大山
倾身顾着山下的石岗田
细妹你看,那唱歌的河流
弯腰抱着身边的沙埔地.....。
──《细妹你看》
词:林生祥、钟永丰/曲:林生祥
“回家”,多么简单的愿望,多么遥远的路程。这趟“精神归乡”的旅途,上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染上了恒春老歌手陈达苍凉辽远的《思想起》。李双泽为《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谱出美丽的旋律,男孩女孩纷纷离开故乡涌向城市,罗大佑痛切地呼喊《台北不是我的家》,群众运动四起,客家乡亲走上街头,替国父遗像蒙上口罩,高喊“还我母语”。唢呐凄厉的号音从《亚细亚的孤儿》吹到《一无所有》再转进《菊花夜行军》,孩子的啼哭,拖拉机的低吼,吉他清脆的拨弹……透过这些,慢慢地我们重新把“故乡”端详清楚:它的美丽,它的丑恶,它的无奈,它的愤怒。然后我们才能分辨,回家的路指往哪个方向。
罗思容年过四十才开始写歌,大器晚成,厚积而薄发,于是可以委婉,可以温暖。听她歌唱,彷佛目睹一树晚开的香花缓缓绽放。她的歌,则是寻常生活积年累月迭压的岩层深处,一缕熠熠发光的矿脉。多少生命中的风雨和伤痕,都低眉敛目收拢了进去。它们有时温馨,有时淘气,有时带着淡淡的伤感,满载着故事的线索,总会让我们对那些欲言又止的部份浮想联翩:
每日清晨,明亮的曙光斜斜的透出来
不知怎么,我的身体找不到世界的出口
我彷徨找不到自己,啊,这是什么世界.....。
看看我的女儿,香香甜甜的沉睡
才发现,恬静的世界是那么庄严
屋旁的橘子花,甜蜜的香味
我的内心突然起了变化
像一个孩子,每日做着奇妙的梦.....。
——《每日》,罗思容词曲
思容的歌,来自朴素的生活,直观的感受。观照世情,则既有母亲的宽容,也有女性的渴欲。这坦诚的眼神,在台湾创作音乐的历史上,竟不多见,在客语创作者之中,更是凤毛麟角。看思容演唱,貌似淡定,其实有的是压抑与克制。偶尔,歌唱进入状态的时候,她会放开身体摇摆轻舞,像母系的族长,像部落里的巫——《每日》专辑这些歌,援引了大量的草根蓝调元素,不正带着巫的味道?静水流深,波光粼粼,这小小的晃动,尚不致搅浊了如镜的心影:
妈妈跟随月光在跳舞
妈妈晃动的影子也在跳舞
妈妈的手不停地摆动
我的身体也跟随妈妈翩翩起舞
两个人的身体,两个人的手
变成四个身体,八只手
啊,哪有妈妈不爱跳舞
啊,哪有女儿不跟随跳舞?
我的女儿看我们快乐的跳舞
她也一直挥手
就像一只蝴蝶,飞到花园去
飞到月光下休憩
妈妈妈妈快快来,我们也来飞翔啊
女儿女儿快快来,我们也来跳舞啊
三个人的身体,三个人的手
变成六个身体,十二只手.....。
——《跟随妈妈跳舞》,罗思容词曲
林生祥的世界,则是另一种色调。在生祥的歌里,我们常常会遇见那个近乡情怯的青年:有时候他叫秀仔,是决意返乡“蹲点”的知青,有时候他叫阿成,在城里混不下去,遮遮掩掩退回老家务农,卷土重来。有时候他叫古锥仔,在都会的底层飘浪,想着哪天兄弟我也来干一则头条新闻。生祥早年的作品多半激切而悲壮,近年则渐渐松缓下来,底气仍足,那自苦的焦虑,却终于可以放下了。
我记得第一次听《我等就来唱山歌》的那个下午。那是1999年,天气很热,我拿着初版那张装帧设计充满“业余味道”的CD,其实并不特别期待什么。然而按下播放键,第一首歌才唱到一半,我已热泪盈眶。那是生祥在“交工乐队”的第一张专辑,我们这一辈的孩子,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史诗。2001年,《菊花夜行军》出版。拿到专辑的午后,我坐在床缘,一动不动听完整张专辑,然后再听一次,然后再听一次。那年“交工”在台大活动中心礼堂演出,全场爆满。我挤在最后一排,激动地想:若我还是大学生,这场演出应该会是改变我一生的“启蒙时刻”吧。当下我很确定,台湾再也没有能够超越他们的摇滚乐队。
然而“交工”竟解散了,传说中的第三张专辑并没有做完。有幸听到几首半成品,洗炼、大气,好听得令人颤抖。直到现在,我仍偶尔痴想那些未完成的歌,不知可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交工”不再,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失魂落魄的乐迷尚未缓过气来,生祥已经组了新团,做出“后交工时代”的第一张专辑《临暗》(2004),然后是彻底回归原音乐器的《种树》(2006)。其他的“交工”哥们儿改组“好客乐队”,发表了《好客戏》(2005)。在“交工”巨大的阴影下,他们各自拓出了截然不同的路线。当我们还在一心凭吊过去,他们已经奋力写下新的历史。
我和生祥同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还不满三十,血液里依稀残留青春时代的烟硝气味。我们认识得晚,却拥有许多共同的回忆:台湾解除戒严那年,我们高二,正是开窍的年纪。待到进了大学,遂各自一头撞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后解严时代”。那几年的记忆,饱含着鲜莽躁动的朝气,是喂养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土壤。
生祥1990年代初便在淡江大学组了“观子音乐坑”,是“交工”的前身。从“观子”到“交工”,就音乐形式来说,是从传统的“四件式”摇滚乐队发展到结合民乐编制的实验。“交工”的鼓组是客家八音鼓和传统爵士鼓的混血,唢呐、月琴、木吉他、电贝斯并驾齐驱,这样的混成编制几无前例可循,每样乐器的旋律线条和音频区段都必须仔细安排,才不至于格。他们从头摸索,建构出属于自己的音场和编曲概念。在现场演出的条件犹然简陋的时代,他们对乐器的收音、内外场音响的调校、乃至于节目的行进,每个环节都做过缜密周到的安排,这使“交工”的演出得以维持极高的水准,放在当时的独立音乐圈,简直是鹤立鸡群。
这种“穷而后工”的“手艺人”精神,延伸到生祥单飞的时代,即使单就录音、制作论之,也替台湾创作音乐树立了可敬的典范。从“交工”时代到《临暗》和《种树》,生祥的编制愈来愈简单。先是拿掉了打击乐器,继而索性只留两把木吉他和一支冲绳三弦。然而尽管编制不断“瘦下去”,音乐却跨着大步前进,不断翻出新境界。和日本吉他手大竹研的合作,不仅让生祥重新认识了木吉他的种种可能,也让他“重新归零”来思考节奏、旋律、和弦这些基本元素。
“交工”时代的生祥多是明火的镬气,到《临暗》和《种树》,则学会了用“减法”思考。如今,他和大竹研在舞台上只用两柄吉他,便能拨弹出一整个世界。信手拈来,清风徐徐,旋律像稻浪翻飞,每个音符都饶富深义。
思容的世界,或许可以视为“私领域”的诗歌,生祥的世界,则承继了“交工”时代对社运、农民与工人的关注,只是笔法不一样了。长期和生祥合作的“笔手”钟永丰,白天是政务官,晚上闭门写诗,骨子里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左派。他和生祥的合作,成色之完熟细腻,放眼近二十年的创作乐坛,或许只有陈明章和陈明瑜的词曲搭档足堪媲美。生祥曾经和我说:从《临暗》到《种树》,他和永丰反复辩诘,希望能用更精简的篇幅、更凝炼的语言,换取更宽阔的音乐空间。几经磨合,我们
乃有了这样精彩的歌词:
种给离乡的人
种给太宽的路面
种给归不得的心情
种给留乡的人
种给落难的童年
种给出不去的心情
种给虫儿逃命
种给鸟儿歇夜
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
种给河流乘凉
种给雨水歇脚
种给南风吹来唱山歌...。
——《种树》,林生祥曲、钟永丰词
若你问我,过去一年台湾最值得注意的“乐坛新人”是谁,我会说,罗思容。《每日》是一张慢火细熬的精品,假如这才只是这位女子音乐事业的起点,不妨想像她接下来的作品,可以有多精彩。这株晚开的花树,才初初绽放出她深邃的香气呢......。
然后若你问我,当今台湾最重要的创作歌手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林生祥。这要是让生祥听到,他一定会急急摇手,赧然微笑,极不好意思地要我千万别这么说。他或许还会说,自己还差得很远等等。这都不要紧,愈是了不起的创作者,原本就愈容易苛待自己。我只想说,能够亲眼目睹他一次次跨过自己设下的高标,能够和他共处在这个时代见证这一切,我着实以此为荣。
听说生祥和思容将在内地举办一系列小型演出,仅以此文向他们致意。他们的现场演出,或许仍可以是改变你的生命的“启蒙时刻”,愿我也能在场。
(载于《城市画报》08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