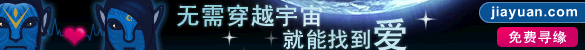周立波余隆:以娱乐的方式拯救“严肃的”音乐
那天,周立波和余隆两位黑西装“上海型男”站在中山音乐堂,每人手里捏着一根指挥棒,背靠背表情故作严肃地向京城媒体摆着娱乐的pose。第二天,京城所有的媒体都以这张合影娱乐大众。对于我来讲,在舞台上的一支交响乐团只能有一根指挥棒,如果有两根的话,无论从它们的长度、粗细、造型上看,都更像是毛衣针。两个中年“上海型男”在北京,能否如毛线女的两只操针手那样引线穿花,幻化西洋古典音乐的“严肃”为“神奇”?或者一个大都没见过的什么东西?用周立波“改变人们的固有的音乐观念”,这多少透露出余隆为困境中的古典音乐寻找“新大陆”的用心良苦。
还记得那年恰逢乐圣莫扎特诞辰250周年,三位小丫头片子蹦蹦跳跳用中文唱着《我不想长大》,一时间,华语世界人人在唱“我不想长大”,但却鲜有人知那竟然是莫扎特第40交响曲的第一个旋律,其实,二百多年前它就是流行曲,那时,人人过耳会唱。250岁的莫扎特仿佛像是跟我们这个世界开着玩笑,变身SHE,降临人间,以“娱乐的”方式拯救“严肃的”音乐。蓦然间人们发现,其实这音乐一点儿都不“古老”,更不“严肃”,仿佛那天周立波说的一模一样。
近来,余隆和他的中国爱乐开始对“娱乐”情有独钟,在周立波首次进京的前一周,他还要“以娱乐的心态”做一台维也纳轻歌剧《风流寡妇》的中文对白版,因为在维也纳,轻歌剧一点儿都不严肃,它就像是歌剧舞台上的二人转,载歌载舞,还要人人碎嘴唠叨会耍贫嘴,说白了就是今天的娱乐搞笑剧。只不过编剧、作曲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所以百年后的今天依然经典。此次,余隆以上海歌剧院歌剧“专业”科班,用中文“耍宝娱乐”,也可以理解为追根溯源,而并非真的标新立异……
一向以古典音乐至尊至上的余隆仿佛“大彻大悟”,开始了以“娱乐的精神”面对古典音乐,周立波和《风流寡妇》可以说是一次美妙而又有趣的新尝试。我们常常给古典音乐套上“严肃”的枷锁而不自知,其实是一种无知。所以,“解放”了观众的同时也就“解放”了自己。反之亦然。或许真能如中国爱乐副团长李南所说,“开辟古典音乐新模式”何乐而不为!诚如《国际歌》所唱“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李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