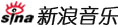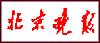|
|
北京“穷摇一代”生存状况采访(组图)
痛仰乐队2006年巡演的海报照片
痛仰乐队全国巡演现场

痛仰乐队2006年EP专辑封面。哪吒自刎。

痛仰乐队新专辑封面。哪吒已经没有愤懑,双手合十,状态平和。
北京的摇滚演出已形成规模,不仅每周都有,而且好演出时常“撞车”。北京原创音乐市场也因此成为全国中心。而且相比文化产业中的流行歌曲部分,原创摇滚更加受到国外观众、媒体、品牌的关注。惠普、摩托罗拉、李维斯、麦克塞尔等品牌对北京音乐节、乐队大赛等的长期赞助就是例证。但在这种“越来越火”的形势下,并不是所有参与其中的音乐人都安枕无忧。甚至,他们与几年前一样仍然在“穷摇”。
这次之所以重点介绍“痛仰(blog)”乐队,是因为他们在新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音乐形式从激烈、暴戾的“重型说唱”变为旋律优美的吟唱。歌词也从充满批判、煽动性的口号内容变为反映自省和个人思考。比如,之前他们吼的是“不用相信规矩!不用相信贵贱!不用相信权威!(《不》)”;现在唱的却是“再也没有流恋的斜阳,再也没有倒映的月亮(《西湖》)。”之前他们吼的是“质问你懦弱的源泉,你的热血哪去了!(《这是个问题》)”;现在唱的却是“华丽的外衣全部都会褪去,但请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因为这些,他们一方面被部分老歌迷斥为“像许巍(听歌)那样投降了”,另一方面他们被新的流行听众接受。甚至,他们诗情画意的新歌《西湖》作为电台主推流行曲被反复播放。媒体普遍认为,如果运作成功,“痛仰”将继许巍、汪峰(听歌 blog)、谢天笑(听歌 blog)之后成为又一个将影响力从摇滚圈扩大到主流领域的艺人。
“穷摇一代”遭遇“跑车一代”
“痛仰”和“左右”是当前北京摇滚圈里广义“新金属”风格的代表。虽然更多的听众会觉得他们还是“新人”,但实际上他们已分别成立10年和4年——“痛仰”的成员多是“70后”,“左右”乐队则是“85后”。
“痛仰”与谢天笑、苏阳、新裤子(听歌)等同属于内地第三代摇滚人(第一代崔健(听歌)等;第二代唐朝(听歌)、黑豹(听歌)、张楚(听歌)、何勇(听歌)等)。“左右”们则是视“痛仰”为前辈、偶像的最新一代乐队。
10月25日,两支乐队凑巧同时举行新专辑上市的演出。演出结束时,地铁已经停运。“痛仰”乐队的主唱高虎似乎不愿支出从星光现场“打的”回通州暂住地的这笔花销,最后他搭朋友的顺风车回了家——事实上他对这套房子的租住能力也近枯竭。高虎已经决定11月中旬就退租,然后去云南“避难”——云南的生活消费要比北京低很多。而在这场演出前,从1999年成立就一直陪伴高虎的同乡、乐队元老、贝司手张静突然离队,宣称要换另外一种生活。据一位乐队友人说,张静做乐队以来一直没有找工作,如今年过三十,没有结婚。家庭、社会各种压力可想而知。“他热爱的摇滚并没有为他带来基本生活保障,这可能是他突然离队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左右”乐队的散场情景则又酷又帅。这支6人乐队中有5位都拥有自己的汽车。除了马自达3、福特福克斯、大众高尔改装版等车型外,乐队主唱张顾卫的车最“拉风”——他的三菱EVO-9型跑车当晚停在MAO门口吸引了所有路人的关注。而张顾卫的梦想就是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兰博基尼’跑车的摇滚人”。
“痛仰”作为“穷摇一代”似乎有些命运弄人。他们视唐朝等乐队为偶像,并被1994年前后国内摇滚大好形势影响。但到他们成立乐队的1999年前后,国内摇滚商业气候已由盛而衰。1998年“树村”开始聚集地下摇滚乐手。到2003年拆迁前,“痛仰”、“夜叉”、“病蛹”等在此“穷摇”、“死磕”的乐队渐成新一代摇滚偶像。此后,“痛仰”们驻进新的“摇滚村”霍营,继续“穷摇”。直到2007年底霍营改造,众乐队迁走。而2004年之后,独立电影逐一浮出水面,获得了资本青睐;现代艺术也通过海外资金开始红日当头;只有地下摇滚“死”得悄无声息。2008年,中国摇滚迎来了新的变革,像“左右”、“刺猬”、“Carsick Cars”、“卡奇社(听歌)”这样的“85后”、“90后”乐队突然崛起(从乐队名字就可以看出两代人的不同状态),受众开始具有消费能力并往年轻化倾斜。而“痛仰”们依然没有工作,继续无法从音乐事业中得到生活保证,搞到乐手退出、主唱“下乡”。
对话高虎:再也不想向亲朋求援度日
对于旋律,其实是我很早就想要的。我们之间出的两张唱片,我的家里人都是不听的。我希望有一天他们和更多的人都能听一听,让摇滚圈外的人也能接受我的音乐。以前我做音乐很追求“最新的”、“跟世界同步的”,忽略了音乐表层下的东西。我们第一张专辑内容很愤怒,但那是我之前10年生活的总结,我在最需要表达的时候表达过了,就足矣了。我不想让这总结像商标一样贴在我身上,不希望它一直延续,我需要表达最新的我。其实我知道听众都喜欢《不》那样的歌,刺激。而我做这种歌也很快,可以做上一批。但我只希望每个时期都尊重自己内心最想表达的内容(记者注:这句话与许巍对“新专辑没有改变”的回答几乎一样)。
2006年我们进行了一次全国巡演,游历了50多个城市。这次巡演和2007年我一个人去旅行对新专辑的改变影响很大。去年,我一个人去了新疆、西藏、尼泊尔、云南。在新疆的时候我跟一些玩音乐的朋友聚在一起。饭桌上每个人都弹唱一首歌。轮到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特别难受,虽然我会唱很多歌,但那些都不是我最想要的心里的表达。这让我对新的创作有了方向的改变。后来去新疆英吉莎水库,我跟朋友露宿。在北京的时候我总觉得我不敢放开声音大喊大叫,怕周围人对我有看法。我以为来到水库就可以喊出来,但没有,我发现我内心还是封闭着。然后我走新藏线,搭了一辆油罐车去西藏,颠簸了3天4夜。途中只有无尽的山、无尽的夜,走一二百公里才能见到一辆车,还遇到了我永生难忘的沙暴。虽然辛苦,但我在北京时的浮躁、喧嚣已经没有了,心已经沉淀下来了。又走尼泊尔到云南,我开始明白其实喊不喊得出来其实不重要,唱歌不是音量的问题。
后来我们回到北京。在2008年的大年三十,我一个人待在北京的房子里,窗外都是烟花,我抱着吉他、翻着几十本几年来记录的素材,开始创作这张新专辑的歌曲。
对于新歌,其实莱昂纳多·科恩、鲍勃·马利对我的影响很大。在中国做摇滚乐,只有第一批“老炮儿”的生活能实现自给自足。之后的绝大多数还是“穷摇”。这个状态本身就很容易让乐队的作品充满绝望、无奈、愤怒。但这不代表这就是摇滚乐的全部。在我迷茫的十字路口,绝望的时候,不是金属、朋克,而是鲍勃·马利那样的音乐给了我力量,让我觉得人生有意义。所以我也希望能带给别人温暖、向上的东西。
说到生活状态,我们圈很多人都会很惭愧。比如我从开始做乐队到今天,一直都是在靠朋友、家人的接济。音乐不能养活自己,生活中又有太多窘境要去面对,而且这个现实短期内还改变不了。所以我马上就要在北京呆不下去了。我告诉自己再也不能向亲戚朋友去张口要了。所以我要去云南,借机安静安静,整理一下我的新歌。真正的光亮还是需要自己内心去点燃的。我觉得我有幸选择了摇滚的生活,我内心有很多东西要去表达,还有很多很好的旋律在我脑海中,我还要把它们都唱出来呢!
本报记者 刘颖文图J188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相关专题:痛苦的信仰《不要停止我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