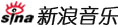|
|
艾敬:从音乐到艺术的跨界旅途(组图)

艾敬 歌手,艺术家,1969年生于沈阳。作品有音乐专辑《我的1997》、《艳粉街的故事》、《追月》、《Made in China》、《是不是梦》、《艾在旅途》等。现往返纽约、北京两地,从事艺术创作
画板、颜料,以及堆积如山的木盒子……艾敬在北京的工作室,已经几乎看不到和音乐有关的什么东西。除了一张小小的CD。封面用的当然是今年最流行的中国红,隐隐有一行字写着:2008年8月8日晚8:00。
那个时刻,举国欢腾,艾敬也满心欢喜。2008年,她觉得一定要回国做点什么,于是从纽约飞回北京,在飞机上就写完了新歌《我的2008》:“乘着一阵风,带着我的梦想,接近我的目标,去努力得到它。”然而伟大时刻到来的夜晚,她却又去了日本东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解释不了。”
那一刻,心里感受如何?
“落寞。”艾敬答。“我更希望在中国的电视台做节目,和中国的直播一起见证历史。”
有区别吗?有。“我这么爱国,其实我还是很边缘。”她微笑着说。
很多人记忆里的艾敬,还是那个穿着宽大的男式外套,抱着木吉他边弹边唱的姑娘。1992年阳光灿烂,她长发飘飘,唱歌如同街坊聊天般絮絮叨叨:“我从北京唱到了上海滩,也从上海唱到曾经向往的南方。我留在广州的日子比较长,因为我的那个他在香港……”这段影像朴素干净,如同日记本里不经意掉落出来的花瓣,还留着当年风干时的形状。《我的1997》MV是张元( blog)执导的,1992年10月在央视“十二演播室”栏目里首播,迅速流行,基本成了当时的唱片公司和歌手们拍MV的范本。翌年同名专辑上市,1个月时间就卖到了20万张,而且在日本还有3万张的不俗成绩。制作这张专辑的幕后班底,有三宝、何勇(听歌)、陈劲、臧天朔、刘效松、黄小茂、王迪、艾迪、王勇……这份名单,即使搁在今天的华语流行乐坛来看,也称得上顶级阵容。
blog)执导的,1992年10月在央视“十二演播室”栏目里首播,迅速流行,基本成了当时的唱片公司和歌手们拍MV的范本。翌年同名专辑上市,1个月时间就卖到了20万张,而且在日本还有3万张的不俗成绩。制作这张专辑的幕后班底,有三宝、何勇(听歌)、陈劲、臧天朔、刘效松、黄小茂、王迪、艾迪、王勇……这份名单,即使搁在今天的华语流行乐坛来看,也称得上顶级阵容。
《我的1997》是艾敬自己作词作曲的第一首歌,写歌的时候,她只是来中央戏剧学院大专班进修表演的学生,无数“北漂”中的一员。一切都如歌中所写,这个姑娘17岁就离家闯荡,“凭着一副能唱歌的喉咙,生活过得不是那么紧张。”她向往着八佰伴的衣服,向往红磡体育馆和午夜场,向往着花花世界的香港,直到有一天真的“给我盖上大红章”。
【艾敬说】
以前我喜欢香港歌,但是不会粤语,只能自己写词。为什么要写1997这个题材,可能是骨子里觉得1997是大家的事,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跟我自己也有关系。我听过美国民谣歌手苏珊娜·薇格的一张唱片,其中有首歌叫《My name is Luka(我的名字叫卢卡)》。她就唱道我的名字叫卢卡,我住在二楼,如果你经常听到我的家里有吵闹的声音,不要觉得很怪异……就是这种叙事性的歌词。我就想,她写的这些事多小啊,我也可以说我的名字叫艾敬,我从沈阳出来,我去过北京,现在想去香港。我的经历比她丰富多了,也可以写首歌。
写完了以后,我找了很多人作曲,他们都说你这个不是歌词,简直是诗歌,数下来一行能有13个字。专辑的编曲王迪鼓励我,说这首歌你应该自己写,别人写不了。
我第一张专辑合作的音乐人,已经是当时北京最有名的了,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他们能来给我帮忙。臧天朔帮我弹琴,王迪帮我编曲,还有打鼓的三儿、刘效松,都是崔健(听歌)乐队里的,艾迪、何勇也来帮我。因为当时有能力录音的人就不多,下决心做到最好的更少,在北京做音乐的这些人,你一张专辑如果没想法,他们肯定不会来。黄小茂就觉得,他的想法可以在我的专辑里实现,合作就很愉快。
《我的1997》在日本很红的时候,经常有外国记者认为,这首歌里有政治隐喻,他们理解成你之所以想去香港,是认为内地不好。当然记者不会直说,他们会从别的角度拐弯去问。每当他们这样问到我,我就会说,这首歌就是一个情歌,是love song。
其实我是在为蓝领歌唱。因为香港给我的幻想和吸引,并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它的“服务”。这种服务是指城市、社区里的那么多公共设施,那么周到,那么浪漫。我们过了多少年才有午夜场的电影院啊,才有那些深夜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啊。这些设施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享受它们的人和做这些服务的人都是老百姓,都是蓝领,我关注的是这个层面。
写完这首歌,我才第一次去香港。
其实刚开始去,也不是那么喜欢。我觉得香港的噪音太大了,路很窄,楼很高,汽车的声音都被笼罩在下面,还有冷气的声音,全都冲到街上。这种噪音让我似曾相识,像小时候父亲的工厂,有点找不着北。我吓坏了,我以为香港应该是很静的状态。我对声音很敏感,第二敏感的就是光,就是色彩。那时候香港还不是柏油马路,是石子、水泥,一块一块的白色,很刺眼。声音和光的刺激,太炫了,让我眩晕,好像踩到珍珠上,怪不得是“东方之珠”。
等我从眩晕中回过神来,看清它的时候,我对香港的感受就更深了。我比以前更喜欢香港,比方说巴士特别好,地铁特别好,还有吃的东西特别好。鱼蛋粉,那个时候9块钱,现在20多块。我亲眼见到清早起来串鱼蛋粉的人,他们低着头,不看周围的世界,只专心打理他的小食档。还有一次我去拍MV,凌晨4点钟,看到报摊的阿婆,已经拿着新鲜的报纸在分类。你说一碗鱼蛋粉、一张报纸能有多少利润?可是他们很敬业,很努力地打拼。为香港的美丽,付出最多的就是他们。
艾敬在歌里写过,童年的记忆是沈阳一个叫做艳粉街的地方,那里没有漂亮的儿童车,只有一起玩“跳方格”的小伙伴,和永远忙碌沉默的大人们。“我最爱五分钱的糖果,我们姊妹三个是爸和妈的欢乐,尽管我家里没有一个存折。”她还记得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大哥哥,被街道大妈押着游街,“他的裤子已被撕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
所以艾敬童年最奢侈的梦想,就是“四个现代化”。六七岁时小艾敬就在纸上画冰箱、电视机,听大人们说,这些东西会在2000年变成现实。
【艾敬说】
我母亲是满族,可能我血统里就有不安分的因素,从小幻想着更大的舞台。上小学时我是全校文艺最突出的学生,参加唱歌比赛拿了很多奖状,我就觉得沈阳这个舞台已经没什么了,也许我应该站在北京的舞台上,向全国人民唱歌。
我就离开家了。初中毕业读艺校,学美声,老师想培养我做抒情女高音。可是我没有读完,我喜欢流行音乐。传统的唱法,一首歌要练半年,感觉都磨没了。而且我理解不了的是,为什么要学意大利文?意大利的文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象不出那种华丽的宫廷生活。能打动我的音乐,就是美国的country music(乡村音乐),那才接近我的生活。
于是我到北京,考上了王昆老师的东方歌舞团。经过了5次考试呢,最后一次我唱的是《小白菜》,还唱了《信天游》,我对自己的声音有自信,觉得王昆老师会喜欢。
我在东方歌舞团待了一段时间,忽然又觉得,怎么北京的团和沈阳的团都是一样的啊?因为都是一个体制嘛,有团长管着,经过考核才能有机会演出。于是我就开始干很多私活儿,所谓的“私活儿”就是出去录音。比如最有名的一个私活儿,是甲丁找我,录了一盘带子叫《大趋势》,卖了600多万盒,其中有首歌叫《沈阳啊,我的故乡》就是我唱的。那时候我17岁,一晚上唱了5首,甲丁说你累了吧,分两首给朱桦(blog)吧。录一首歌能挣几百块,相当于现在几千块呢。
干私活儿我不敢写自己的真名,但也不愿意改名字,就写了个“艾静”,我想我应该“静悄悄地”干私活儿。600多万盒磁带卖出去,就有人找我,要给我出专辑了。我就去广州,待了一年半,跟白天鹅、太平洋、E时代、广州中唱这些大公司都合作过,主要是翻唱港台的流行歌曲。除了录歌,居然还拍了一个电视剧《情魔》。因为导演看到我的唱片海报,觉得这女孩“长得像山口百惠( 听歌),笑起来像栗原小卷”。
听歌),笑起来像栗原小卷”。
广州的唱片工业比较正规,虽然我们是翻唱别人的歌,可是每个音符都要重新录,词曲版权也要给人家钱。对我来说,这是个锻炼的机会,翻唱了十几张专辑,也挣了不少钱。但我当时觉得很茫然,音乐道路肯定不是这样走的,我这么小就挣这么多钱,太安逸了。在中国原创音乐兴起的年代,为什么不能有我自己的专辑呢?这就是我的野心。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中戏进修期间认识了来北京的徐克导演,他建议我改回本名。我想对啊,人们应该记住的是“艾敬”。
东京-纽约 China girl的梦想
1996年,艾敬签约SONY唱片,把自己的音乐阵地全面转向日本。有一天肚子饿了,她走进东京的一家餐馆,对着满纸日文的菜单发呆。这时,女招待突然用中国话问她:“想吃点什么?”
“你会说中国话?”艾敬吃惊。
“对呀,”女孩一笑,“中国人当然会说中国话。”
艾敬就写了一首歌,《东京餐馆里的China girl》。“远方有你的妹呦你的哥呦你的自行车,那有条小胡同小河流在你家门前流过。这里有你追的梦你受的罪你是否想过,满天是星星太刺眼你想摘哪一颗。”事实上艾敬和这个餐馆女孩再无更多的交流,她只是在猜测,同样身处异国他乡,与自己并无交集的陌生人,会有怎样的生活。
【艾敬说】
《我的1997》起点太高,第二张专辑《艳粉街的故事》开始和陈升(听歌)合作,乐队是澳洲的,录音在香港。然后第三张去日本,第四张在美国,我就不在国内做音乐了,因为不可能把那些顶尖的音乐人再聚到一起,我不能重复自己,必须走出去。
第一次去纽约,我找了个房产中介,我说我需要住在中央公园旁边,你帮我找个公寓。他说你要住多久,我说三个月,他大吃一惊:“中国人来了想住三个月就走?不可思议。”我讲这个例子不能代表中国人在海外的生存状态,但是可以说明一点问题,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来纽约,就应该千方百计留下来,扎根在这里,才算合情合理。而我在任何一个环境中,都是抽离的,是一种漂流的状态,我想这恰恰像艺术家的生活。看到什么我都想写歌,纽约到处都是印着“Made in China”的东西,我就写了《Made in China》。这张专辑是个契机,让我从音乐转向艺术。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觉得艺术可以使我忘掉很多。
从1999年开始我比较认真地画画,2005年开始,待在纽约的时间比较长。每天早上起来,吃面包和咖啡,然后就去画室,一整天过去,傍晚去买菜,回家花三四个小时煮饭,这么久也不过做出两个菜。我家人说,你把做菜也当成艺术了。我有时候也会想,这有什么意义呢?人非得干活才觉得自己没白活着?艺术就是打发时间让自己感觉到存在?反正这种方式让我感到快乐。
音乐-艺术 传递中国能量
11月初,艾敬要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做一个展览,作品就是堆在她工作室里的那些方盒子。从北京奥运倒计时100天起,每天的日期数字印在盒子上,打开来,里面是当天的报纸,《纽约时报》、《南华早报》、《新京报》……艾敬觉得在国外这些年,省略掉很多情感的挣扎,对祖国的关注会更客观。“我跟徐冰聊起,为什么要回中国来。他说你看中国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更刺激,更适合做艺术。”艾敬说,“我也有同感,这一年哪怕什么都不干,也一定要回国。”
使用艺术,想表达什么?抑或说明什么?
【艾敬说】
我想表达的东西挺多。比如符号,这种抽象的东西会给人很多信息。不用说2008年8月8日8时这样的数字,谁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单是随便一个普通的日子拽出来,都会给你不同的感受。4月30日那天你在干吗?哦,可能在吃饭,也可能刚失恋呢。5月12日地震了,世界就变成了黑色。到8月8日,又变成了红色。这些符号里也有很荒诞的感觉,荒诞就在于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相信“8”,谁能告诉我,“8”就代表幸福?但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相信,你看这个8,两个圆圈在一起,很好看,像装满了宝藏的葫芦。
所以我有了很多理由,要把这些日子、这些数字留下来。也许十几亿人对“8”输入的气场,真的会产生一种能量,这一天使你感受到的讯息,在今天、在10年以后、20年以后,都会不一样,就像蔡国强在纽约上空炸开的云,太伟大了,太玄了。
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我的1997,在国家和民族面前,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是集体里面的一个小小分子。而我总要强调个人,个人没有什么不好,一滴水是最真实的。我的2008也一样,本能告诉我,你要把我这个小分子汇集,我就会汇集;你要不把我汇集,我也会表达自己。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实习生 熊寥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更多关于 艾敬 的新闻
-
艾敬:因为爱北京,所以我漂泊(图) 2008-10-14 18:15
艾敬师从张晓刚 “改行”当画家(图) 2008-10-10 04:25
艾敬唱而优则画个人画展将于下月举行 2008-10-09 17:10
艾敬:纪念《中国制造》 十周年 2008-10-08 18:25
许巍顺子艾敬18日唱响重庆大田湾 2008-10-08 10:45
许巍携手才女顺子、艾敬18日唱响重庆(图) 2008-10-08 04:55
艾敬学画10年首次办个展(图) 2008-10-08 00:00
艾敬个展将于11月初举行 首次以艺术家身份示人 2008-10-07 14:12
艾敬:我非艺术家但一直过着艺术家的生活 2008-09-01 16:37
艾敬:《功夫熊猫》的三点启示 2008-07-23 10:12
艾敬8年前拍摄短片曝光 向《功夫熊猫》致敬 2008-07-22 11:48
艾敬:每年都有拍摄的约定 我会继续美丽(图) 2008-07-01 15:00
艾敬为灾区献爱心不遗余力 绘画作品首度拍卖 2008-05-29 18:17
视频:摇滚赈灾义演 艾敬演唱《你是我的天使》 2008-05-23 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