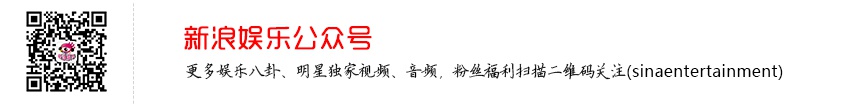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话剧舞台】
舞台上的《小城之春》运用很多画面给观众留下了淡淡的伤痛和深深的无奈,正是这种深深的无奈是对人生的一种美学上的解释,那是无法逃避的人生一景,只是在六乙导演的手下变成了人生的一种美感。
每年清明时节,只要人在上海,我会去黄佐临先生的墓前鞠躬。今年虽然不在上海,刚看完李六乙的《小城之春》的我,却可以非常高兴地告诉佐临先生,他一直梦想的“写意话剧”被六乙成功地呈现在舞台上了。
“写意话剧”是什么?
黄佐临先生是中国最早引进布莱希特的戏剧导演。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他曾经遇到的困难。在“大一统”的时代,话剧只能是“斯坦尼”一统天下,其他的学派,其他的艺术手段都被排斥之外。佐临先生推崇布莱希特,并不是要抹杀斯坦尼,而是要丰富戏剧人对戏剧作品的理解,是要打破僵化的舞台,是要从剧本和想要达到的目的出发,运用相应的艺术手段。佐临先生在奋斗的过程中,始终是孤立的,而且遭遇过莫名其妙的阻力,甚至中伤。佐临先生在推广布莱希特的同时,内心怀有一个真诚的梦想,那就是他提出的“写意话剧”。要了解“写意”是什么,看看八大山人的画就会有初步的体验,那是中国和东方特有的艺术韵味:简单的线条、纯而又纯的结构、切忌太满的美,又能赋予观者想象和思考(如今在现代舞和西方的现代美术中也出现了这些元素)。佐临先生也做过类似的实验,只是当时的大环境无法给他创造很好的条件,而且在他走后那段日子,他的许多观点完全被话剧的“多样性”所淹没。
现在的导演虽然已经没有什么阻力,艺术手段的丰富也令人刮目相看,但我始终没有忘记佐临先生的“写意话剧”,没有忘记他所追求的审美,也始终担心看不到高度的审美作品,所以看了李六乙导演的佳作《小城之春》,真的为佐临先生高兴。
“小城”追求角色最内心的过程
在我看来,一个好导演身上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高度的文学理解能力和高度的审美能力。六乙身上就完全不乏这两个先天或后天的条件。《小城之春》就是最好的证明。导演调动一切戏剧因素,让我们享受到我理解的写意话剧的本质。
从演员的表演来看,演员并不追求“我就是那个角色”的创作方式,导演通过超乎寻找意义的调度,不断地打断“此时此地”的确定性,而是追求角色最内心的过程。角色之间本应带有距离的独白变成了直接的对话,而直接的对话又会变成带有距离的独白。最奇怪的是,恰恰是这种对话造成的张力对耳朵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卢芳控制舞台的能力、她的气场在话剧舞台上非常鲜见。她在讲述、独白和对话之间的自然转换绝对是这部作品的亮点之一,这样的表演在我眼里看来,就是最好的“写意”手段,它打破了演员和角色的所谓一体,而且不会给观者有压迫感,更没有口号的痕迹,而是邀请你进去,进入她的内心。其他所有演员的表演也非常赏心悦目,特别是李云龙老师短暂的显身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个戏的调度是这部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导演可谓是游刃有余地通过调度,不断地制造空间,分割空间。舞台上很小的空间被导演这么处理会突然变得非常之大,这也是一种特别奇特的感受。当然无声的灯光语言也非常好地帮助导演制造空间。这部作品中的舞美和灯光都不单单是辅助的技术手段,而是独立的叙述部分。 舞美讲述着破坏,而灯光则暗示绝望。这也是布莱希特提倡的做法,也是黄佐临先生一直向往的呈现。
这部作品的音乐非常统一,而且几乎是中性,一点也没有煽情的意愿,这肯定给这部作品的审美添上重重的一个加号。
伤痛和无奈变成了人生的美感
几十年以前看过费穆先生的电影《小城之春》,至今还记得周玉纹的脚步、城墙、还有空气中寒冷的春风。那也是一部绝美之作。几十年了,这样的作品不会减少美感,而只会引起后人的惊叹。应该说,面对这样的经典,李六乙导演的《小城之春》应该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但他胜任了。
舞台上的《小城之春》不仅不亚于电影,而且运用很多画面给观众留下了淡淡的伤痛和深深的无奈,正是这种深深的无奈是对人生的一种美学上的解释,那是无法逃避的人生一景,只是在六乙导演的手下变成了人生的一种美感,尽管无可奈何,但依然美丽。
近年来,话剧界引进不少外国名作,我看过(参与翻译)的外国作品从审美上确实比不上《小城之春》。我想,这肯定也是西方现在开始重视东方美学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一些现代舞的编导成为西方戏剧舞台的编导就是一例。
东方艺术中的写意之美肯定是我们固有的财富,只是要挖掘这种美,必定需要很多懂得美的艺术家。这就是李六乙和他和他的团队的《小城之春》的意义,也是佐临先生毕生努力的意义。
□李健鸣(戏剧编导)
(原标题:《小城之春》美在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