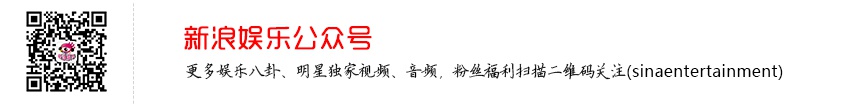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从它诞生起至今这150多年里,从来都是上演城市的一件轰动的文化事件,喜爱它的观众将其奉若至高神明,赞美热捧无以复加,不喜欢的人一场下来混混沌沌酣睡挨熬的也不在少数。在欧洲的历史上这种关于瓦格纳歌剧睡觉的故事不绝于耳,但更让人好奇的是,是什么原因人们如此喜爱追逐《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仅仅是因为那个浪漫的“爱之死”吗?为此,北京晨报记者采访了著名作曲家、中国音协主席叶小纲和著名指挥家张国勇。
叶小纲:第一个和弦预示了音乐100年的革新
北京晨报:为什么《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只要在一座城市上演就会引起轰动效应,进而成为文化现象?
叶小纲: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音乐上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音乐是革命性的,它的前奏曲的第一个和弦——“特里斯坦和弦”,已经成为了这个音乐革命的标志。《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音乐上的成功,主要还有瓦格纳创造的“调性瓦解”对音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都体现在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里面。从开始那几个和弦预示了音乐一百年后的革新。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瓦格纳音乐的“无终模式”也是导致音乐的巨大革命的动力。瓦格纳对角色内心激烈的交响澎湃导致这部戏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很高。我认为,这是中国音乐圈最在意,一定要从全国各地专程来北京现场观赏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北京晨报:对于这个大剧院版本的风格你有什么样的见解?
叶小纲:大剧院的演出我只看了第一场。这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一次在北京演舞台版,自然会引起观众的很大兴趣,但我还是觉得欧洲的文化确实是没落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音乐的革命性和强大的推动力,舞台上不应该是这种呈现方式。舞美其实是与音乐相悖的,他的音乐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火爆,但是这个舞台的颜色非常的单一,采光总是一小块在不停地变换着区域而已。台上不如台下,音乐真的是很激动人心,但舞台上的呈现并不如我对瓦格纳音乐的理解。我在拜罗伊特看过一个《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版本,也是这个问题,真的是台上不如台下。所以,我认为欧洲正在没落。他们在舞台呈现上都不具备瓦格纳那样的革命性,并没有完全与瓦格纳的音乐直接对位的吻合。
张国勇:国家大剧院终于可以自己写“大字”了
北京晨报:为什么《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只要在一座城市上演就会引起轰动效应,进而成为文化现象?
张国勇:《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是最能够体现瓦格纳的精神思想和创作技巧巅峰的标志性作品。我们过去一直都在讲他创造的“主导动机”,在瓦格纳的这部作品里,它的和声——“特里斯坦和声”都带有符号性质的,它的和声色彩直接用于描写人物的心理,这个和声是作为近代的晚期浪漫派巅峰的标志,它最能够体现瓦格纳创作的内心世界以及最能够反映瓦格纳最高超的创作技巧。所以说,这部戏一出现就一定会引起效应。
在中国的话,除了自己制作歌剧,这部歌剧的长度,对国家大剧院的演员也是一个考验,对中国的观众也是一个考验。说实话,真的还是有人睡着了,醒过来继续认真欣赏,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可贵、很可爱的事情。无论从体力上,还是心智上我们可能都接受不了四个小时的歌剧音乐,这既反映了这部作品的欣赏难度,同时也反映了坐在里面的人都是怀着崇敬的心去欣赏的,因为大家都明白瓦格纳这部歌剧在历史上的地位。这部戏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上演,都是当地的一件文化盛事,一件大事,对我们中国音乐圈也就是内行人来讲就更是一件大事。我们自己的作品没有这么长的,单场演出全程5个小时,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北京晨报:您如何看待这次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舞台版的中国首演?
张国勇:跟国家大剧院合作这么多年,所有在这里工作过的中外指挥中,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是最早一个到大剧院,并且坚持到了现在的一个指挥,大剧院歌剧从无到有的历程我都见证了。我觉得国家大剧院在制作歌剧领域已经足以媲美世界最著名的各大歌剧院,同时,这部戏的上演,它的策划一定是考虑到了听众的接受度,一定是考虑到了它的社会效应,我听说四场票都卖光了。我们引进西方先进的舞台艺术是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的,也就是写大字刚开始先要描红模子,然后才能开始自己写字,这是个过程。全中国所有的地方他们都等不得,要不就在描红模子阶段就夭折了,要不就早早“写大字”了,那个字能看吗?但是唯有国家大剧院坚持到今天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今天它终于可以自己写“大字”了!而且写的是拿得出手的“大字”。《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是我们厚积薄发的一个点。这次一票难求,首演那天我跟郭文景聊天,他说也很想去看,但是首演的票他都得不到,只能看后面的场次。郭文景应该算是大剧院最重要的作曲家和最尊贵的客人了吧,他都拿不到首演的票,因为全国各地的艺术机构、文艺院团的人都来了。国家大剧院就是全中国歌剧的领航,它的一举一动,都会蝴蝶效应引发全国的效仿,它的示范意义非常的重要。
北京晨报:对于这个现代版、诠释版大家的反应非常不一样,您如何看?
张国勇:我是一个介乎于创新和保守之间的人,如果一味地守旧,时代对我们是有要求的,你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来的样子去做吧,时代都变了,信息传播的渠道都变了,欣赏习惯也变了,我们的审美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不创新一定是不行。但假如说走得太远我也不主张。比如第一幕的那个九宫格的床舱的形式,舞台上同时多画面的出现,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东西,但是也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而且呢演员演唱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他们在一个小空间里面唱,声音是有问题的,但是到了第三幕完全打开了,声音就对了。但是你也要理解,这个制作是和波兰华沙大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德国巴登巴登歌剧院联合制作的,人家可能已经是第十五个版本了,尽管国家大剧院只是第一个版本,但也必须要考虑毕竟是联合制作吗!可以理解。
北京晨报:从一个指挥家的角度您如何看待“特里斯坦”?
张国勇:这个戏在中国,平时我们也不太可能有机会演,但是它的前奏曲和尾声也就是“爱之死”,我是演过的,它通常是连在一起在音乐会上演的,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带声乐的,一个是完全管弦乐版的。这两个版本我都演过。我个人认为,瓦格纳所有最伟大的东西就在这一头一尾的差不多17分钟内,中间三个多小时所有纠结、纠缠,有的乐句听起来还是蛮费神的。但反过来讲,这就是音乐创作的逻辑性,没有“起、承、转”,到了“合”的时候怎么会有“大同”之感呢!也许这就是瓦格纳神来之笔的妙处,中间这三个半小时的铺垫都是为了最后的“爱之死”做准备的。我相信所有的指挥都希望能够指挥这部作品。一位年轻的女高音歌唱家对我讲,“一个歌唱家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唱什么样的作品,如果过早介入普契尼或者威尔第尤其是威尔第晚期的作品,可能会毁掉自己的嗓子,所以,唱瓦格纳的歌唱家没有年轻的,都是像一棵老树,它的皮是褶皱的,但是根扎得很深,才能够枝繁叶茂。虽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唱到45岁以后,但是如果有机会那时候唱瓦格纳,艺术生涯足矣!”我觉得,瓦格纳的音乐像催眠术像巫术,它拉着你的手,你不能放开,一放开,你就会有摔倒或者掉进深渊的恐惧感,你会有一点点好奇、神秘,一点点胆怯,但是它又太有吸引力了,你会跟着它过去,不由自主……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李澄/文
记者 柴春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