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 半生是非俱终结
8月18日深夜,一代文化老人舒芜去世。这位因“胡风运动”而名噪一时的文化人,因其站在了不光彩的一列,终其一生背负着骂名。随着这个“反面角色”的离世,因“胡风运动”而纠缠其半个世纪的个人恩怨也到此为止。而作为学者、作家的舒芜,其早年对文艺理论的某些探索,晚年在古典文学、杂文写作等方面的成就,不会因历史问题而磨灭。
 |
舒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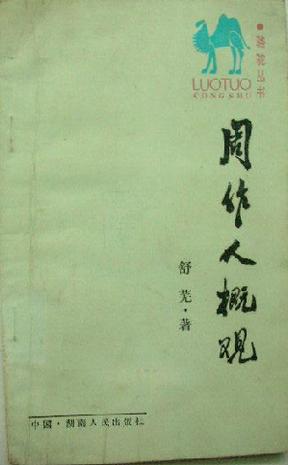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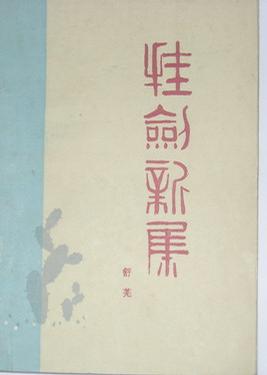 |
 |
从朋友到犹大
舒芜,1922年出生于安徽桐城,在《<回归五四>后序》中他说,父亲和祖父都是读书人,从小受到熏陶,上中学前已通读四书五经,并开始阅读哲学和新文学,然后迷恋上鲁迅、周作人,十五六岁开始,那些阅读过的进步书籍已经给少年舒芜思想上留下很深的印痕:“一、信马克思主义;二、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三、反法西斯主义;四、尤反蒋介石政权在文化上搞的法西斯主义。”
1938年,日军攻入安徽,舒芜随家人逃亡,并在逃亡途中开始发表文章,但影响不大。“这两年中,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就是1940年冬天认识了青年小说家徐嗣兴(路翎)。其所以重要,一是他介绍我到建华中学教书,二是他介绍我认识了胡风。” 舒芜曾写道。与路翎,特别是经路翎介绍认识胡风,舒芜也承认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当时,胡风已经是最具知名度的文艺理论家。
谈到与胡风的认识,舒芜说:1943年七八月间,报上刊登了胡风等作家来到重庆的消息,“路翎看了消息,非常兴奋,决定第二天请假进城去看胡风,并且要我一起去。我说我不想见名人,路翎说,‘你要这样想,那就无话可说了。’我同意去看看。”还带上了几篇文章。不过在路翎的回忆中,他写道:“由于生活的环境,我认识了舒芜,应他的要求,又将他介绍给胡风。”到底谁的记忆更为准确,也不得而知,不过重要的是,之后舒芜和胡风熟识了,也通过胡风认识了更多名人。不过胡风感觉到舒芜与其他年轻文友气质上不同,在胡风眼中,舒芜“既是书生,又是打括弧的‘实际’的人”。尽管“舒芜喜欢卖弄,善于迎合”(路莘《三十万言30年》),但胡风还是非常赏识舒芜的才学。当年胡风创办《希望》杂志时,也将舒芜的文章刊登在创刊号上。
之后几年,舒芜发表了一些小有名气的文章,南宁解放之后,舒芜任南宁高中校长,但他一直托在上海的胡风帮忙,希望调入北京或上海。1952年,他进入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为“舒芜”的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文章的编者按说: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这个“编者按”出自毛泽东。舒芜的材料将胡风问题提高到如此程度,这是许多人包括舒芜本人没想到的。舒芜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编辑室的编辑,比胡风年轻近20岁。舒芜的材料大致有三部分:从胡风给他的书信中摘取一些段落或句子并分类编排;对这些段落或句子分别加上他的注释;舒芜本人的文字。
当胡风和各地“胡风分子”纷纷下狱之时,舒芜不仅名噪一时,还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7年,舒芜在他的《<回归五四>后序》中写道,他最初的文章题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后被一改再改成《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系“始料未及”。不过学界对于舒芜的这一澄清仍有疑问,标题从《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最初改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确为舒芜所为,从“小集团”最后上升为“反革命集团”非舒芜所作。舒芜献出“密信”这一叛卖性事件,将舒芜变成了“犹大”。绿原说:“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他把舒芜的典型性称为“舒芜方式”。
“无知”之路上的知识分子
舒芜如何走进“告密者”行列?也许可以把这一行为归之于当时的整个政治环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思想上相信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舒芜,赞成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他认为,不但自己的思想需要改造,而且还有权利,也有义务帮助友人进行改造。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说: “解放后三十年,我走了一条‘改造路’:先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去改造别人;后来是在‘次革命’的地位上自我改造,以求成为‘最革命’;结果是被置于反革命的地位,接受另一性质的改造。反正谁有马克思主义,谁就有权改造别人。而改造的标准、真理的标准,都是实践,集中到最高的实践,即共和国的政治、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与策略。”
舒芜在1955年的行为多年来一直为人所议论,视其“犹大”者有之,为其辩护者不乏其人。但他“背叛”、“出卖”、“陷害”朋友的行为,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在晚年,舒芜做了忏悔:“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但承担什么责任,舒芜并没多言。而且,他似乎对外界纠缠于“告密信”有点不满,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去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好,这我可以理解,换上我,我也不会有什么好感觉的。但事实是,包括交信等问题,都是有出入的。”
不久前过世的另一位“胡风分子”何满子也说:“如果不是舒芜的‘揭发’和上纲上线,并提供那些书信,就不会产生一个子虚乌有的‘胡风集团’,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事件,牵涉到那么多的人。连我这个跟胡风毫无关系的人,竟然也受到了牵连。为此,我这些年写了十多篇反击文章。”
舒芜是“胡风运动”中关键的一个环节,但从整个历史角度看,“舒芜”的出现又是必然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很早就已为当时政治环境所不容。舒芜是历史中大人物的一个棋子而已。如果要总结其一生,舒芜晚年自己说的一句话非常到位:“我解放以前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就为权威所否认;解放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自己,也得到‘那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与权威者达成共识。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到了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回来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
无论是站在舒芜一队的,还是站在对立面的,相当数量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都走了这一段“无知”之路。
晚年努力坚持五四精神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前几天在一个采访中我就谈到了“胡风运动”,其中就有关于舒芜先生在其中的角色。在这一事件中,舒芜是有责任的,但主要不在他个人身上,对他人身作过多的谴责是不合适的。关键我们要研究的是,在那个体制下,他或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特别是舒芜有很高的文学理论修养,他怎么会走上“告密”之路?他的转变有其自身的逻辑。对于这个人物和他的转变,是我计划中所作的研究之一。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他晚年他做了什么?很可贵的是,舒芜晚年在学术和写作上做出了大量成就,比如他对周作人艺术、思想的研究,我曾经就认为他是国内第一人。此外,他晚年写了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这一写作实际上秉承了五四对妇女问题关注的思想脉络。最重要的是,他作了反省,我觉得,舒芜在晚年已经对自己的行为作了反省,这就已经够了,至于达不到某些人的“反省”要求,那是另外一回事请,对他也不公平。
所以,舒芜先生一生有曲折,但他在晚年一直在努力坚持五四精神,这就足够值得我们尊敬了。
当代最重要的文化人之一
张业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对于舒芜先生的过世,我表示哀悼,他是当代最重要的文化人之一,在多方面有着重要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文化史发展,知识分子在几十年中的复杂经历在他身上都有集中体现。
舒芜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后代,在追求进步的一生中,遭遇了很多始料未及的变故,在此过程中,他留下了个人作为文化人的浓重痕迹,尽管有很多非议,但他一生的重要成就还是正面价值居多,比如他在古典文学上的造诣,对五四新文化特别是周氏兄弟精神的传播以及个人创作方面,都是值得书写的。尤其是在他晚年,特别是1980年代后的三十年间,他作为一位重要文化人,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谈到舒芜先生,我们没办法绕开胡风运动。到今年,“胡风集团”的主要人物基本都已去世,而随着提供“材料”的舒芜的离开,代表这段历史差不多成了往事。对于“胡风运动”,总体上我们对当事人的个人评价和表现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但从当代史角度整体上为“胡风运动”作盖棺定论为时尚早。与该事件相关私人的材料我们基本上都能了解,但作为国家层面的一些历史档案还未解密,所以很难从历史角度对该事件作整体把握。我们现在对当时的一些个人立论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个人觉得不必要再纠缠于私人的恩怨,而需要耐心等待某些档案的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