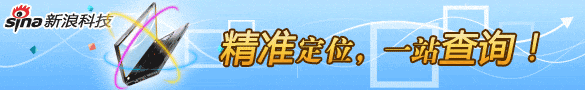实录:京剧艺术家谈流派继承 最怕越传越窄(图)
 京剧艺术家李长春(左)和荀皓导演
京剧艺术家李长春(左)和荀皓导演
 两位名家谈到京剧传承满含感情
两位名家谈到京剧传承满含感情
 京剧艺术家李长春(左)和荀皓导演
京剧艺术家李长春(左)和荀皓导演
 京剧艺术家李长春和新浪网友合影
京剧艺术家李长春和新浪网友合影
新浪娱乐讯 “京剧流派班”全称“中国京剧流派艺术研习班”,举办诉求是以研习班的形式进行京剧流派人才培养,引起了京剧界、文化界极大的兴趣和关注。2010年夏天,京剧流派班的各教学基地已相继开班授课,年底前将举办多场汇报演出,流派班的成绩如何?它是如何培养京剧人才的?对艺术传承意义何在?为此,在与国家京剧院 视频:京剧艺术沙龙第六期 流派继承怕越传越窄 媒体来源:新浪娱乐 联合举办的“京剧艺术沙龙”第六期中,新浪娱乐对话京剧名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长春和著名导演、四大名旦荀慧生之孙荀皓,共谈“流派班”。国家京剧院宋官林院长也谈了他的感受和见解。
宋官林:各位网友好!非常高兴能跟大家见面,我是国家京剧院院长宋官林,感谢新浪娱乐对我们国家京剧院的关爱、关注和支持,也感谢网友对我们国家京剧院的关爱。这次关于京剧流派的课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伴随着京剧艺术传承发展自始至终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京剧流派的传承发展是京剧艺术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我非常高兴的看到,在中央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关心下,京剧流派的传承建设工程终于摆放在了一个应有的位置,引起了全国京剧界热情的参与和支持,也引起了广大戏迷朋友和网友广泛的关注。
闫平: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国家京剧院艺术博物馆,我是闫平。今天仍然是国家京剧院和新浪娱乐合作的京剧艺术沙龙,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是京剧艺术流派班,今天到现场的两位嘉宾是裘派艺术家李长春老师和荀慧生先生的孙子荀皓老师,也是我们非常著名的戏曲导演和电视导演,两位好!
荀皓:你好!大家好!
李长春:你好!大家好!
荀皓:首先祝新浪网友朋友们身体健康、节日快乐,多关心我们的国粹,多关心我们的京剧事业,谢谢你们!
李长春:我是京剧裘派艺术的传人李长春,生旦净丑,所谓过去这些角、这些大师、这些艺术家们,那是真正在我们心目中的艺术家,一直是京剧的门面,这些流派支撑着京剧的发展、传承,一直到现在,生旦净丑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四大名旦,就是四大流派,老生也这样,花脸来说也是这样,我师父裘派掌门人,也是创始人。所以京剧历史上都是这些流派在支撑着,而且人家是真正的可以说京剧的最精粹的京剧艺术,甭管生旦净丑。这些流派,这些艺术家们,他们也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的,形成自己的流派,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承认、公认、喜爱,这也是我们京剧艺术最宝贵的、最珍贵的东西。
京剧要为演员量身定制 流派不是一个人创造的
闫平:现在这个时代,看电视剧的、看电影的会更多一些,央视八套曾播出了荀皓导演也参与导演的《荀慧生》,是您的祖父荀慧生的故事,流派和这些艺术家的名字是挂钩的、是等同的,您在做《荀慧生》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是不是也跟荀派艺术的传承或者对他们的传播有自己的考虑在里面?
荀皓:对,因为这戏播了一段时间了,就是拍我祖父荀慧生的一个电视剧。首先从这个创意开始,就想写活生生的一个荀派创始人我祖父荀慧生,这里面不要拔高,我的第一观点,第二,要写的说荀慧生舞台艺术的光彩很难,你说找谁绝对太是荀慧生了一模一样了,不太现实。我的主要思想就是,要写他能够成为四大名旦,他这一生对艺术是多么的执着、多么的刻苦,一生只奉献于京剧,他也和王先生学习,王瑶卿先生,老夫子陈德霖先生,很多很多的老师教他。但是教要学,他自己学完了要化,化成什么?化成自己的,化成自己的就要结合自己的条件,就是说四大名旦完全不一样的,各有特色,完全是继承、发展。学习流派,就是说学王派、学老夫子,他要结合自己的条件,根据他自己的条件去塑造一个人物。
刚才长春老师也说了,京剧出了这么多的艺术家,而且是大家,但是京剧这个艺术形式,年轻人其实也知道,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主演,按老话说是角儿的艺术,不是别的,说现在我们搞一个戏,写出一个剧本,有一个编剧,说请您演,您没时间,说请您演,您没时间,您有时间,好,你来演。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写出这个本子是量身定作的,就是他的。比如说过去陈墨香先生给荀慧生写剧本,现在叫编剧,过去叫打本子的,不叫编剧,因为要搞一个什么内容,比如就说现在恢复的《红楼二尤》,荀慧生提出来了能不能把这个故事拿出来,一块跟编剧,现在叫编剧,过去叫打本子的,协商出一个提纲,这个提纲打本子落到文字,然后拿回来再和荀慧生去商量,然后一场怎么着、二场怎么着,戏曲的结构是有规律的,戏曲的艺术创作规律是必须要遵守的。搞出来以后荀慧生提出来头场唱一场二黄,二场我唱西皮,三场唱什么高拨子、反二黄,根据这个陈墨香先生再去填词,根据这个人物此时此刻所应该表达的内心东西来去填这个词。师哥也知道,有十三道辙口,每个人的嗓音条件不一样,他适合哪一个,这个词必须落到这个上是荀慧生最合适的,最能发挥他的常处的。写出来的这个剧本再通过时间反复磨炼,那就是他的,不是任何人的,所以他创造了流派。
光继承流派不行 得赋予它生命力
闫平:《香罗带》这个戏也是很长时间没见排了?
荀皓:没人演,原来只有《红娘》,《红娘》传了70多年。
闫平:它是荀慧生先生当年根据自己条件创作出来的一个剧目,就像您刚才说的环境产生流派。我们今天做这个流派班,我们怎么去教这些青年的演员?我们是教他荀慧生的手势在这儿,或者这个腔是怎么使的,这个教出来的学生是不是我们讲的流派?
荀皓:我们现在要弘扬是个前提,要发展流派是个大的任务,就不是说当年荀慧生是怎么一指,当年荀慧生是怎么样一个眼神,不,老先生老说戏比天大,所谓戏比天大,演的,因为老先生创造这些人物,别的不敢说,就先说,甭说子不言父,先说我爷爷,他创造这些东西出来以后,他完全是结合人物此时此刻的内心的,所有的动作是次要的,你要演人物,我爷爷老说唱京剧,唱的最高境界是说,说就要有对象,跟谁说?跟观众说。你有了对象,像说一样跟他聊天,就跟观众产生了共鸣,观众就容易被你感染,这是从唱。从念,还是从人物出发,他说要想着念,不要抢着念,抢着念是在重复自己今天、明天、后天,演一个戏同样的,想着念是在人物之中。所以他有一个戏曲的理论,叫戏演三分生,不要永远重复自己,这样你就没有任何进步。
我一直要求,演人物、演人物,说荀的特点这么指、那么指、各种抬杠,我说都错了,为什么?说不管怎么指,荀说这么一指是这么指,他不是这么一指,完全在人物,跟观众互动,这个指变成次要的,不是这个指,手眼身法步,不是,所以荀的特点在脑袋这儿呢、在表情呢,所有的都是辅助的,决不会单纯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动作,不能反映人物的内心。
所以这次在八楼(畅和园小剧场)演出,观众是可爱的,为什么呢?就是说老戏说《香罗带》是78年了,今天整理,因为过去的戏比较长,必须要压缩、整理,把它紧凑一点,但今天挖出来这个戏,我都没想到,作为京剧故事情节有三次满堂大掌声,太少了,多年不见了!他受了冤枉了,最后清白出来了,给她丈夫一个嘴巴,后边她又受怨了,要斩没斩了,又回来了,又掌声,说明什么?说明这样咱们是挖掘了流派、是传承了流派,为什么?它有生命力。今天的观众能理解了,你必须要把观众带到里面来,让今天的观众通过历史故事他有所感悟、他有所吸收,有所总结,这是我们要做的。说50年、100年,再一代还要按照这种创作的思路去继承流派,不是模仿。
刘长瑜老说,跟我爷爷学戏完了特像。说:“后来我演完戏特高兴,等荀先生到后台夸我呢,荀先生一进来,说以后不教你了,我没让你演荀慧生,我没让你演一个60多岁的老头,我让你演的人物。”说上海“三小一白”,那边他一期是3000大洋十天,过去什么概念?北京买一所四合院300多大洋,你说是什么概念,但是我爸爸老说,说你爷爷甭说3000,你给他200大洋他能数到天亮数不完,数一落倒了,明天再来,他不看这个,跟钱没关系。他挣这么多钱,吃什么、穿什么?你也见过,没有,就一个呢子大衣,冬天就是一个呢子的中山服,但是自己特别满足。我小时候老听见着谁都夸耀,说我这个中山服跟你们的不一样?说这不也是呢子的吗?说不,这里面絮了一个丝绵里,很舒服,他也就穿到这儿了,他没穿过别的。特别满足、特别简单。您看电视剧也是,烙饼摊鸡蛋就乐的不行了。
闫平:但是裘盛戎先生是比较爱享受吗?
李长春:不是这样的。
闫平:您给说说。
李长春:接着说说我师傅的习惯、我师傅的一天。因为我,为什么前面我说我比很多师哥更了解,我十几年来跟着我师父在一起形影不离吧,来伺候他。我师父是一个沉默、少言,话很少的一个人,他话不多,但是又有一定的幽默性。
荀皓:特别幽默。
李长春:他可以说一心一意全身心全是在台上,后来收了徒弟,也想到他自己传承的事情,把一部分心思放在学生上头。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多的好像享受或者什么,比如说他的吃,他的吃非常随便,我师父最喜欢吃的三个饭店,第一烤肉宛,第二鸿宾楼,第三东来顺,他本身喜欢吃羊肉,所以我拜师的时候,我们校长征求他意见,在哪好?东来顺。
除了他规律的休息以外脑袋里没别的就是戏,你看晚年一些成功的创作,晚年留下的和马、谭、张合作的《赵氏孤儿》精品,现代戏《雪花飘》,精品。他在艺术上,一个是自己琢磨,一个他喜欢跟别人研究,尊重别人。比如《赵氏孤儿》里大家最喜欢的一段,也是重新起的名字,很多朋友也都喜欢这段,汉调,“我魏绛”,就是我师父和音乐家李慕良先生共同创作出来的,从来没有这种调,花脸更没有这种调,他是吸取了地方戏,从打击乐一直研究到唱腔,怎么样运用、怎么样配合,所以给人们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荀皓:刚才师哥说的这个“我魏绛”,这是一出大戏,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继承,我们作为一个晚辈,下面要办不管什么流派学习班,点到一个题,我常说,现在既然举到“我魏绛”,这么大一出戏,我们作为想帮助青年人能够提高,更进一步,首先要考虑为什么这么大一出戏那么多的艺术家,到今天只流传一个“我魏绛”,为什么?要想想啊,这是个大事啊,这不是个小事啊,说我创这个、创那个,有创新没有流传,这个东西就不是创新,没有用。
闫平:流派不流传也不称其为流派了。
荀皓:不流就没有传,就不成为流派,所以他创造一个,这个汉调“我魏绛”。要说举,别的不敢举了,还是说荀吧,比如说《红娘》,有那么多大段唱,我听我父亲讲,说你爷爷当年创的时候,有专业演员听完了要认真下苦工夫学一段时间才能把它唱好,但是这一出戏也要考虑到另一层观众,新的观众我们怎么去领,知识文化浅的,按过去讲话,劳动人民,过去讲拉洋车的,就类似吧,这话,就是普通劳动人民,这一出戏也有他喜欢的,所以就有“叫张生”,听一遍就会,明天大街谁都会哼哼,这一出戏要这样去安排,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才能照顾大面更宽广。这是一个创作很重要的一个规律,说想办法怎么难,越难越好。
我曾经搞过一个戏,就想,跟高雅侬一块,就说《李清照》这个戏,总想把它弄好,当然李维康的条件也好,谁都学不了,他太难了,票友都学不了,别说不怎么熟悉京剧这个艺术形式,咱们怎么去把他领进来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