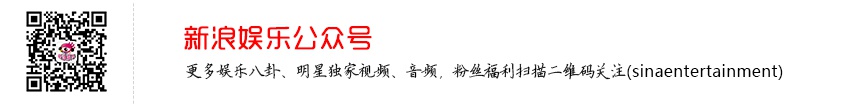年过半百的杨辉与他剧中人物一样命运波折。
年过半百的杨辉与他剧中人物一样命运波折。
 杨辉的新戏《边界》讨论了一个国际性话题,“我们讲人性,讲平民受到的战争的伤害。”
杨辉的新戏《边界》讨论了一个国际性话题,“我们讲人性,讲平民受到的战争的伤害。”
因为热门舞台剧《战马》和《大先生》,一度无人问津的“偶戏”在近一年里拥有了颇高的曝光度。两部戏让很多人发现,原来偶戏不只是演给小孩子看的, 舞台上栩栩如生的偶,不仅能同真人演员一样表情达意,有时还更抢眼球。旅欧的中国偶戏大师杨辉(Yeung Fai),4月受台湾国际艺术节之邀,在台北 首演新剧《边界》,跨越中国传统布袋戏与西方当代表演艺术的边界,演绎战争背景下小人物的离散、漂泊与寻根。如今年过半百的杨辉,旅居海外二十余载,与他 的剧中人物一样命运波折。新京报专访杨辉,讲述偶戏大师背后的故事。
出 身
他是漳州布袋戏世家的第五代传人
因代替生病的二哥演出,从而开启事业
留着长发,身材精瘦的杨辉,一口闽南口音,长相酷似印第安人。他生于1964年,是漳州布袋戏世家的第五代传人。父亲杨胜是“北派布袋戏宗师”,对台湾 布袋戏也影响深远,大哥杨亚州是木偶雕刻家,二哥杨烽曾任中国木偶皮影协会副会长。杨辉从小跟着二哥学布袋戏,14岁考入福建省艺术学院木偶专业,毕业后 留校任教。当时国内的偶戏很不景气,剧团也总演一成不变的传统戏,这让杨辉深感苦闷,一度想放弃家传。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出国潮中, 杨辉去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打工,后因生计所迫干回老本行演起偶戏,渐渐地足迹遍布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国家。一次,因代替生病的二哥去西班牙演 出,杨辉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台下的一位法国观众,这位观众恰好是法国一家戏剧中心的制作人,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杨辉开始到法国发展他的事业。转战欧洲后, 杨辉开始大量接触西方当代艺术,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他想,“欧洲当代艺术很多的象征、写意,其实都是受中国戏曲的启发,为什么我们不行呢?”他也越来越 意识到,偶戏不是没人看,作为表演艺术的偶戏要与当代结合,才能找到当代的观众,“打动观众,偶戏也做得到”。
杨辉在欧洲发展的另一位 贵人是法国斯特拉斯堡青年剧院的院长Grégoire Callies,他们曾于2004年合作改编元杂剧《窦娥冤》,以《六月雪》为名搬上舞台,杨辉在 剧中操纵了二十多个偶。此后,他们又相继合作了融合漳州布袋戏与日本传统文乐木偶戏的《堂吉诃德》,以及《奥德赛》的儿童版《奥德赛1-2-3》。杨辉曾 在斯特拉斯堡住了八年,对那段时光充满了感激。“如果说福建省艺校的五年是我的小学,斯特拉斯堡那八年就是我的中学,我在那里看了很多戏,看了很多当代艺术”。
流 浪
24岁起辗转居住多个国家,是个“世界人”
到现在也不是很稳定,经历太多悲欢离合
迄今为止,杨辉创作了六部偶戏作品,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欢迎。二十多年前,他的独角偶戏《京剧之景》曾在北美、南美、欧洲、亚洲的艺术节上演。2009年 他受瑞士洛桑剧院委约创作了改编自他个人家族史的《操偶师的故事》,三年演出超过360场,巡演至全世界二十多国,曾登上香港艺术节和台湾国际艺术节。 2013年,杨辉再度与洛桑剧院合作偶戏《牛仔裤》,以记录的视角聚焦牛仔裤生产的过程。
2015年,他的偶戏《茶馆》在欧洲著名的 “沙勒维尔国际木偶戏剧节”上演,讲述过去操偶师在茶馆演出,同时扮演教育与文化的象征,而今却被其他现代的娱乐方式所取代。此次在台北演出的《边界》, 同样未演先火,开演前几周票就全部售罄。在法国,杨辉是著名的“莫里哀戏剧奖”史上第一位来自亚洲的表演嘉宾,还是法国沙勒维尔-梅济耶尔市国立高等偶戏 艺术学校唯一的亚洲教师,这所学校是欧洲公认最重要的偶戏学校。
杨辉将自己的生活形容为“流浪”,自24岁离开中国内地起,他辗转居住 过多个国家,“到现在也是很不稳定,命运非常坎坷,人生的悲欢离合经历太多了。这个月在瑞士演出,早上6点还要去移民局排队办身份”。如今的杨辉,拿着香 港身份,有四个国家的居留证,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界人”。他的偶戏作品在全世界巡演,受邀在纽约林肯中心、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等知名剧院演出。除了闽南 话、普通话,他还会讲英文、西班牙语、法语、粤语,“都讲得不好。我儿子在法国出生,我跟他学法语;英文会讲,但写起来要用谷歌翻译。语言是我的弱点,所 以我就创作少语言的作品”,杨辉说。
每回出国巡演,杨辉领着四五个人的小团队就出发了。2008年,因在Callies导演的项目中合作,杨辉与法国操偶师、演员Yoann Pencolé相识,后者追随他至今,“这些学生都跟了我很多年了,我喜欢小的(团队),大家在一起也很好玩”。
新 戏
《边界》灵感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讲的还是情感与人性
杨辉的新戏《边界》是一部60分钟的偶戏,宛若一部诗意铺陈的电影,以战争为背景,运用多重叙述视角编织成一幅浩瀚时代下的历史缩影。他介绍说,戏的灵 感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人不得已离开家乡,一生颠沛流离,让我深受感动。我自己的生活也很不明确,到处流浪,我对二战时期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也访问 了很多家庭。在那个大变迁的时期,平民百姓没有选择权,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想这可不可以用偶戏创作出来,这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虽然描写血淋淋的战争, 但讲的还是情感与人性”。
在《边界》的开场,三层嵌套式帷幕的舞台层层打开,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舞台上人偶同台,杨辉与两位台 湾演员洪健藏、陈佳豪合作,以近40个手制的布袋偶、提线偶、手套偶,融合灯光与影像,将故事娓娓道来。被迫卷入异国战争的士兵,父亲遇难的孤儿,因边界 漂移、家乡变异乡的难民,甚至是巢穴被占的乌鸦……故事中,角色没有名字和清晰的故事线,而是以意识流的叙述串联起来。剧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演绎的是 内战中的同族相杀,杨辉左右手各持一只偶,上演“两手互搏”,背景如同庙宇的祭坛,这些牺牲者何尝不是战争的祭品呢?正如杨辉所说,“对我来说,人类的开 始没有边界,边界是人为的概念,是意识形态的划线。但我们有很多东西都处于边界之间,很多边界也是尴尬、模糊的”。
新作《边界》中还插 入了一段与创作者自身相关的记忆。杨辉将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变成剧中的一段戏中戏,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是法德边界的斯特拉斯堡,杨辉曾在那里居住了八 年,汲取欧洲当代艺术的营养。“斯特拉斯堡在历史上一会儿归法国,一会儿归德国,那里的人身份很不明确,尤其对处在成长期的人来说影响很大。有的家庭两个 兄弟,一个参加德军,去东线作战,另一个在法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边界》讨论了一个国际性的话题。“我们讲人性,讲平民受到的战 争的伤害。偶戏是很单纯的东西,而艺术的基本点是人性。以前演传统戏,我差点要转行,因为情感输送不出来。后来自己做戏,《操偶师的故事》就是我爸爸的故 事,还有《边界》,每次演都有很多回忆涌出来。这就是剧场,观众在那边,跟我们融合在一起。偶戏是人类的智慧,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家族”,杨辉说。
Q&A
1
新京报:这次剧名叫《边界》,在跨越传统和现代的边界上,你经历了什么?
杨辉:非常困难,因为要打破很多东西,传统就是这不能做、那不能做,因为有规则。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做你爸爸的东西。其实我爸爸跟我爷爷也不一样,我 爸爸也在我爷爷基础上创新。我们家五代人,每一代都有留下一些偶。欧洲的偶戏来自街头,我们以前是乡村,一个村子就一条街,偶戏在茶馆演出。以前的偶都是 说书人演,那时候没什么娱乐,也不是人人都识字,我爷爷、曾祖父都是识字的说书先生。我看到我爷爷的偶非常小,他说书,就在茶馆的桌子上演偶戏,后来慢慢 加了乐师,有了表演。闽南的偶戏一开始也不是京剧,我父亲是北派创始人,把京剧系统跟偶结合起来。所以,什么叫传统?谁可以代表传统?在什么时间点上你代 表传统?我后来就说,管他呢,我就做我自己。我在国外如果只做中国传统偶戏,没有人会支持我,给我钱,我怎么生活下来,我一直靠偶来生活。
2
新京报:在出国前你已经有了过硬的传统技术,出国给你带来什么刺激?
杨辉:国外更多是自由的空间和想象力。我们以前读书比较缺少这个,但我们的基本功都很扎实。从亚洲出去的艺术家,包括舞者、画家,底子都很好,外国人学 画画的,你叫他画素描他可能画不了,都只会当代的抽象的东西。技术通过以后,你可以飞得更高更自由,有技术来支持你的想法。我在法国教专业,就是让亚洲学 生和欧洲学生互相平衡一点,亚洲学生让他们更自由地去想象,欧洲学生就要他们练一下功。
3
新京报:国内也有很多偶戏和偶剧团,但市面上能见到的演出却不多。最近一年是因为《战马》中文版在国内演出很受欢迎,很多人才注意到偶戏。
杨辉:我们和《战马》的南非剧团Handspring(掌上乾坤剧团)一起在林肯中心演出,他们也邀请我去他们剧团教课。他们的偶是南非的传统技术,用 藤条编成,英国的沙发椅很多也是那个做的。《战马》也是把传统技艺当代化,做得很漂亮。从我们华人来讲,我们的传统技艺太多了,欧洲现在常见到很多大的纸 偶,造型抽象,非常当代,这个技术和我们以前烧给人往生的那种纸人、纸房子(祭祀用品)差不多。
4
新京报:你认为偶戏适于表达什么样的故事?有没有它自身的局限?
杨辉:偶是没有边界的,根据需要,做什么都可以。创作最难就是找到体现的方法,是用偶,还是用手,还是人偶关系。我们基本上都是没台词或少台词的,《战 马》他们都是画故事板的,台词最后写上去。我跟《芝麻街》他们关系也很好,去他们工作室,整个桌子都是故事板,也是画出来的,我们也是这样。
5
新京报:你也在国内学传统偶戏,对今天偶戏在内地没什么市场怎么看?
杨辉:80年代文化部派我去美国访问演出,我接触到日本当代偶戏,才发现我们的舞美不行,故事不行,感情是假的,那时候就想要出去学一下再回来。国内的 偶戏团,被国家养起来,人就懒了,不演戏,就做偶卖游客,变成做生意了。全部保护反而没有了空气,还是需要一点自由,不然人都是有惰性的。都保护起来是养 熊猫,离开那个环境就不行了。我们这些人出去,会灯光,会舞美,会开车,会去跟人家谈巡演,什么都会。
6
新京报:你的演出都很多,但欧洲这些年经济状况不好,是否有影响?
杨辉:我们做得越多,缴税越高。欧洲有经济问题和治安问题,日子不好过,但是偶戏我可以做小的,欧洲不行我就去南美,我是从那边一路走来的。我们演出都 是这个节目把钱赚回来,再用到第二个制作里,我是很厉害,都不会亏本。我做很多独角戏,我在舞台上很享受。艺术家生活简单就好,又不是歌星、影星。这种职 业就是寻找快乐,有时候觉得也挺酷的。
新京报记者 陈然 台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