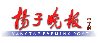陈凯歌谈父亲心怀愧疚 自曝全家都爱上网偷菜
 陈凯歌接受采访 尤晓源 摄
陈凯歌接受采访 尤晓源 摄
 葛优饰演程婴
葛优饰演程婴
凌晨三点,我收拾起采访本和录音笔,在陈凯歌和陈红热情又显疲惫的目送中离开他们的房间。他们只能休息三个小时,又要出发去下一个城市做《赵氏孤儿》的宣传。这次,我们聊了足足三个小时。陈凯歌的面前,一碗冷掉的面条原封不动地放着,因为房间里气温高,他只穿一件白色圆领汗衫,不时会发出低沉的带有磁性的笑声。他笑起来的样子就是一位温和地道的"北京纯爷们"。
电影:《赵氏孤儿》说的是礼义仁智信
一部《霸王别姬》使陈凯歌步入人生的巅峰,一部《无极》又曾让他成了网络“娱乐”的对象,从《黄土地》到今天的《赵氏孤儿》,人们对他的作品评价不一,但都不影响对他在电影中文化追求的肯定。当聊起新片《赵氏孤儿》时,我忽然发现了陈凯歌的孩童气,还带点儿犟的那种感觉。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本来对信仰就有他的那份执著,要与当下人进行精神的接轨又不失尊严,这应该是件挺难的事,但在这部新片中,陈凯歌成功地做到了,接了地气。
采访是从他的自传《少年陈凯歌》引起,提到这本书凯歌眼中顿时有了神采,看得出他对这本书很满意。毕竟那里面是他的亲身经历,风云际会,往事不堪回首但必须回首。
扬子晚报:我曾读过你的《少年陈凯歌》,里面说你家的保姆因为饥饿偷吃点面,你说人在饥饿恐惧面前,爱就没有了。是不是可以理解程婴这个小人物在恐惧面前,也是这样?
陈凯歌:我本质上还是认同礼义仁智信这些东西,是中国人多少年总结出来的,不是偶然发生的,礼义仁智信我觉得它是给中国人立规矩的,你应该怎么做人,是一个社会契约式的东西,但是这个社会契约在今天被粉碎了,因为整个时代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大规模进入之后,最后防线守不住了。我为什么会把程婴写成一个百姓小人物呢,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在京剧里是个失败者,还是希望能和今天的实际相结合。
忠义这两个字我本身是非常认同的,但是如果把忠义这样的标准放到百姓身上,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所以我举老保姆的例子。其实人都是由当下决定的,你不能说他不是个好人,但是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是有恐惧的,所以我觉得程婴厉害就厉害在,他是顺着常识走的,他虽然也有恐惧,但是他在恐惧中仍然不违背常识,这个就已经够了。我们看到他惊恐的状态,但只要他确保自己的孩子安全的情况下,他愿意去救赵家的孩子,如果他不去屠岸贾那儿,这个事跟他没有关系,他愿意去帮助别人,这就已经是了不得了。所以我在处理程婴这个人物时,我就觉得一定要可信,所以这个电影所有的故事都是从程婴开始的,从程婴来切入,如果程婴能做到的,应该大家都能做到。
扬子晚报:你的书中说到十四岁时,批斗父亲时在逼迫下你也用手推了你父亲,文字中表达了一种爱恨的交织。这部戏中,儿子赵武(程勃)和爹的对抗中,也有你的影子吗?
陈凯歌: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在西方,父子关系始终是主体,我觉得在“文革”中的事,中国人有一种东西,就是生怕被集体甩掉,一旦脱离了集体,你没有办法成为个体,所以“文革”的时候就是我不愿意被甩出去,你要不愿意被甩,你就要证明你是集体的一部分,你必须做一件事,就是对被批斗的父亲不尊敬,但是自己心里清楚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我对我父亲一直怀有愧疚的,但是我父亲对于我做错的事情完全不计较,这个就是程婴怎么对待孩子,就是我父亲当年怎么对待我,再加上我自己有了孩子,我就更体会这个孩子的心情是什么。
扬子晚报:程婴的可靠和诚信,似乎是这个片子给人带来思考的中心点,在你的《梅兰芳》中,也有十三燕临死前把戏服拿出来送给赛过自己的徒弟这样感人的细节。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现代人的诚信越来越少,更显得这样的可靠弥足珍贵?
陈凯歌:不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人就都不好了,为什么人不好了?为什么人在亲情友情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倒退的状态?因为生存环境的艰难和残酷,这个是有道理的。现在大学生出来,就得到处找工作,不一定找得到,所以就叫人人为己的观念被生存的需求放大了。我在我的电影中间,不光在讲人性的变异,也在对生存环境的合理性提问,举例来说,《霸王别姬》中一唱戏的,他招谁了?他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不公正,会遇到这么多的坎坷?很简单,他的生存和环境不合理。大的时代环境变了,他这个人跟不上这个时代,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因为你必须自私,所以我觉得《赵氏孤儿》这样的电影不仅要提出诚信缺失的事实,还要去探究诚信缺失的原因,生存环境的不合理。
扬子晚报:“不把自己的敌人当敌人那就天下无敌”等闪耀智慧的警言无处不在,这些台词也构成了不少特色,尤其在杀人魔王屠岸贾的嘴里说出。
陈凯歌:电影总体上来讲是有一个自己的系统,这个系统里面包括一个原则,就是电影地语言要精练而短,应该尽可能地少用语言,但是少用不等于不用,包括一些警句,你必须在一个非常适当的情况之下才能说出来,“不把你的敌人当敌人,那就天下无敌”,这样的话必须有前因有后果,其实屠岸贾输给谁了?他输给自己了。程婴赢了谁?赢了自己,他可以把私仇放下,只剩下义愤。所以表面上看是屠岸贾的语言,其实说的是程婴,你看屠岸贾喝他的药都不怀疑,他是不是没有把程婴当成敌人?因此他是无敌的。每个人一定都有敌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你在与你的敌人斗争中,自己发展,自己成长,自己变化,那走到最后,你有没有敌人?
有位教授看过电影后说,这部电影是中国元素,世界表达。屠岸贾这个问题问得是很犀利的,“你有什么权利决定你儿子的生死?有什么权利让别人的孩子为你报仇?”这两句话其实是今天人的提问,不仅是对《赵氏孤儿》的提问。
扬子晚报:树林中的战争以及后来决斗时两度不还手,让屠岸贾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人,显露出他作为干爹的温柔一面。《赵氏孤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复仇故事?
陈凯歌:如果这个事情是计划的,他遇到危险我就要救他,那就是假的,就是在这一刻,他回去要救他,这就是所谓的人和事情的真实性,我同时还有个感觉,我觉得他作恶以后想做好人,他心中有暗自的忏悔。但是,王学圻(饰屠岸贾)这个人物之所以是立体的、成功的人物,就是他还是没能赢得了自己,他可以在这个当下救了赵孤,但是如果他说程婴,我听你的,我不会再杀这孩子,我们两清,故事就是另外一个结局,先动手杀程婴的是屠岸贾,说明他的心结一直到他死都解不开,他最后是可悲的。
扬子晚报:是否可以认为最淡定伟大的是庄姬,她自杀死前说,不要告诉孩子的仇人是谁,父母是谁。庄姬戏不多但在她身上有着强烈的冲突。
陈凯歌:我觉得庄姬这个女人,虽然她的篇幅不多,但是有对比的。她开始时高高在上,永远富贵下去的形象,一刹那她的命运就改变了,她连一个普通妇女最卑微的愿望都实现不了了。她保不住她刚出生的孩子,多惨多可怜的一个女人,但是她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她能用最平静的态度处理这个事情,这就是性格,她多聪明啊,她对程婴说那话,两重含义,第一求你救我孩子,第二含义是对韩厥说我的孩子不会影响到你的主子,这个女人了不得!我们在编剧时,曾经想到她怎么拿这把匕首去刺韩厥,谁想到她最后对准的是自己!她对人性有多么大的信任啊,(陈红:这也是女人的直觉,她对程婴的直觉),其实人世间所有的壮举都是在突然或没办法的时候出现的。
扬子晚报:不少人认为影片下半部分没有上半部分精彩,你如何看呢?
陈凯歌:前半段精彩是因为在讲故事,后半段是在讲人物感情的变化,因此故事性没有前半段强,电影前半部是“事”,后半部是“情”。合起来才是“事情”。如果一个电影只是在说事,那就太简单,要将事情串起来才圆满。我觉得下半部分的戏,是由前半部分激烈的外部的冲突变成了尖锐的内心冲突,因为程婴本身是陷入矛盾的,他最初就是要把这个小孩变成一个工具,他对这个小孩没有感情,但是他紧接着就陷入一个矛盾,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南辕北辙,离复仇越来越远,走不到复仇那个地方去了,当这个小孩长大,有了自己独立的意识,有了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他没法控制它了,这是一次博弈。救孤并不难拍,因为它的戏剧张力在那里。相反,程婴对赵孤15年的养育之恩的表现难度就很大,也有人说,恰恰后半部分才是你陈凯歌的。
演员:葛优是个万人迷
说到葛优时,陈凯歌像在片场指挥千军万马一样,左手用力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声调同时加大了一倍,看得出他对葛爷的喜爱。而在谈到爱子在片中的表演时,他的声音一下子绵软下来,爱怜之心溢于言表。“你看他演得可爱吧?呵呵!”一个大导演瞬间变为一个沉浸在幸福中的父亲。
扬子晚报:葛优扮演的程婴很到位,这也是我第一次看他的表演没有发出笑声。你眼中的葛优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凯歌:我跟谁都没说过,葛优是这样一个他从他的人物身上学东西,葛优是他演过的所有人物的总和,不是他把自己平均分配给他所有的角色,比如说葛优确实胆小,从哪来的?就是他追寻他演的那些小人物,包括《活着》,他越想越害怕,所以他变成了今天的葛优,但是他也演了不少讲诚信的人物,他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这些人物了解到,做一个可靠的人是重要的,他真是一个万人迷,但是他的谦卑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人物里来的,这个是葛优了不起的地方,角色居然影响了他。有的演员,演一个摔一个,越演越狂,这就说明他跟他演的人物是隔绝的。葛优是老从这些人物里学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是天生的演员料,这东西是教不来的,我认为他是最会运用形体的,没有台词、没有对话的时候,哪怕是一个背影,你还是觉得他浑身是戏,这个不是过分地褒奖他,只是说这么一个感觉,他其实是非常自信的,一般人演这个角色肯定害怕,因为演喜剧演成习惯了。但没有,悲剧角色又让他完全是另一个人。
扬子晚报:观众曾评价海清演的媳妇非常真实,现在片子播出了,你也是这样认为?
陈凯歌:海清不错,她和程婴演的是平常夫妻,平常夫妻才可靠,最后墙打开,你看海清演得多好,绝望和无助,其实她已经了解她丈夫的心思,她知道她自己的孩子保不住了,这样一小节戏精彩至极。
扬子晚报:有观众说黄晓明不会表演,只会放电?所以一出场年轻观众就笑。
陈凯歌:(笑)黄晓明被偶像化了,对偶像明星观众会有一个非此即彼的判断,既然你是偶像,那你肯定就不会演戏。如果你说葛优是个偶像,大家也不会接受的,他肯定不是偶像,他就是演技派,所以你不能兼而得之。你既然是偶像,那我们永远拿你当偶像看,你怎么演我都不认为你会演,汤姆·克鲁斯是美国的黄晓明,他演得多好啊,但是就是不被认定,这个就是黄晓明的“指环”,将来他要用多大的力气才能挣脱这个“指环”。
扬子晚报:你们的儿子在片中 “客串”了晋灵公的小儿子,是否会就此培养他演艺方面的特长?
陈凯歌:我和陈红都没有替儿子设计将来,将来如果他确实有兴趣,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我们知道,我们一旦感觉到在演艺上发展也无妨。这次拍前他也会有点小紧张,当你告诉他之后,他就自己演了,很放松,演得不错,一两条就过了,你看他演得可爱吧?呵呵。
坚守:“玩意”与票房都需要
与陈凯歌谈文化命题,气氛就严肃了许多,他总是沉默片刻,然后一字一句说出他深思熟虑的话,语调平静,不张扬更无造作,那双能洞穿一切的眼睛认真地盯着你,让你心里一阵阵发紧,而大脑又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思路前行——感染力和控制力可能就是一个导演最重要的基本功吧。
扬子晚报:忠义二字穿插整个戏,观众对剧中的价值观表现了高度的认可,是否过去我们高调唱得太多?
陈凯歌:常识是多少代积累下来的东西。高调唱不得,我们是一个相当情绪化的民族,理性的判断都比较少,当潮水来得太猛烈的时候,很多我们原来相信的东西倒塌了,所以现在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回头看,我们要去捡回来,这不是十年八年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有信心,我们终究会认识到原来传统价值的东西会帮助我们重新建构起信仰。
扬子晚报:与前几部略小众化的电影相比,这部电影让我们感觉陈导又回到普通人中间了。
陈凯歌:随着自己拍电影的时间越来越长,也会有一些感悟。你有对文化上面的想法,一定要通过一个更加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我父亲没跟我讲过什么电影方面的技巧,他就跟我讲了四个字:主观客观,所以我就觉得所有做创作的人都要觉得你怎么样让你的观众去接受你的想法。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在这个电影上,大家接受上是非常好的,我只是站在他们中间。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看到了《赵氏孤儿》,记住了程婴这个名字。那时候我生活得很痛苦,希望有一个像陈婴一样的人来帮我,走出这种痛苦。其实在这部电影里,有的都是我心里边想的一些东西,里面没有高屋建瓴的思想,也没有扭曲变形的人性。就是一些朴素的东西。
扬子晚报:在娱乐的时代如何让充满文化元素的电影生存?
陈凯歌:你也曾经搞过京剧吧,我就举一个梨园行的例子:戏曲界讲两个东西:票房、玩意,票房跟玩意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你在强调票房的年代你就可以没有玩意,京剧在以前的中国就是最大的娱乐了,你看一场梅兰芳的戏那还不是娱乐嘛?但是你从梅先生的戏里你又得到了娱乐以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是回答了,也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坚持和坚守。
扬子晚报:你的很多电影,都是在大人物中的小故事,和小人物的大背景中传递东方的仁爱礼义,也有人称你为文化的传教士。
陈凯歌:我没有那么了不起,唯一能说的是,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电影,必然地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相连接,这两样东西是必须连接的,如果在一个国家的电影中间,没有文化特质,中国电影如果没有中国的特质,它不是电影。但是别人说我是文化传教士或布道者,我觉得我远远不够,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文化、历史不要轻易丢掉。
扬子晚报:在黑泽明的电影中,如《罗生门》、《七武士》等,对场面做出了张力十足的处理,利用针锋相对的对峙冲突,来展示人生的欲望和毁灭,有评论家认为你的镜头影像中能看到黑泽明的身影,称你是中国电影界的黑泽明?
陈凯歌:不不不,这个绝不能由此来判断说我是不是中国的黑泽明,那是位伟大的导演艺术家。黑泽明表现的是什么呢,是日本文化的矛盾冲突,所以他被看成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他并不是给日本文化唱赞歌的。西方人说你要想了解日本人,你就要看黑泽明。
扬子晚报:一部片子公映,观众和网民会有评头论足,如遇猛烈的批评会怎样面对?
陈凯歌:照单全收,不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会有它存在的理由,听取、接受、筛选,探讨,这都是个让人快乐和进步的过程。
家庭:我们常一起“偷菜”
恩爱夫妻,一个是制片人,一个是导演,家门里的故事应该很多。当我问陈红问题时,陈凯歌会抢着答题;问陈凯歌时,陈红会抢着答题。一个回答另一个则不断点头称是,不用商量,十分有趣。
扬子晚报:陈红对你具体的拍摄会提些意见吗?
陈红: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导演特别尊重个体,他把这种对个体尊重放在了他的电影里,他不停的在否定自己,文学剧本发给演员,你们拿回去看,等再给大家分镜头剧本的时候,似乎和文学剧本差别很大,其实内在的必然的联系都没变。我们两个在一起讨论最多的不是生活就是电影,因为对电影的热爱是我们两个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陈凯歌:我们两个没争执,不是说惊人的一致,是她对我的工作方法完全没有怀疑。当然,她会对我某个镜头提些建议,互相否定也会有,我们是高度默契的一种合作。
扬子晚报:曾有报道说你一直在寻找可靠的人,现在找到了,是陈红。
陈红:他要的那种可靠就是有程婴的那种精神理想的人,但是我没有经历那种(笑),这是他对人性的渴望。
扬子晚报:你平时上网吗?
陈凯歌:电影占据我们生活太大的部分,有95%吧,自己的娱乐也很少,挺遗憾的。
陈红:我从96年跟他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出去度过假,以后60%的工作时间就够了,应该边享受边工作,他有一天开玩笑说不想拍电影了,我知道是开玩笑的,但是我还认真了一把,特别的开心,工作其实是很苦。我们都不拒绝网络,会看看新闻,他有时候也“偷菜”,他有时候也和我儿子两个去“偷菜”。
本报记者 鞠健夫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