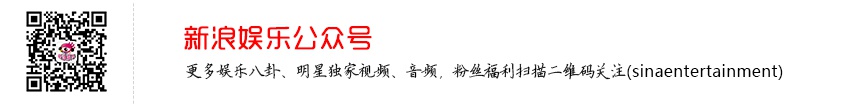鲁韵子/文 王远宏/摄影 刘嘉奇/摄像
新浪娱乐讯 今年北京的冬天来得很突然。才11月初,玻璃窗外就只剩一片雾沉沉的阴天,几棵颤巍巍的老树。顶着寒气,裹在羽绒长大衣里的董子健摇摇晃晃走进采访间。他抱一杯热水,鼻孔翕张着,一脸的欲喷嚏还休。
《山河故人》的宣传期还未结束又刚提名了金马影帝,还要制定自己投资并主演的《少年巴比伦》的宣传策略,21岁的他正忙得不可开交,这感冒来得着实不巧。不过,这无损于这位少年得志者特有的怡然自得。在采访开始前,董子健捡起桌上的糖果罐发问,他的声音因鼻子不通气而闷得厉害:“你吃大白兔吗?”
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这位有望成为史上第二年轻金马影帝的少年把手伸进了糖堆:“那我先吃一块,小时候就爱吃这个。”
就这样,在一丝隐约的甜香中,我们与少年小董聊起了他的新片《德兰》和美国留学记,他从“第一经纪人王金花的儿子”到贾樟柯爱将、再到出征金马的散碎体悟。当然,作为老北京、古着迷和影视公司老板的经验也由他独家放送。他的语言始终如陈国富形容的一般早熟。而他的眼睛——那依然是一双青春的、追寻着一切变化和可能的天之骄子的眼睛。
[小董自述]
为拍《德兰》,我像跳跳糖一样在睡袋中融化
在拍《德兰》之前,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旁边的一个小镇待了一年半,在格林威尔大学(Greenville College)做交换生,学国际政治和电影。其实也没什么,就打打工、刷盘子,挣了钱也没处用。刚好碰上我们社区有个影像比赛,让你从三样物品——墨镜,电梯和酒店的床——联想,用三天天做一个短片。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拍片参赛,拿了几千美金的奖金,我们特开心,你想,要挣这么多得刷多久的盘子啊?
拿了那些钱,我们就直接干个影像社,用iPhone和DV拍婚礼、葬礼赚外快。后来我拿出了一些中国的经验,到处贴些小广告,发些传单。结果有很多人找我拍,最奇葩的有一次有个人说:你能不能帮我拍我老婆生孩子?
那时我一直在纠结到底是不是该去拍商业片。后来证明,拍《德兰》这个决定是对的,要不我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那样的人、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
《德兰》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剧本,角色又离我自己的生活非常远,我就想能不能体验一下生活。在去年年初,我就跟着剧组去了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先坐早班机从北京飞到昆明,下午转机到香格里拉,住一夜。第二天早上开10小时的车,翻两座雪山才到。我在那跟着一个选角副导演体验了一个月的生活。他常常去每个村选演员,我就去村民家种个地什么的。
有一次我跟着山民上山采药材,顺着溪流,没有路,用棍子把很高的草拨开往前走。到了山顶,突然眼前一片开阔,特别的亮。你看着所有都是高山,但是高山都比你矮,那大概是5、6点钟,有点夕阳,天上半边红,半边蓝,在山上大面喊,我觉得挺好。
进组后,我演的第一场戏是在山路上,坐着一个拖拉机慢慢走。我记得全是平行的山,云压得低低的。透不出光,但是走一会,又会透出一道光打到你的脸上。我就看着远方,一直这样,都不知道他们在没在拍。
但我突然一想,村民们每天面对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感觉?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就是他们一辈子。我突然就有些奇怪的感触。
那时候也很苦。我穿了一个白T恤,里面全是跳蚤咬的红包,特别像奥特曼身上那个“滴滴滴”发亮的红灯。后来我们又住睡袋,躺在袋里,你总感觉到自己身上“怦怦怦”不停地有东西在跳、蹦,我像块跳跳糖一样慢慢融化。早上的时候,脸很痒,一拍,看到两个跳蚤,一下子就跳飞了,打都打不死。
刘杰导演当时让我去村里找人,学他们的生活习惯、走路的姿势、耸肩的感觉、说话的习惯和节奏。云南话腔调也奇怪,我就先跟我们的女主演德姬——她是四川阿坝那边的藏族人——学四川话,再转音。导演还给我捋了一个云南话版的角色小传,诸如“我妈妈在我6岁的时候就死掉了,我7岁就跟我爸爸一起生活,我13岁的时候跟奶奶一家”,如何如何。我就不停地念,让它催眠我。
演戏的时候,我有时有点崩不住了,但要克制。我知道我的“绷不住”,是来自“小董”这个第三者产生的同情,而“小王”不会这样。刚开始,导演只跟我说了一点剧情:你爸爸失踪了,你要找你爸。过了几天,他又说:有个藏族女孩跟你一起去,你就跟她产生感情了,又发现有问题。就这样,我一点一点进入角色。
我习惯于从角色中找到自己心底的那一部分,把它放大。演片中的“小王”,其实也是在演自己的体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进藏民家,也三个月没有澡洗,就穿着那一套衣服,味道都酸了。要有人欺负我,我说咱俩拥抱一个,他们就吓跑了。藏民的屋里很昏暗,有天窗的地方又特别亮;他们吃糌粑,喝酥油茶,我开始也不习惯。这些感官上的冲击,都被我用到戏里去了。
小王是个情窦初开的小孩,陷入藏地,也陷入对德兰的爱。他想的就是:我要为她付出一切,想带她走,给她她想要的。这并不难理解。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同学谈恋爱,特别逗。他害羞,就一个人在那儿笑,我说你笑什么呢?他说我在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字——你懂这种感觉吧?最后小王含痛离开,那是以为自己很高尚、很伟大的离开。如果我是小王,可能还没他坚强。
有一场戏,是我不小心看到德兰和那个男的做爱。演之前,导演跟我说了他第一次的经历,说到那会儿呼吸急促,满眼又红的感觉。结果我演着演着就开始崩溃,大哭,哭了两分多钟,一边哭一边假装摔打东西,希望他们能发现我在这。那完全是即兴的。那条大概7分多钟,拍两条过了。看剧本的时候,我可能会分析;真正演的时候,我会这样去做减法。
这次,刘杰导演会跟我说得更多了,他开始拿我当演员了,之前拍《青春派》的时候,只是把我当作一个高中生。从我的角度来说,每个导演给予的帮助很大,也都会改变我。刘杰导演则是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没有他,那中国可能少了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哈哈!
拍完了《德兰》,我终于接受了自己的演员身份。现在我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跟导演合作,我挺阴魂不散的,导演开会我跟着,跟摄影师、灯光师、编剧都要聊天,积极起来。因为我决定要回国来做电了,想开个电影公司,演几部好的戏,想学写剧本、做导演。不过,如果我明天想开饭馆,可能我就开饭馆去了。生活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什么“一辈子要完成的心愿”,对我来说,不刺激。
我做演员这些年 我做老北京这辈子
从去年到今年,我前前后后演了《德兰》《少年巴比伦》《少年班》《山河故人》《六弄咖啡馆》五个电影,基本没休息,现在一直在修复元气。有时候演戏会让你有点迷失。有人说,演多了就好了,可以演各种各样的角色,面对镜头更轻松。但是我不觉得。我需要对镜头的敬畏感、紧张感,才可以更好的去诠释。我希望自己拍每部戏的时候,都像拍第一部戏一样,有非常好的初衷。
《山河故人》中的张到乐(Dollar)是生活在澳洲的少年,《少年巴比伦》的路小路则在中国内地小城。这两个角色还真有很多相同点,比如他们都生活在被选择的人生里。不一样的是,路小路最后去追逐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张到乐是无奈的,他觉得自己非常卑微,他也不知道身上这把钥匙,还能不能回去再打开他记忆中的那扇门。生活在上世纪的路小路,更像一个时代倒塌的见证者。而活在2025年的张到乐更像一个对未来的预言。
现在想起来,《青春派》里的居然,算是最接近我本人的一个角色。不过你要是当时问我是不是本色演出,我会说:不是!哈哈,那时候不承认,觉得咱是靠演技的。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偏本色的,作为一个高中生去演高中生。
其实小时候特别想做一个出租车司机,因为小时候不爱说话,这些师傅特能聊,我特别羡慕,感觉他们什么事都知道。上到国家大事,下到菜价,鸡毛蒜皮,一根葱多少钱,我觉得他们全部都知道。另外我也特想开车。估计有机会,也演演《出租车司机》的续集吧。《李米的猜想》?那是女的,我不行,最多演个《董米的猜想》。
《出租车司机》是我“干爹影片”——所谓“干爹影片”,是我的暗语,指那些对我影响很深的电影。比如《暴雨降至》《地下》《黑猫白猫》《爸爸去出差》,还有美国的《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还有比利·怀尔德的《热情似火》。我的“干爹”嘛,有库斯图里卡,大卫·芬奇,比利·怀尔德,卓别林,老导演太多啦。
冯小刚导演的表演我就特喜欢。他演北京都是有光彩的。我记得,《山河故人》做宣传的时候,有一个香港记者问:“现在的年轻人对故乡没有概念,你对你的故乡有爱吗?”这是什么问题?太国际化了。我对我故乡特别有爱,有很多乡愁,就算它有再多问题,我也觉得这是我的家。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小时候的北京天气挺好的,晚上一抬头全是星星。尤其是秋天是北京最美的一个时节。现在空气变差了,城市变杂了。我记得以前进了城,三环以内基本全是北京人,现在好像都不是北京人了。北京都去哪儿了?北京都被拆迁到五环外了。我就有点莫名的哀伤。陈凯歌导演拍的《百花深处》,那讲的就是这种流失。
我本来就特别怀旧。特别喜欢老物件,老东西,老歌。要是去伦敦、巴黎,我不逛名牌店,也不懂时尚啥的,我就喜欢去那些古着店、二手货店,去淘一些小表啊,小书啊,小玩意儿。买老的那种牛仔裤、老皮衣,很大、很脏。小时候爱听披头士,后来听Eric Clapton的《天堂之泪》(Tears In Heaven),听U2,Bob Marley, Bob Dylan。
说我星二代、拼娘?我没什么好躲避的
我对《少年巴比伦》的情感太深了。其实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它并不是一个“好项目”,也就是说不一定赚钱。如果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我一定只投成本低、演员的粉丝多、剧本又简单的片子。但我对《少巴》,是从最早的第一版剧本跟到最后的第十几版剧本的。它不像现在大家市场上看到的IP,群众基础那么强、情节那么简单。要看懂它,需了解整个时代背景。
我想它放到影院未必卖坐,但大家可能觉得这帮年轻人是认真做电影的,甚至“中国电影的未来电影有希望了”。我们希望把口碑先热起来,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思路,比如去走校园、走工厂、走技校。
这部片投资不高,反正不到三千万吧。我自己片酬没怎么要,能养活自己就够了。如果我拿一千万的片酬,那就意味着制作费少一千万,电影就会少1000万的质量。我投资电影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片酬、参加活动以及真人秀。要是拿别人钱来投,就不可能只投那么点了。现在我还在跟杜蕾斯合作做新媒体活动,反正是尝试,没试过永远不知道,大家就给对方一次机会。
三乐影业是去年我和一位从事广告业的朋友合作建立的,合作模式是我来带资源,他来谈一些商业合作。我希望我们做得都是有品质的电影,不能拿这个当挣钱的工具。现在公司是盈利状态,《捉妖记》的回报很好,加上我们之前投了两个综艺节目,这样就可以用盈利的钱往下滚。如果不做电影,我就不希望再拿自己钱出来了,因为觉得没有意思。
现在还有很多人问我,做星二代是什么样的感觉?小时候被范冰冰姐姐他们捏脸是什么感觉?有人觉得:“这小子发展得好因为他妈是花姐,你说他演戏能不好吗?他肯定认识很多人。”这说得都没错,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拍完《青春派》以后,有个报纸写我,说“拼爹的时代已经过了,现在改拼娘了”,特别大的黑体字标题。我当时特生气,特难受。拍戏前前后后大概半年,我见家里人也就三四面,而且刘杰导演也是无意中碰到我的。当时我想,这个圈子果然像之前想的那么无聊,太龌龊了。后来明白,其实大家都只看到一面,我真的没什么可躲避的。(鲁韵子/文 王远宏/图片 刘嘉奇/视频)
 更多好文请关注【玩儿电影】
更多好文请关注【玩儿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