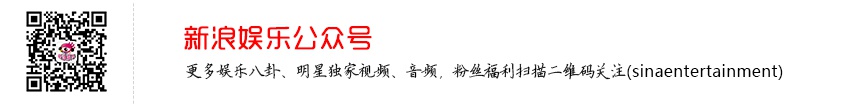文/阿郎
1954年10月23日,台湾屏东潮州,时任花莲师专校长的李升家里,新添了一个大胖小子。按照老辈人的说法,这个孩子属马,其命纳音为砂中金命,流年纳音为长流水。金水相生,运势不错,但琐碎,劳碌。
此时是李升到达台湾的第四个年头,这是他的第三个孩子,另外的一儿一女不得不留在老家江西省德安县乌石门村,一同留下的还有他教育部主任秘书的头衔,一栋五井大宅院,以及开在九江的“恒裕商行”。
1954年,世事如棋,倏忽万变,每个人都如风中飘萍。对于客居他乡的李升来说,这个孩子的出生,使得中国人的随遇而安和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找到了更切实的着力点。李升给儿子起名为安,把他当做长子养。
很多年后,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李安解释说,父亲起的这个名字,一是要后人不要忘了老家德安,一是纪念来台时搭乘的“永安号”货轮。
当时谁都不会料到,这个叫李安的孩子,成了家里最不争气的那一个。他没有做到父亲希望的那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甚至在李安结婚,有了孩子之后,父亲还写信骂他,要他“像个男人一样”。但也正是这个父亲口中的“鬼样子”的李安,成为目前最成功的华人导演。
他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一次金球奖最佳导演,两个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两个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被供奉进世界电影史。他打破了好莱坞对外裔导演绵延了近百年的偏见,也打破了民族、种族的文化界限。他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被誉为“当世界都以为电影已经老去的时候,这部电影则证明,电影刚刚被发明”。
现在,他忙于自己的第14部电影,[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休息],一部“伊战版的[第22条军规]”。
他叫李安,他说他一直是个失败者。
一
小时候的李安在花莲长大,对于花莲,李安的记忆是“很单纯,泥土性很强”。就像很多人对小时候的记忆一样,李安对花莲的记忆也是模糊,甚至是混乱的。
他记得每年过年时候家里要拜祖宗,但他不记得拜祖仪式和随后对父母大人的叩拜,在细节上有什么不同了。他记得每次吃饭时候,气氛都很端庄,因为父亲教导过“食不言,寝不语”。他也记得,父亲还会在吃饭之前告诉他们,“不要把饭都吃光,留一点给内地的哥哥姐姐”。
很多年后,李安总结说,在花莲“接受的是美式自由开放的实验教育”,他像一匹野马,可以随意奔驰,但家里是典型的老式儒家环境,一回到堂屋,他必须按下心思,抚平所有纵横交错的念头和举动。
但作为一个小孩子,李安永远不会做到收放自如天衣无缝,弟弟李岗也说,“哥哥小时候挨揍比较多”。父亲对于长子的期望,从一开始就沉甸甸地压在李安身上,这是他直到现在为止还在心系念念的,每当家里出现了任何大事小情,他的第一反应都是,“我是长子,这个应该由我来”。
和爸爸的严厉不同,妈妈和李安“是一伙儿的”,他最高兴的就是和妈妈去看电影。十岁之前,李安记忆最深的,是和妈妈看了李翰祥的[梁祝],九岁的李安哭得稀里哗啦。
这件事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李安对李翰祥的崇拜绵延至今;二是换来了父亲更大吨位的失望。李升第一次对儿子说出“要像个男人一样”这句话,当时他不会料到,此后,这竟成了他对家中这个长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李安不止一次地承认,“不是个合格的儿子”。从小李安就没有表现出父亲所期望的胸怀和担当,不但不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就连“仁义、好施、慷慨、重诺”都磕磕绊绊。失败的儿子当到十岁,李安又迎来他生命中另一个更失败的身份,学生。
10岁那年,家里搬到台南。“老师都讲闽南话”,而且台南实行的日式教育,李安“上课第二天,就因为数学考不好被打耳光”,“打完还要谢谢老师”。这让李安再一次生出外省人之感,10岁的少年开始学习此后他一直需要学会的融入。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融入一个环境,首先得在学习上占据话语权,而这恰恰是李安作为一个家学渊源的孩子,最感到丢脸的,他的成绩“比糟糕还糟糕”。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失败的学生,李安另一方面的优点开始浮出水面,唱歌、跳舞、书法,他都冠绝全校。但每次放学,他又暗暗企盼,这些要是能反作用在他的科目上,该有多好。
大概每一位天才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撕扯吧,自我与他者的厮杀,要么以向现实缴械而终结,要么以涅槃重生为起点,而每一个这样死里逃生的天才,这一番挣扎最后都成为其赞美诗中的一个特别的注脚,以供旁观者津津乐道,但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这有多凶险,有多煎熬。尤其是16岁之后,他进入了由父亲做校长的台南一中。
李安不止一次地和媒体说起,在台南一中时候,看见父亲时的复杂心情以及他远远避开的举动,听者无不莞尔,李安亦憨厚地笑着。作为成功后的点缀,任何艰苦都有了足够盛大的理由,但少年李安的艰苦,似乎应该更被记取其艰苦本身的意义。
李安说,他至今遭到两个重大的磨难,一是两次高考落榜,第一年差了六分,第二年差了一分,也就在得知第二次高考失利的当天,李安摔了桌上的台灯和课本,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激烈的举动”,其恢弘可以和当年因为在戏剧社里扮演女生被父亲骂,他摔门逃走相并列。第二个磨难就是从纽约大学毕业后,在家赋闲了六年。
这六年仍然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传奇,想想看,一个后来震惊世界影坛的大人物,在毕业后整整六年的时间里,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老婆要下班的时候,就和儿子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回家”,是不是比一部好莱坞电影还要惊险刺激?在一次和朋友闲聊的时候,李安说起那段被人赞叹为“起跳前的下蹲”的六年时间,说“我要是有日本丈夫的气节,早就剖腹自杀了”。
妻子林惠嘉是李安去芝加哥替中华荣工青少棒比赛加油的时候认识的,在关于李安的各种文字里,林惠嘉被誉为奇女子。这个伊利诺大学毕业的生物学博士,比李安酷得多。
大儿子出生,她居然没有通知李安,“第二天我搭飞机赶到伊利诺,医院的人都高兴得鼓起掌来。原来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和亲友,她说不用了,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她感觉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没油的汽车就到医院生孩子去。
二儿子出生时她也赶我走,说你又不能帮忙,又不能生!”李安功成名就后,和妻子去菜市场买菜,有人羡慕“你命真好,先生还可以和你买菜”,她答“是我今天特意抽空陪他买菜的”。
即便酷如林惠嘉,也曾被李安那六年弄得几近崩溃,她打电话和妈妈诉苦,妈妈要她离婚,放下电话,林惠嘉自责“我怎么变成这样子的女人了”。难怪老父亲写信骂他,就连李安自己都丧失了信心,想去学电脑,聊以度日。妻子林惠嘉骂他,“学电脑的人这么多,不在乎你李安一个”。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的“成功与失败永远一步之遥”这种泛酸的话,是大多数人碌碌无为的主要原因吧,起码这句话的光芒折射到了李安身上。他的成名作[推手]是献给父亲的,也是献给妻子的,在影片最后他专门写有郑重鸣谢林惠嘉。这个失败的儿子、丈夫,终于等到了极有可能等不到的这一天。
二
李安的电影被誉为打破了东西方界限,曾有专家为此专门研讨,他跨越种族与文化的藩篱的原因,结论是李安对人的思索是基于人性本身出发的,而人性从来都不曾被时间和空间围剿得手过。
这或许只是一家之言,当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被纳入到大众视野的时候,其解读永远都带着仰视的切入点。
正如[理智与情感]对于英国文化的认知,[与魔鬼共骑]对美国历史的观看,[卧虎藏龙]对于东方文化的审视一样,李安被当做某种符号被放大定格。他不得不在越来越盛大的洪流中起伏。所以他说“我可以处理电影,但我无法掌握现实。面对现实人生,我经常束手无策,只有用梦境去解脫我的挫败感。我对电影的憧憬,正是我心蠢动的根源”。
换句话说,李安的成功正在于他对自己失败的直视。
李安的电影一直没有走出他的少年阴影,他在[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中探讨的是两代的隔阂,所以,他把这三部电影命名为父亲三部曲。他借着电影怯生生地和这个以父亲为代表的世界讲和,他试着去理解,去沟通,去勇敢地到父亲面前大马金刀地坐下来。
但他到底还是那个在花莲疯跑完了,在进入堂屋之前,先整理了衣服的孩子。对父亲的敬畏,是他探寻那些他所不知道的世界的缘由。父亲高大的背影一直出现在他的每一部电影中,在这样的背影的笼罩下,长大了的李安依然背负了那个小小的李安的全部,努力地和每一个风车战斗,希望得到来自父亲的认可。
他说,从[绿巨人]开始,他走了出来,但这也是迄今为止他不甚成功的作品。在影片巨大的投入产出的压力面前,最后还是父亲对他说,“要是不行,你还是回来当老师吧”。
在父亲面前的失败,造就了李安的成功。李安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像是他的自传。片中pi的父母去世,他没机会见到父母最后一面,只能对着大海喊,“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李安也借这部电影向父亲说感谢和对不起。
父亲李升在2004年过世,当时李安正在拍摄[断背山],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他连夜回家,在机场,接到弟弟的电话,他隔着电话和父亲说话,但再也没有听到父亲说话,再也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他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说李安的电影都在写父亲,有些言过其实,但李安的每一部电影的确都带着父亲的气息,[卧虎藏龙]时,他听取了父亲“用力不要太深,着色不要太重”的劝告,拍摄出了中国人所独有的冲虚空灵的禅意。[断背山]拍摄之前,父亲鼓励他“等你拍到五十岁,应该可以得奥斯卡 ”,他说“没有这句话,我可能坚持不下去” ,但李安很少和人提及的是,父亲紧接着说的是,“到时你就退休,去教书”。
[色·戒]的时候,较真较到死心眼地步的李安濒临崩溃,在法罗岛见到伯格曼,抱着老爷子大哭,这个被李安称作精神之父的男人再次挽救了他。李安回到上海,完成了[色·戒]。
李安用电影去向父亲求和,去获得那句他从小就一直梦想的来自父亲的首肯。他用电影和父亲沟通,也用电影去寻找父亲的精神,现在他知道了,父亲是他的一个结果,但更多的是他的原因。因果相生,如金水循环。
除了两代的隔阂,李安在他的电影中一直在做的,就是在探讨不同文化的共通之处。这是他的电影可以穿透种族的天然壁垒,并最终获得世界范围内应和的原因。其实,这也是他从小就不得不去做的。
李安出生于花莲,相对于父亲的漂泊来台,算得上土生土长。可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下,他的出生地只是他的一个眷村,他和父亲一样,生活在当地人的故乡里。加上10岁时迁移至台南,小小少年就不得不在两种以上的文化漩涡中,寻找他的立足点。
少年时候,他是台湾的外省人,硕士毕业后,他是对于纽约来说更遥远的异乡客,他的前半生,一直在故乡之外颠沛流离。
他永远是一个失败的异乡人,找不到工作的李安甚至去到剧组打杂,具体工作就是在拍摄时去拦阻围观,生性温和的李安,被一个非裔女人指着鼻子,“再挡,就揍你”,吓得跑开,一下午都不敢出现。李安的电影一直以中国人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拦人,去做有效沟通,他发现了那些篆刻在石碑上的字。
所以,他的电影都隐忍,就像[断背山]探讨的禁忌之爱那样,隐忍着,但也如儒家水滴石穿的坚韧那样,坚持着。和李安合作过的人都说,李安在艺术上和为人上完全是两个人,在电影面前,他寸步不让,在平时的生活里,他温和腼腆。
还有人比李安更失败的人吗?在父权和异乡长大的孩子,对人情世故总是理解得特别深刻,他必须学会很多,才可以保证自己在一个个他不慎闯入的世界里求得安全。他在台南的要做的,其实就是他在纽约要做的,也是他的电影一直在做的。
还有比李安更成功的华语电影人吗?他的成功就在于他对自己失败的坦诚相见,他从不企图用后来的成功去涂抹之前的失败,以供书写者去制造一个天赋异禀的佛陀,他不需要供奉,经历过排斥和拒绝的孩子对平等和博爱的需求,远大于这几个字的表面意义。
所以,电影是他的入口,也是出口。就在不久前,再次聊起那部[色·戒],他承认,“其实王佳芝很像我,邝裕民身上也有我的影子,那个,那个……我也有点像易先生”,台下哄堂大笑。除了拍电影,他一无长物,“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呆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
他喜欢在电影里把人逼上绝路,就像[色·戒]里绷紧的易先生,他总是把恶塑造得更恶,但他的恶之花总是汁液淋漓、羞惭鲜妍。电影里有现实中的他,也有他自己愿望中的他,如李慕白,如绿巨人。
李安永远记得父亲教他写毛笔字,“写字要回锋,走到尽头时要回来,要圆润才完整、好看”。李安做人如写字,做电影也如写字。
李安新片[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休息],2016年11月11日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