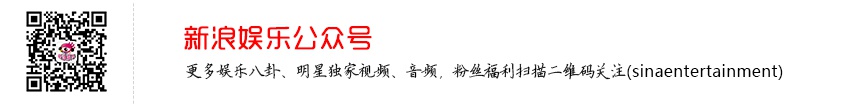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才子杨树口吐莲花,瞬间即可折服一些老板,也瞬间折服一些姑娘。”
这是高群书对杨树鹏的评价。初见时,46岁的他和24岁的欧豪并排坐在桌前,他对比着两人的青春:“就像所有的街头少年一样打打杀杀,殊不知我们都幸存下来了,然后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很怕事的中年人。”
 少年
少年可骨子里的叛逆改不了。在《匹夫》遭受争议的四年后,杨树鹏又拍出了《少年》,在“重工业”大片《长城》与华丽黑帮年代戏《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夹击之下,这部成本不高的青春犯罪片似乎从片名就注定了结局:5%的排片和刚过千万的票房,再青春莽撞也抵不过电影市场这个“成人世界”定下的残酷秩序。
少年对成人世界的一次入侵
伴随着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咏叹调,一个男人把车慢慢倒回去,然后杀了一个人。
这是杨树鹏拍《少年》时涌现的第一个灵感。欧豪和郭姝彤的组合难免让观众留下“这是青春片”的印象,然而看过的人往往会被其中的血腥、阴暗与残酷吓到。反转是电影的关键词,看起来是一个坏小子叛逆捣蛋的故事,但成人世界建立起的规则与正义感,随着剧情的递进,被少年黑客为爱复仇的利刃迅速撕破。
 《少年》剧照
《少年》剧照逻辑性似乎永远不是杨树鹏电影里想要强调的,正如他讨厌蒙德里安的色块,而偏爱神经质的卢西安·弗洛伊德。在《少年》中,欧豪饰演的苏昂近乎惊人的设局能力,以及“色诱”郭晓冬饰演的变态艺术家的手法,细想禁不起推敲,但影片呈现出的力量感与不加伪饰的冲突张力令人着迷。
郭晓冬和余男畸形的夫妻关系,张译和刘天佐作为警察的疲于奔命,让欧豪郭姝彤这对少年伴侣之间的纯真感情,仿佛黑夜中蹿出的一缕烟火,搅动着他人一潭死水般的生活。“我把内心里最纯真的一面寄托在了欧豪身上,而把阴暗的部分放到了郭晓冬身上,”杨树鹏坦言。
在他的诗集《我买下的绝望地》里,杨树鹏回忆起自己生长的地方盛产无所事事的街头少年,街头经常扬起一阵尘土,一帮少年就滚打起来,再一会儿就有一个血人冲出来,“一切都乱哄哄的没有来由”,这些鲜活的记忆也许都被他拍进了《少年》里。
 杨树鹏
杨树鹏他自己的经历也充满传奇。初中毕业的问题少年,15岁改年龄加入消防大队,后作为编导和崔永元一起,把《实话实说》和《电影传奇》做成了央视王牌节目。
“他们很厌憎我不踏实在自己工作岗位上,每天写写画画想入非非的状态,我也很厌憎他们蝇营狗苟被体制修剪成一个豆腐块的样子。”享受着暴烈青春的杨树鹏,一边打架一边读着《百年孤独》,这让很多人无法把他同时和混混与诗人联系到一起,正如现在人们不能理解他身上怎能兼具成年人的圆滑与少年的叛逆。
从《烽火》、《我的唐朝兄弟》到《匹夫》,杨树鹏的每一部电影都争议颇多,有人说他是天才,也有人认为其过于自我,“太忙于表达才华而把电影给忘了”。
 《我的唐朝兄弟》
《我的唐朝兄弟》尽管如此,杨树鹏执导的几部电影作品,背后出品方星美、上影以及光线均是业内赫赫有名的公司,他所有的电影票房都谈不上亮眼,却总有人愿意为其买单,是大佬们纷纷看走眼么?
“国内的环境和资源都复杂,有的导演作品卖,有的导演作品不卖,这里面因素太多了,”《少年》的制作人张思阳感叹。首次主投主控一部电影,在电影行业也是“少年”的腾讯影业显然还需要积累经验。张思阳仍坚信杨树鹏是非常好的内容创作者,“之前的作品《烽火》、《唐朝兄弟》也都很靠谱,《匹夫》争议蛮大,但其实项目有很多细节都不被了解,不怪导演的。”
撇开作品不谈,在人际交往上杨树鹏确实是个妙人。据说当初拍《匹夫》,他用一顿饭就搞定了黄晓明,两人一见如故。王长田觉得自己与杨树鹏心有灵犀一点通,“刚想抽空去买笔,他就送来了”。他甚至把与张歆艺的离婚声明写成了一封情书,分手了也“请继续相信爱情”。
“反正他人挺好的,说话从来不大声,就算着急骂人也是不大声,特别可爱。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导演在现场发脾气,但剧组里没人讨厌他。”欧豪说杨树鹏给他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去他那儿喝茶,译哥也在,大家就聊一下角色和故事,越聊越high。”
放弃暧昧,往类型化的路子上再扎深一点
《匹夫》过后,杨树鹏沉寂了四年。他告诉小娱,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作为创作者如何面对电影市场的巨变。更多的机遇和诱惑摆在眼前,最终杨树鹏选择了腾讯,因为他觉得传统影业已逐渐形成大佬风格,“一帮业内的高级别从业人员坐在一起,商定一个中年而保守的项目”,相比之下腾讯更年轻,“做东西有诚意,而不是光用他们的钱和团队来振晕你”。
 匹夫
匹夫杨树鹏也在尝试改变。“《少年》拍到第15天的时候,我就说你看,到现在为止我连一个有风格的镜头还没有拍过!”说这话时,他的语气耐人寻味。他坚信一部影片的风格就是导演描绘世界的笔触,和看待世界的方法,每个人都追求极致化的表达;但他同时也逐渐意识到,电影是一场昂贵的游戏,太强烈的风格会让观众无所适从。
“我对电影的文学性要求过高,导致影片中有很多含混、暧昧、说不清楚的片段,这些对于阅读通俗影片的观众来说是不对的。”杨树鹏反思道,“电影一定要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文学性,而不能被它影响,你看塔可夫斯基从来没在电影里念诗,但充盈饱满的诗性从里面喷薄而出。”
《少年》这个项目,让杨树鹏往类型化的方向上走得更远。“这次我们还真的希望能够在青春犯罪片这个亚类型上有一点开拓,毕竟青春片从2013年小欧演的《左耳》开始进入到勃兴的状态,今年已经是又快向下滑落的类型,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在好莱坞,青春性喜剧、青春恐怖片、青春科幻片一抓一大把,但在对青春缺乏想象的中国电影市场,青春片似乎总要和校园、三角恋和堕胎勾连在一起。
以原剧本《梅雨时节》为基础,杨树鹏发展出的《少年》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来日无多的黑客,为帮女朋友报十年之仇借刀杀人。选中欧豪是因为杨树鹏觉得他身上的黑暗气质与角色分外契合,倔强能打,想要挑战秩序,做事不给自己留余地。
 《少年》
《少年》“你不觉得很多时候成年人想要压制少年么?”戏外的欧豪,活脱脱也还是戏中那个话不多但语出惊人的少年,“他们总觉得你们是小屁孩,我们说什么都是对的,但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意识到自己说的到底对不对。少年会容易去反抗,因为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少年总有一天也会步入成年?”
“所以我们在设定上其实是限制死了。”杨树鹏抢先指着欧豪笑道,“(在片中)他没有成年了,所以才敢这样想这件事情。”
“我在我的少年时代,他在他的少年时代都是一样,打打杀杀的。”与仍未走出叛逆期的欧豪像比,46岁的杨树鹏是一个矛盾体,尽管他形容自己为唯唯诺诺的中年人,套上了压抑、掩饰、隐忍这些成年人惯有的保护壳,会巧妙掩饰生活中的一些本质,但孩子气是所有才华横溢者无法抹去的印记。
比如谈到审查,他明显抬高了声调,“他们(指审查机构)老当真!这点特吓人。而且咱们国家真事那么多。。。。。”随即欲言又止,“算了我还是别讲了,不然他们又说,哎呀你怎么说话没个把门儿的!”
对欧豪,他夸奖之余带着几分羡慕:“小欧还在他的青春期,可以张扬地纹身、喝酒、犯错误。可能我们就不行了,晚上出去看见街上人多都害怕,成年人的责任感越来越多,时常假装去理解别人,心理默默骂对方傻逼。”
纺锤形的电影市场,离我们还有多远?
平衡个人风格与市场需求对于每位才子型导演而言,都是一道需要迈过的坎儿。“我们很多人都在困惑,”杨树鹏说,“也有的人不困惑,比如说就是拍一部商业大制作,他完全隐藏了他自己,没有自我。”
他说的也许是已经功成名就不需要电影为自己正名的张艺谋。刚刚过去的周末,《长城》以接近6亿的票房对同档期的其他电影形成碾压之势。大制作、大卡司、高排片,没有什么理由让国师不笑到最后。
 《长城》
《长城》在坚持风格的导演里,程耳算是一个。“程耳依旧是我的菜!上映去看第三遍。”《罗曼蒂克消亡史》首映后,曾为导演程耳监制过《边境风云》的宁浩在朋友圈力挺。
《罗曼蒂克消亡史》乍一看去,很像是杨树鹏口中那些传统影视大佬们拍脑门敲定的片子:葛优、章子怡领衔的国内最顶级明星阵容,美学风格成熟,导演功力深厚,甚至缅怀逝去时代的主题,也有显得些老生常谈。
然而这部电影的文学质感让你很难去把它对比以往套路化的年代戏。不断的倒叙和插叙延续了程耳过去令人惊艳的叙事节奏,观众在碎片化的故事中逐渐勾勒出一个旧上海应有的样子,它就藏在葛优的帽檐下,章子怡的颦笑间,甚至是倪大红喝粥的气势里,优雅、不紧不慢,又透着注定曲终人散的惆怅和伤感。
尽管不断被人说像《教父》、《布达佩斯大饭店》、《美国往事》甚至黑帮版的《花样年华》,《罗曼蒂克》依然是一部非常特别的片子。露骨的调情与床戏,几近残酷的枪杀儿童的场面,个性鲜活的众生隐没在大时代的动荡里,程耳以他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叙事结构,将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释放。
 《罗曼蒂克消亡史》
《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杨树鹏一样,程耳导演的名号前常被冠以“才子”的称谓,这在一个以票房论成败的电影市场,似乎难免成为了“叫好不叫座”的代名词。在一场面向媒体的点映结束后,有人表示了对《罗曼蒂克》市场前景的担忧,更有人直言此片会像《一步之遥》一样难被观众接受。
面对这样的问题,程耳有所迟疑。“我觉得不用做特别具体的比较,这两部片子太不一样了。”而华谊兄弟影业副总经理柳庆庆则接过话筒代为回答,他把《罗曼蒂克》归类为“更有电影质感、更具开创性”的电影:“人们对于《一步之遥》的高期待,更多是基于对《让子弹飞》的印象,我们会在预告片、音乐等方面更准确地传递《罗曼蒂克》这部片子应有的气质。”
口碑成了面对市场反应的挡箭牌。当《长城》的宣传方在朋友圈秀票房过亿的海报时,《少年》和《罗曼蒂克》的出品方们则在收集知名电影人和影评人的背书。
 《少年》
《少年》乐观来想,正如从没人看到王家卫坐上票房冠军的位置,但他依然被人们尊为电影大师一样,杨树鹏、程耳、徐浩峰们的明天也会是在电影殿堂而非票房排行榜。但有时又忍不住悲观,再有情怀的电影公司也不会把拍电影当慈善,当资本热钱涌向别处、才子导演和投资人之间的罗曼蒂克消逝后,所谓“中产阶级电影”、“风格化电影”的形容会不会被矫情自饰、曲高和寡替代?
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是徐浩峰导演爱念叨的一句话,可能才子导演也存在诸如此类的进阶,多数人仍徘徊在自己的优势与局限,真要达到“见众生”的境界,不仅靠导演修为,也需要电影市场和观众都更有耐心一点。
所幸这些人还有诗与远方。徐浩峰那些诡谲而惊艳的武侠小说出了一本又一本,程耳把电影里没说完的故事,放在了电影同名书《罗曼蒂克消亡史》里,而杨树鹏去年刚出了个人文集《在世界遗忘你之前》。
 《罗曼蒂克消亡史》
《罗曼蒂克消亡史》当听到小娱说自己也买了一本时,他惊讶之余默默颔首:“谢谢,我微薄的收入里有你一份。”这部由写成于2007到2013年的短篇合集,比杨树鹏的电影更加天马行空,有寥寥数百字的《离汤》,也有价格100块一夜的《贩梦》,“我能窥见他们的命运,并修改他们的命运,” 这似乎才是文字世界里的杨树鹏更享受的状态。
杨树鹏从未想过要把这些笔端记录的灵感片段拍成电影,“因为确实都不太好拍”,它们不过是电影之外他所热衷的廉价游戏,但依然有不少人追着想要买下版权。“我说他妈的,我都不拍你们来拍?”他笑起来,话头一转,“不过有朋友来买也就很便宜卖了。”
“成年人活在当下,少年人活在未来,”如今的杨树鹏依然很淡定。他说自己一直鼓吹的观点是,电影市场的结构应该是纺锤形。“只有中等级别的影片足够精良和类型化,市场才会正常运转,也不会被大明星卡死。”他也忍不住吐槽,“现在所有人都在问一线明星要档期,即便是我的朋友,也在问我你认识杨幂吗?我说你真的别想了,她都不知道排到哪一年去了。”
(作者/曹乐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