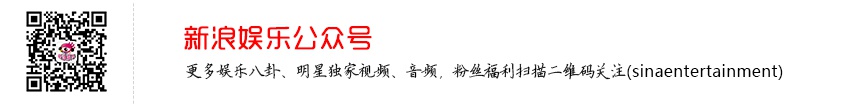新浪娱乐讯 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VR竞赛单元的入围影片里,蔡明亮的《家在兰若寺》显得有些特别。
《家在兰若寺》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讲究视觉奇观或者互动体验的VR电影,尽管有着“蔡明亮首部VR作品”的噱头,这依旧是一部非常蔡明亮的电影:固定机位,凝固的空间,极少的场景。

意大利时间9月9日,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各大奖项揭晓。《家在兰若寺》遗憾没有在首次设立的VR竞赛单元中有所斩获,但蔡导在艺术片领域对VR的探索,依旧是一次勇气可嘉的尝试。
有人说蔡明亮适合拍VR,因为他擅长建构空间,而VR电影能全景式地展现蔡明亮的空间艺术,让观众沉浸其中。对此蔡明亮如何看待?VR对他过往的经验有怎样的挑战?VR有没有改变他的镜头语言和摄影方式?VR电影如何发行?他的废墟美学在VR电影中如何继续推进?
在威尼斯的一个午后,新浪娱乐对话蔡明亮,听听他的VR观。
本文由蔡明亮的回答整理而成。

“VR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媒材,没有一个模式”
其实拍电影没有模式,我的电影更是没有了。我的电影跟一般做电影的人的思考是不一样的,当然我在想讲故事,表达一个清楚的议题,但是我不觉得我要说清楚事情,我要让你感觉到我想表达什么。
所以我的逻辑是非常不同的,你也不需要觉得我是一个标准,别人也不是标准。那VR更是,因为它太新了,所以我觉得我投进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探索,很认真在探索。它就是一个电影创作,电影也有游戏的电影,现在也有商业片,也有很创作性的,VR也是一样。
VR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媒材,电影100多年后发展到这个状况,使用这个方式的时候,你就要去面对它。你不一定要被它拉着走,可是你要面对它。
我拍《家在兰若寺》还是用一个拍电影的概念,我用我的摄影师,我要很标准的打光的方式,我的收音师也是。演员就演吧,不需要说因为VR就变成另外一种表演,只是说可能观看的感觉有点不一样了,表演的面向也变了。
开始是有点不安,怎么样才好看?怎么样的视觉?怎么样的高度?怎么样的距离才不只是清楚还好看?VR不是我们人的眼睛,它是一个机器的眼睛,它会变形。比如这个柱子在我旁边是这样的,可是它在VR里面就变大了变高了。
你不能改变它,你不能说我不要这样,VR目前就发展成这个样子。所以有很多思考在里面,怎么样看起来好看、舒服,你觉得它是真的,它又不是真的;你觉得它有点现实,它其实有点超现实;你觉得它超现实,它又有点真实,这个复杂性很怪。
拍前是有非常多考虑,这种考虑有时候会让你很不安,你知道你拍下去就拍下去了,就是一个作品了,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作品,你不做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很难去谈VR到底该怎么样,就先做了,没有一个模式。

“回到了最早拍35厘米的没有监控器的年代”
用带头显的概念来思考空间和思考声音,是跟你平常看电影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好玩儿,我也觉得很辛苦,很痛苦。因为你想的到但你不能掌握它,目前就是这样。
开始他们给我监控器,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就是变形的一个画面,没有意义。我就说我不看这个监控器。我自己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是没有监控器的,我的那个年代。然后所有的导演都是在摄影机的旁边,要做的工作就是看演员、看气氛、回到这个现场来。
现在拍VR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回到了最早拍35厘米的没有监控器的年代,我觉得那个其实更准确,监控器其实不是太准确。监控器只是一个画面的准确性,但是它某一些氛围还不见得那么准确,反而肉眼看到是最准确的。
VR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它是一个缝接的概念,我们现在用的是24个镜头,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你一下拍了24个画面,你是可以替代的,比如你可以修掉这个画面,用另外一个画面补上去。所以工作人员是可以在画面里面的,我就要求我在那个戏里面,在场景里面看演员表演,我每场戏都看,哪怕最难的位置我都要看,我都要躲在一个地方看演员是怎么样演出。
VR的声音很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思考,比如说我的录音师他们非常认真,他们总觉得VR就是360度,你一转头声音就变了。我不觉得,转头我还是在这里啊,我没有离开太远啊。那做技术的很多思考也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我必须要跟做技术的人做很多沟通,让他也往我这边想一下,我也会往他那边想一下,所以跟以前拍电影完全不同的。

“我的主导性削弱了一点,我必须分一部分思考在观众身上”
VR几乎没有办法处理特写,突然间就没有了我们习惯的构图的概念和景深的思考。所以那个构图,很怪,好像构图落到观众的身上,当然也是导演的身上,他是随时都在构图,所以要思考很多面向,比较多的面向比我以前拍电影麻烦还多。
以前在构图上我的主导性很强,就我想让你看起来就看什么。但现在我发现我的主导性可能要削弱一点,我要想着观众在哪里会比较舒服,我必须要分一部分的思考在观众身上。
当然这次还是我怎么看你怎么看,可是我得去思考这群观众,也许本来就是我的观众,他可能会开始不安分,因为他被告知他是看VR,他进到一个VR世界是可以自由转头的,甚至将来可能发展到可以自由移动身体,都有可能。所以我就必须思考说,我怎么样去面对这种使人家焦躁不安的媒材。
所以这都是在事前要做的考量,拍每一个镜头都已经大概要想好我要在哪里,我镜头要在哪里,也就是观众在哪里的意思。他可以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什么他不需要看的。其实还是一个电影的概念,真的有构图,可是它同时在进行另外一种新的构图。
我的VR跟别的游戏性质的VR是不同的。游戏性质的VR,你看这个楼梯你就可以走上去,我的楼梯他只是一个构图,不能使用。

“VR有一点像剧场,VR是一个人的电影”
我是剧场导演,我不想演员在镜框舞台上做表演,我希望观众可以靠他很近,他可以靠观众很近。VR有一点像是我的这类的剧场思考,演员离观众是很近的,好像演员可以走到台下来演,观众也可以允许走到台上去看的。
我目前的感受就是,VR是一个人的电影,所以你带上头显的时候其实有一种隐秘感、隐私感。你的投入可以再减少一点,但是你的观看变得更多一点,更自由一点。
有点像布雷希特的概念,我看一个戏,这个戏为什么我不投入?因为它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比如西方人看一个评剧,他就觉得有很大的距离,可是他在看的时候,他反而比那种投入的人更容易欣赏到这种剧,这种创作的一些美感。他不是十分的投入,但他被吸引进去。
我觉得VR有这种功能,你进去了,你有很多的怀疑,因为你看到的不是真的,你看到的是一个梦境而已,你看到的是一个被虚拟出来的地方,跟看电影的投入有点不一样。
我希望我的观众看我的电影是比较清醒的,他可以很投入,可是他有时候要稍微理性一点,我不是叫他去判断什么,而是叫他去做思考,为什么这样拍,为什么是这样的表达,不要做一个傻傻的观众,理性的时候你会欣赏到很多那种傻傻的人欣赏不到的东西,那种电影的时间感空间感、电影本来有的特质、电影的美学概念。电影不是只是一个故事,让你哭哭啼啼或者让你开心,我做电影不往那边发展,因为那边很无聊。
VR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的角色是空的,水流过来,可是它没有碰到你。角色这么近的距离,可是他的脸上还是有一些电子的感觉,当然我们这个技术还没有发展到百分之百的清晰。那如果到了百分之百的清晰你会不会很害怕呢?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感觉。可是那个感觉不是真的,我永远觉得电影不是真的。

“找了我这么奇怪的导演,怎么发行呢?”
其实关于电影,我是一直在颠覆很多概念。大家说电影要在电影院看,当然最舒服的是在电影院看,但是有些电影没办法在电影院做商业的操作,那只好找别的平台。如果你老是觉得电影拍完就一定要在电影院看,你就努力去追求电影的规格,所以你没有自由,你没有创作。
我经历过了那个过程,我就很清楚当你做你自己的时候,你要去找你的平台,你要做的很好,要被认同。当被认同的时候,可以在美术馆,可以在很多场合都能做放映的概念,甚至到家庭,到网络,将来都是有可能的。
那VR更有趣,我刚刚说它是一个人的电影,我看那些发展VR的商人,他们的愿景和商机就是在:你最好给我买一台头显。你看大家现在买手机都不手软的,将来年轻一辈的一定是这种人。可是呢,你戴上这个头显时候你看到什么东西还蛮重要的,它一定要很多可能性,也有剧情片,也有艺术片,也有游戏,什么都有。
所以HTC找我来拍VR,就让这个可能性被显现出来。好,找了我这么奇怪的导演,怎么发行呢?他们会去头痛,可是我的感觉是,怎么发行都可以,但是要恰当地去思考,你的内容的属性是什么?像我还蛮适合去美术馆的。
看VR的人心里被告知说你可以自由乱看。可是到了美术馆之后,就被告知这是一个艺术创作,你要认真看,都有一些这种预设的状态。所以我的电影,我的VR很适合去美术馆,做很多实验性的活动。
我们都在讨论VR的商业发行,我觉得非常好玩儿,它可以无所不在,它可以在公车上看,可以在菜市场里面也搞一个VR。VR很新,还没有很恰当的、完全适合的固定的场地,所以我觉得现在玩VR的人可以开始异想天开。
如果它不卖钱的话,可能在电影院演一个礼拜就被片商强迫下片了。也许在一个公车上好了,它就可以演半年,可以演到好几万人都可以看到,可能大家都来排队等公车去看。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改变大家对观影的概念。
“我拍了一个VR,我其实没有改变什么”
我觉得电影不能完全让市场操控着创作,你完全让市场操控,你就没有创作。
那创作者也不能让技术操纵,也不能让科技操纵。你拿到这些东西都是最新的,可是你要随之起舞还是被它拖着走,这个就是我在想的事情。
所以我拍了一个VR,我其实没有改变什么,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而已。你看VR也可以包容我,我也来了威尼斯,很可能我也可以上市场。当然有人不喜欢,那他去喜欢别的,没有关系。
我们最近遇到了一个硅谷来的研究VR的导演,他来看了,看了两次,他评价《家在兰若寺》“是全部拍VR的人都要来看的一个作品”,因为他觉得这个作品开发了他的脑袋,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面向来思考VR,因为这是一个安静的东西。
还有一个国外的导演,看完他说“我真高兴我看完的第一部VR是您的电影,让我觉得我也想拍VR”。因为他听到的VR都是那种商业啦,游戏啦,他那个年龄或者他这种人没有兴趣。他看到我的VR之后,他就觉得好玩儿。
虽然我觉得好玩儿,但是玩得很辛苦。这是一个起步。我觉得也值得。

“给废墟上点妆,我的超现实是手工的”
我习惯拍废墟,尤其这个废墟是在我家旁边,我是在两年多前就开始使用它了。因为身体的关系,我们也不想跑远,不太想出门,但是想创作。我想,这个地方就是我创作的场景。
废墟我觉得是上帝的杰作,废墟长什么样子你不能控制它,通常你被它吸引是因为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吸引你的那个样子。我们这次拍的这个废墟里面有很多空间,每个空间其实是一样的格局,但是它长成不同的感觉,有流浪汉住过啊,留下一些东西,还有植入的生长状态不一样啊,或者是破落的状况不一样,长的每一点都不一样。
我拍电影是这样,我到一个空间,基本上我的美术组跟我的工作都是用眼睛在看,我们在讨论这个地方就是要这样子,不动了,不增加,不减少。所以进到我剧组的人都被告知说不能改变任何东西,包括灰尘。
我利用废墟拍了几个东西了,《郊游》也拍了废墟。后来觉得除了拍它之外,废墟还可以做点什么。不一定只是光拍,把它当做一个事情发生的地方,你还可以在它身上做什么事情。

这几年我的电影创作走向比较手工的概念,更加造型一些。造型不一定是落在人的身上,其实是整个空间,所有的空间都可以做造型。
所以我开始在进行这种创作方式,进到《家在兰若寺》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思考到这个空间可能需要做一些变化,因为我太熟悉了,拍来拍去就这样子。
我想能不能给它上点妆。
最后他们两个醒过来的那个场景,是在废墟里面贴纸做的造型。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八个人,其中有两个是艺术家,我们买了很多宣纸,每一天都贴,有点没有目的性的。贴了大概一个多月,过程里要去烧它,要改变它,要喷水,要弄脏,还要维持它的质感,也改变纸的质感,要风干它等等,最后就做了一个型出来。
那个型会有一种飘忽的感觉,不确定是天堂还是地狱那种概念,可是它是在人间的一个空间。
这个作品让我的创作再往前推了一下,我的超现实是不用电脑的,我的所有的这些视觉是不要电脑的,我都是用手来做的。

“我觉得我大概做了八九成了,先这样子吧”
我对《家在兰若寺》现在还是不够满意,现在还是觉得只做了八成。因为它每一个步骤都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这个步骤是我只有等着看它出来是什么,我只有要求,但是我不能操作,像以前我还可以下去操作。
这次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是互相非常折磨的,因为我盯得很紧,他们也很用功,日以继夜,有人根本不睡觉的,一两个月不回家的也有,但是出来的效果老是觉得不够,不够,不够,就是质感上面,有些东西不能解决。
我是一个讲求画面的人,非常讲究构图画、品质。我来威尼斯之前我看了两个月,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个椅子的角没有弄对。结果在我出国前的一天发现了,我说“这个很严重,如果有人回头呢”,我自己为什么没看到,我觉得应该很少人回头看这个地方,因为大家都被他们两个演员吸引了,那场风雨的戏。你看到要不要改呢?当然要改啊,他们还没改,所以就这样子。
我来威尼斯之前,我觉得我大概做了八九成了,我就接受了,先这样子吧。两年后可能《家在兰若寺》更好看,会变得更有质感。
(杨晋亚/文 宫德辉/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