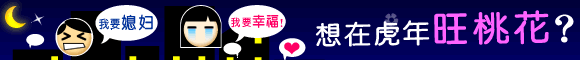王全安团圆在柏林 讲述与余男非一般爱恋(组图)

上一次力夺金熊奖,是与余男合作的《图雅的婚事》。这次再战金熊,两人重聚于柏林,王全安自然感慨万千

王全安或许是中国导演中经历最多彩、活得最妄为的那一位

王全安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前世今生,以及与余男非一般的爱恋
执行/王苗 撰文/许涯男 助理/仲峤 摄影/童梦(STUDIO 6)
化妆/王耀葳(东田造型) 场地/STUDIO 6 封面提供/Brooks Brothers
王全安或许是中国导演中经历最多彩、活得最妄为的那一位。幼时学画,少时跳舞,遍游欧美,与洋妞谈恋爱。异国恋情诱发了他的电影梦,于是他杀了个回马枪,闯进了电影学院。从表演系的捣蛋鬼跃变为中国最超前的导演,历时十年,气哭了无数老师,写了十几个剧本,放弃了N次别人眼中的大好良机,只因“那些东西我不想要”。直至偶遇一个爱才的大款不假思索地扔给他450万元,让他随便拍,他才恣意妄为,大显身手,捣鼓出了至今都在影迷心中引为惊才异数的《月蚀》。
《月蚀》也是王全安与余男的月老,是他俩的处女导与处女演。此后十年,两人的生命紧紧相连,一起爱,一起梦,联袂拍出《惊蛰》《图雅的婚事》《纺织姑娘》。几部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无数,导演与其“御用女演员”双双杀入全球视线,像极了当年的张艺谋与巩俐。“张巩”后来分了,原因众说纷纭,“王余”后来也分了,两人不予回应。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又将二人牵到了一起,余男是评委,王全安的新作《团圆》是竞赛片。再重逢,不在片场,却在赛场。此《团圆》非彼“团圆”,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
只有当事人最有发言权,且听王全安藉由《精品》首次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前世今生,以及与余男非一般的爱恋。
再见马晓晴,方知20年
记者:《团圆》这部电影里有多年未曾演出的马晓晴,怎么找到她的?
王全安(以下简称王):我和马晓晴其实很有缘分,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我就在《北京你早》里演了她的男朋友。此后一隔20年没见。刚好《团圆》这部戏里有“大女儿”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在生活中颇遭压力,婚姻不幸,整个人有点儿神经脆弱。
记者:马晓晴后来似乎也有点儿这种特质?
王:对。她性格很鲜明,也有点儿敏感脆弱,个人状态非常适合这个角色,甚至特别能发挥自身特性。我俩一见面,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全安我是不是老了?我说你一点儿也不老,正合适。她说我一定演得让你出乎意料。她确实做到了。
记者:20年后再相逢,尤其是看到现在的马晓晴,是否很有感触?
王:我真是感触颇深。我看不见自己的变化,但见到她,多少能感受到时间过去了多久,感觉她确实经历了很多事情。我觉得她现在的状态还好,她在上海生活得比在北京好。当初演《北京你早》那时候,她说着一口京片子,我完全以为她是北京人。这次一打电话,她说的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她告诉我,“我本来就是上海人啊!”我想这才是她本来的样子吧,没必要刻意去做某种人。
没读万卷书,行了万里路
记者:你当年怎么就从一个爱画画的孩子变成歌舞团的演员了?
王:小时候的确爱画画,上小学时,全年级的黑板报都被我一个人承包了,人家一到点都去上课了,就我站在梯子上画画。后来延安歌舞团来学校招生,家里人想让我去,因为这份工作挺不错,而且还不用上山下乡。但我一进歌舞团,上山下乡运动也就结束了。但我没后悔,觉得挺好的,因为终于可以离家了,自由了,上路了。少男少女们情窦初开,在一起很欢喜,蹦蹦跳跳,天天与音乐为伴,所以我没有接受过太多应试教育,应试教育里有意思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多,所以我接受的无效教育比较少。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没读万卷书,但行了万里路。
记者:那时候你就已经不停地随团演出、周游世界了?
王:回头想想,我在那样的年代的出国经验,其实令自己开了一个大窍。最初是在1983年,同龄人都想考舞蹈学院,我也有条件和机会,但冥冥之中又觉得更该把该出的国出完,上学还可以晚两年。所以那两三年一直在外面跑。那段经历对我后来的人生状态有着很大影响,首先是自由自在,另外对不同世界的人,生生就那么接触上了,所以我很早就习惯了所谓的差异。先跑了中国香港、日本等亚洲区域,然后跑欧洲。西欧、北欧几乎跑遍了,在法国呆的时间最长,整整半年。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完全没有独自行动的能力,人家老外都是成年人。那时候对外部世界还是很恐慌,第一次出访前,还被进行了防策反教育,怕被演化成间谍了。
法国女朋友,触动电影梦
记者:后来怎么又不跳舞、不游荡了?怎么又转向电影世界去了?
王:其实想拍电影,源于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当时我在法国,正跟一个法国姑娘谈恋爱呢,她是苏联代表队的陪同。组织上原本是不同意谈恋爱这样的事情的,但这次领导却有点儿高兴,因为当时正跟苏联对抗呢,领导觉得我有点儿为国立功的意思。那个法国姑娘问我有没有看过《老枪》这部电影?我说没看过。她告诉我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就带我去真实的发生地玩儿。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下午,欧洲的阳光很明亮,她谈起电影时的那种眉飞色舞令我很有触动,我就觉得这一生应该去拍电影。马上付诸行动。她帮我联系里昂电影学院,进展很顺利,可等到就要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将来拍什么?你肯定变不成法国人,拍不过法国人。你在人家这儿呆着,中国变化那么快,几年后你再回去,就彻底断线了,就该整不明白了。于是我马上决定还是应该在国内解决电影问题。
当时只有电影学院跟电影有直接关系,但我读书不多,如果考别的系,文化课就有点儿吃力。我当时的心态就是进去为先。现在想想,当时能有考学的想法,在理论上几乎不可能。因为你已经在团里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人家培养了你,你却去考电影学院,等于隔了行啊,完全不允许。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同时报考舞蹈学院。当时是舞蹈学院编导系首次招生,全国只录取8个,我考上了。我拿着通知书又去考电影学院,也考上了。
当时还有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怎么把档案从单位发到电影学院。有一天我刚好从管档案的那个人家门前经过,发现门开着,屋里没人。我就偷偷溜了进去,竟然看见一个孤零零的档案袋放在桌上,上面正写着我的名字。我就拿走了,带到电影学院。学院很吃惊,问你个人怎么能把档案带过来?我瞎编说,这正说明了组织上对我的绝对信任。
不怕钱不来,只要活儿够好
记者:真是胆大包天,做事几乎不考虑后果。不过话说回来,不这样做也就没门儿了。
王:入校一年后,对环境很失望,很不满足,于是几乎把所有老师都气哭了。其实是要表达不满——干嘛非要把简单的东西讲得那么大费周折?第二年,排练演出片段,可老演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不过瘾,就自己编了一段儿,还骗老师说是小说片段,名叫《通风的小屋》。每演一次,同学们都哭成一片,因为它更能触动同龄人,后来甚至成了学校的演出剧目。我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有力量,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班的同学作业大都是我编的。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上课,上艺术史课、上导演课,旷掉很多规定课去上。每学期我都先计算好能旷的次数,好像是30堂吧,不至于被开除,但要被记大过,所以我每学期都会挨处分,每次去签字,别人都哭成一片,就我高兴。
记者:你一毕业怎么就回西安去了?大多数想搞电影的不都混在北京吗?
王:我想回西影写剧本,想弄自己的东西。西安能够容忍闲人,在北京都非要干点儿什么似的。我一口气写了10个剧本,期间把该看的书重新通读一遍。一直写到第13个剧本,5年也就过来了,中间也有拍戏的机会,但都没弄成,因为都不是我想弄的电影。
直到第五个年头,单位改制,不发工资了,你还得交劳务费,生活无以为继。我记得那时候把西影厂门口的饭馆都欠遍了,出去都得乔装打扮。后来厂里也组织过年轻人拍电影,但我一看还不是自己想要的。我就想自己拍。刚好我半年前在北京的一个酒会上认识了一个哥们儿,我俩都不爱往人堆里钻,就站在门口抽烟、瞎聊。他问我拍电影能挣钱吗?我说没戏。他又问我,那拍一个好电影有没有可能?我说这还有点儿戏。他说那好,想拍电影你就来找我。半年后我找到他,弄了几个故事,其中一个就是《月蚀》,这哥们儿10天后就把5万块钱剧本费打过来了,在当时算很高了。我跟这哥们儿后来来往并不多,他是做房地产的,做得很出色,挣钱很多。生意之外,他更想做点儿凭直觉的事情,也想帮直觉上觉得不错的人。他说他就是这么过来的,关键时刻被人帮过,于是每年都拿出钱来做同样的事。当时我说你给我300来万就能拍了,他说你说300万,我就给你600万,最后我说那就450万吧,再多也就不对劲了。就这样,我拍了自己的第一部戏。
记者: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王:所以我老说我是个落网分子,游离在人群之外。毕业时,同学们都拿着本子到处找投资,几年下来千疮百孔,搞得很沧桑。我从没想过那么做。我觉得永远有人拿钱拍电影,问题在于你是否独特,是否真够好。真要活儿好,钱自然会找你。
真爱一个人,那就放手吧
记者:《月蚀》也是你和余男的月老,此后你俩相伴10年,但在外人看来最辉煌、最默契的时候却骤然分手了,问题出在谁身上?
王:其实在遇到余男之前,我的生活一直很随意,甚至很混乱。遇到余男,劫数来了,冤家来了。我跟她在一起的10年,过得比较简单,也需要这种简单。我们共同营造了一个相对单纯的拍电影和生活的环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点儿自给自足的意思。那种氛围挺棒的。但当事情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无论是电影还是生活都需要拓展。其实我一直对她有所愧疚,她跟我好的时候,很小,这么多年下来,有些东西是我不能给的。我可以给她电影和经验,但属于她自己的人生和阅历,我没法儿给。所以分开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不得已,我俩都很清醒。我妈都说,你们把人生中最好的时光都给了对方,你俩都问心无愧。
记者:其实有种不执著、想让对方更能自由飞翔的心态?
王:对。所以我觉得我俩的关系超乎一般的两个人。其实所谓分开,也是对对方的一种给予。真爱一个人,那就放手吧。从心底讲,我觉得余男值得尊重。她这种性格的人,适合当最好的演员。她有信念,也有障碍。她不是那种自以为无所不能、钢筋铁骨、永不会被伤害的演员。感人的角色永不会属于那样的演员。而当你看到图雅,还是能把她和余男个人的执著联系到一起,她能够让你相信这个角色。
记者:你看过分手后余男接演的别的导演的电影吗?
王:说实话,都没看。因为我知道那些电影是什么类型,我也明白她的想法。她想拓展自己,但在那样的领域里,对演员的表演来讲,探索度和饱满度相对都会弱,但并不妨碍她尝试不同领域的愿望。
分开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不得已,我俩都很清醒。我妈都说,你们把人生中最好的时光都给了对方,你俩都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