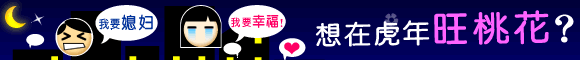王全安:我从未处心积虑拍过一部电影(图)

45岁的王全安属于大龄第六代导演之列,至今只拍了5部影片,却几乎每一部都受到柏林电影节的青睐

王全安的《团圆》不仅成为此次柏林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还最终拿下最佳编剧银熊奖
柏林电影节向来青睐王全安。继三年前凭借《图雅的婚事》拿到金熊奖后,今年王全安的《团员》不仅成为此次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还最终拿下最佳编剧银熊奖。不过,在王全安看来,这些得奖作品,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真正想拍的电影做准备。
文 / 李俊 摄影 / 秦斌
嗓子哑了。和3年前《图雅的婚事》在柏林电影节拿到金熊奖一样,经历了疲劳、亢奋的电影大战之后,导演王全安感冒了。
影片《团圆》是第60届柏林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并最终获得最佳编剧银熊奖。王全安第二天就回到北京,没安排通宵庆功宴,也没了当年的那股兴奋劲儿。“回国了,就要回到各自的岗位上。”他引用了张艺谋的这句话。
在北京公寓的柜子里,摆着当年的那支金熊奖杯。回到家,王全安专门把它翻出来,左手一支“金熊”,右手一支“银熊”,掂量了一下,重量都差不多。他开玩笑地说:“可以用来当哑铃健身。不过,这可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对哑铃了!”
在中国,同样拥有这样一对金银“熊哑铃”的人,是张艺谋(参赛作分别是《红高粱》和《我的父亲母亲》)。今年,两个不同时代、风格迥异的陕西籍导演被摆在柏林电影节的大擂台上,最终王全安胜出。
45岁的王全安,崛起于最近10年,属于大龄第六代导演之列。从2000年的《月蚀》至今,他只拍摄了5部影片,几乎每一部都受到柏林电影节的亲睐。国外媒体认为,王安全一直聚焦中国当代的困境,是具有独特自我风格的新一代中国导演。
“我还从没处心积虑拍过一部电影。”这个生于红色延安的西北汉子很自信,认为前两部拿奖作品,都只是小试牛刀而已。
“现在我很振奋。我终于用了10年时间,想明白了一些问题,也证明了自己的电影观是正确的。”接下来,王全安要赶紧去拍自己真正想拍的电影。
“认识余男之前,我就是一个混蛋”
柏林电影节组委会打来电话,通知《团圆》入围今年电影节的竞赛单元。当时,王全安正在比利时参加达内兄弟为他举行的一个影展。组委会在看完粗剪的毛片后,对王全安说:“我们想让这部影片成为开幕片。”
王全安急了。他反复和对方交涉:“我不是什么德高望重的导演,还不到做开幕片的份量。我情愿这个片子正正经经地去参赛。”组委会的态度很坚定,开幕片也能参赛。
柏林电影节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中,选片向来偏重政治性。《团圆》以国共对峙、两岸分离为大背景,讲述一位离开上海的台湾老兵,50年后重回故里,希望带走当年的爱人。而当年的爱人今已儿孙满堂,两人的决定引发了种种矛盾。
“我害怕这片子一开始太受瞩目,劲儿很快就会过去。”王全安说道,“尤其对于那些评委,他们要看20多部电影,后来都被‘折磨’得差不多了。在后半段看到一个不错的电影,就觉得定了。”按照国际电影节评片的“潜规则”,王全安觉得这个安排对影片拿奖很不利。
北京时间2月21日凌晨,精通法、英、中三国语言的评委之一余男,站在台上讲了一段煽情的中文致词:“这个世界真的很小,我们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分开,我们又会在同一个地方相遇。”接着,她便为王全安的《团圆》颁发了最佳编剧银熊奖。
这番话中,一语多关的寓意不言而喻。余男是王全安最近10年的御用女主角,两人也一度相恋,默契程度媲美当年的张艺谋与巩俐。3年前,他们还在这里共同举起了金熊奖。而今,两人劳燕各自飞。
“认识余男之前,我就是个混蛋。”王全安说道。为处女作《月蚀》选演员时,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找到了颇有个性的余男。“我的人生还从来没有那么宁静、深刻过,过去我一直处于一种混乱中。和余男一起后,我变了一个人,开始踏踏实实做事情,能够集中精力去驾驭、掌控自己。”
在这10年里,两人共同进步。王安全想明白了电影观的问题,而余男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成长为一名实力派女演员。
“我对人生做过计算。从事这个职业,什么时候开始起跑,我需要带什么装备,需要中间加什么燃料,就像准备长跑一样。这些决定了我能跑多远。”王全安告诉记者。
他显然是个优秀的“长跑运动员”。比起同龄人,王全安更有耐心,甚至从没有为找资金焦虑过。他走的每一步都深思熟虑,包括在拿到金熊奖后,他并没有迅速投身商业电影,而是选择继续拍摄低成本的文艺片《纺织姑娘》与《团圆》。
“人生需要一些智慧和偶然”
王全安的父亲是延安党校校长。他却从小性格顽劣,非常叛逆。
他小时候学过画画,11岁进入延安歌舞团。据王全安自己透露,16岁时他搞到一张毛片,给他爸看:“你一定很惊讶,不要太紧张。我想你需要了解一下,现在我出去,你一个人看。”
他也大方向记者承认,在电影学院读表演系时,的确和蒋雯丽谈过恋爱。那时候他27岁,蒋雯丽26岁。1989年,蒋雯丽出演银幕处女作《离离原上草》,饰演一位山区姑娘水秀,而王全安扮演一个有点智障的家族少爷,两人因戏生情,成为当时电影学院郎才女貌的一对。
“蒋雯丽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人,”王全安透露,当时蒋雯丽是所有老师都喜欢的好学生,“我希望能够跟她学得规矩一点,但事实上,没能成功。”
蒋雯丽最近刚完成了导演处女作《我们天上见》。王全安看过这部电影的剧本,原名叫《初潮》,他认为这个名字很好,但蒋雯丽担心通不过电影局审查,最后改了名。
“我一直劝她,不要担心审查,要坚持自己。”提起这事,王安全就着急。他作品的题材其实都挺敏感,《团圆》的背景是台湾与内地的对峙状态,《图雅的婚事》则关于一女嫁二夫的故事,但每一次他都能顺利地过审查关。
“很多人以为我有什么背景,其实我什么背景都没有。”王全安说道。他一般会风风火火跑到电影局,急吼吼地催着审片,“人家都以为你疯了。其实他们以前是虐待狂,突然来了一个人,他们就变成了受虐狂。被你催着、赶着,也就让你过了。”
这种在体制下生存的狡黠,被王全安称为“智慧”。在生命中几次重大转折中,他的“智慧”都成为扭转命运的灵药。
1987年,王全安为了考北京电影学院,和原来的工作单位延安歌舞团动用了各种迂回战术。他首先报考北京舞蹈学院,拿着舞蹈学院的成绩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需要单位介绍信,他就在街上找个刻章的老头帮他伪造了一个章。
考取北电表演系后,他必须从原单位调出自己的档案。据他自己透露,某个黄昏经过档案室,他发现门开着,没有人,而桌上刚好摆着自己的档案,便顺手拿走带到电影学院。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管理档案的人问他,档案怎么会被他自己带来,他答道:“因为我们单位非常信任我。”
1991年,王全安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便到西影厂写剧本。他在北京某个电影圈内酒会上遇到一人,和他同在门外抽烟。那哥们问:“拍电影能挣钱吗?”王全安答:“别信!”那哥们又问:“那能拍个好电影出来吗?”“太罕见了!不过这比挣钱多点可能。”“你要想拍电影,就来找我,”那哥们说。
半年后,西影改制,不发工资了。王全安写完13个剧本后,呆不下去了,才开始想自己拍电影。他给那哥们寄了两个剧本,其中一个就是《月蚀》。几天后,那哥们便汇来10万元钱,“你来北京把这个片子拍完吧,这个剧本我买了。”
B =《外滩画报》
w=王全安
“这个时代不缺大师,缺的是手艺人”
B:《团圆》在上海拍摄时,当时有传言说,这是部主旋律影片。
W:它完全不是所谓的主旋律影片。《团圆》其实是一个复杂、敏感的背景下的故事。在柏林首映后,我很感慨,没有一个记者来问这个故事的背景事件。甚至有的记者,在提完问题之后说:“我们那里也有这种状况。”这就是电影让他产生了思考,而不是电影自己在那里说:“我在思考。”
我在突破过去大家拍电影的一些视野。过去我们拍的所有文艺片,其实都是受制于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狭小空间——别人就是把你当做第三世界的启示录,给你同情。我们这些拍电影的人都一直在其中挣扎,要把自己的东西超越这些限制。我对这一点感受很深,当我拍第二部电影《惊蛰》的时候,就在那里挣扎,但是到了拍摄《图雅的婚事》,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文化观。别人看你的电影,不再认为这是一部中国特色的影片,也不会无法理解这些角色的情感。
B: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里,柏林电影节最重视政治题材的电影,《团圆》被选为开幕片似乎就强调了它本身的政治性,你个人是否认同这部电影背后的政治考量?
W:可以这么理解。语言、影像都是表达工具,但我从来没有用政治来探讨对与错。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自己的利益立足点,所以,我更想从个人的情感角度来看这个故事。电影主角是三个老人,他们共同回忆起当年分开那天的情景,因为心境不同,这三个人回忆里的当天状况也完全不同,甚至连天气都不一样。什么是历史?历史到底有什么价值?虽然我们有那么多不同,但是我们在“吃”这样的底线上还是一致的,大家还可以沟通。所以电影里,我安排了好几个吃饭的场景。
B:你是否觉得,中国沉下心来欣赏艺术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艺术片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W:是。大家都被裹挟在一个东西里面了。中国电影经历了转型的变化后,现在大家都在一窝蜂地摒弃艺术片,开始朝另外一个极端走。现在的中国电影院里,商业片是绝对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观众被裹挟了,你不看这些电影不行,电影院里都是这样的东西。只是这些商业电影的质量还不那么好,让观众不满意。很多人都是带着期待进去了,然后骂着出来。
B:其实在《图雅的婚事》拿奖之后,你当时在第六代导演里,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走向商业化的导演之一,因为对镜头运用的成熟和讲好故事的能力。但是接下来,你却一直在拍摄低成本的电影,比如现在的《团圆》、《纺织姑娘》,为什么没有顺从大流?
W:我为什么要拍商业片呢?为什么要拍电影?电影意味着什么?这是关于电影本体的问题。我受的教育告诉我,电影就是表达我对环境的感受,这也是我擅长的工作。但不是你拍个电影就能去电影节,就能去拿奖,这还要有才能。不管拍文艺片、商业片,作为职业导演来说,都应该在品质上有要求。但是我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大家不分类型,对着商业片问艺术,对着艺术片来问商业……你永远都不会觉得舒服。仿佛这样问,发问的人才更有力量,其实这完全不是同一个问题。我所面临的是一个选择:是要把路修好了,再去拍电影;还是一边拍,一边等着路修好。
B:你会怎么做选择?
W:我当然选择边拍边等。中国电影已经从原来的艺术为上极致走到现在的另一个极端,文艺片都被剿灭了。前几年还有人在抗争,现在大家都纷纷缴械投降了。大家一窝蜂地转型,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连最基本的电影元素都没解决好,比如叙事、人物,然后就奔向大片,所以大片也被拍得七零八落。我算是仅存的几个抗争者之一,我也明白现在电影面临的问题,没关系,我会在商业和艺术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阿凡达》创造了全年最高票房,大家都低估了这部电影里的创造力。在技术上的探索,还不是我们现在能玩得起的把戏。中国电影人一般看的不是人家十年拍一片的等待,而是觉得最好我们能够一年拍出3部这样的电影。如果都去投入这种表面技术,就会损失电影的品质。
B:在国内现在的环境下,还坚持拍文艺片,你的日子过得好吗?
W:你是个好人,谢谢。相比那些和我同年龄的导演来说,我过得很好。我的片酬不错,而且我从来都没有为自己的电影找资金有过压力,一般我拍电影用的资金都是为了扩大影响力。生活有很多方式,我算是个另类,对物质层面的要求不高,一部戏能拿到300万的片酬,已经够我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活了。这个圈子里有很多宿命,出名了就要折腾更大的事情。我只是喜欢电影中的力量感。
这次从柏林回来,我很振奋,又回到了刚开始拍电影的那种感觉。我对目前自己的电影观确认无疑,我终于正常了。过去,我老担心自己会局限在里面。现在,你终于能和世界的艺术家一样了,大家就是在活上见分晓。这个时代不缺大师,缺的是手艺人,我就是手艺人。
B:后面这句话,张艺谋也说过。这次柏林电影节,你们第五代、第六代的两个陕西人正面交锋,媒体也喜欢对比你们两人,你怎么看待这种比较?
W: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前面的人是优秀的,成熟的。我们后辈的人,以前受的教育就是,你出来就是要把过去干掉,自大,目空一切,其实不应该是这样。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这么成熟。他们失利了,是先于我们去尝试了,我们的经验也是从他们那里来的,第五代已经在他们属于的阶段发挥了作用,他们的导演成就,应该受到尊敬。我经常想,如果这一生能拍一两部让自己满足的电影,立马就不干这行了,立刻成为一个混蛋,这辈子就完整了。
B:你还没拍到自己满足的电影?《图雅的婚事》、《团圆》都不能算吗?
W:我还从来没有处心积虑地拍一部电影。我还在生活中,一边生活,一边拍电影,顺便谈谈恋爱,什么也没耽误。我花了10年的功夫,终于想明白了一些事情。前几年拍得慢,其实我就是在判断自己的电影观,都是在尝试,现在证明这是对的。《图雅的婚事》、《团圆》都是为我接下来的电影作准备,为我更看重的电影结构和手法试刀。这些电影已经在我心里搁了很久,我知道,我不拍,也没有人能拍。现在,练习做完了,我要赶快拍戏。